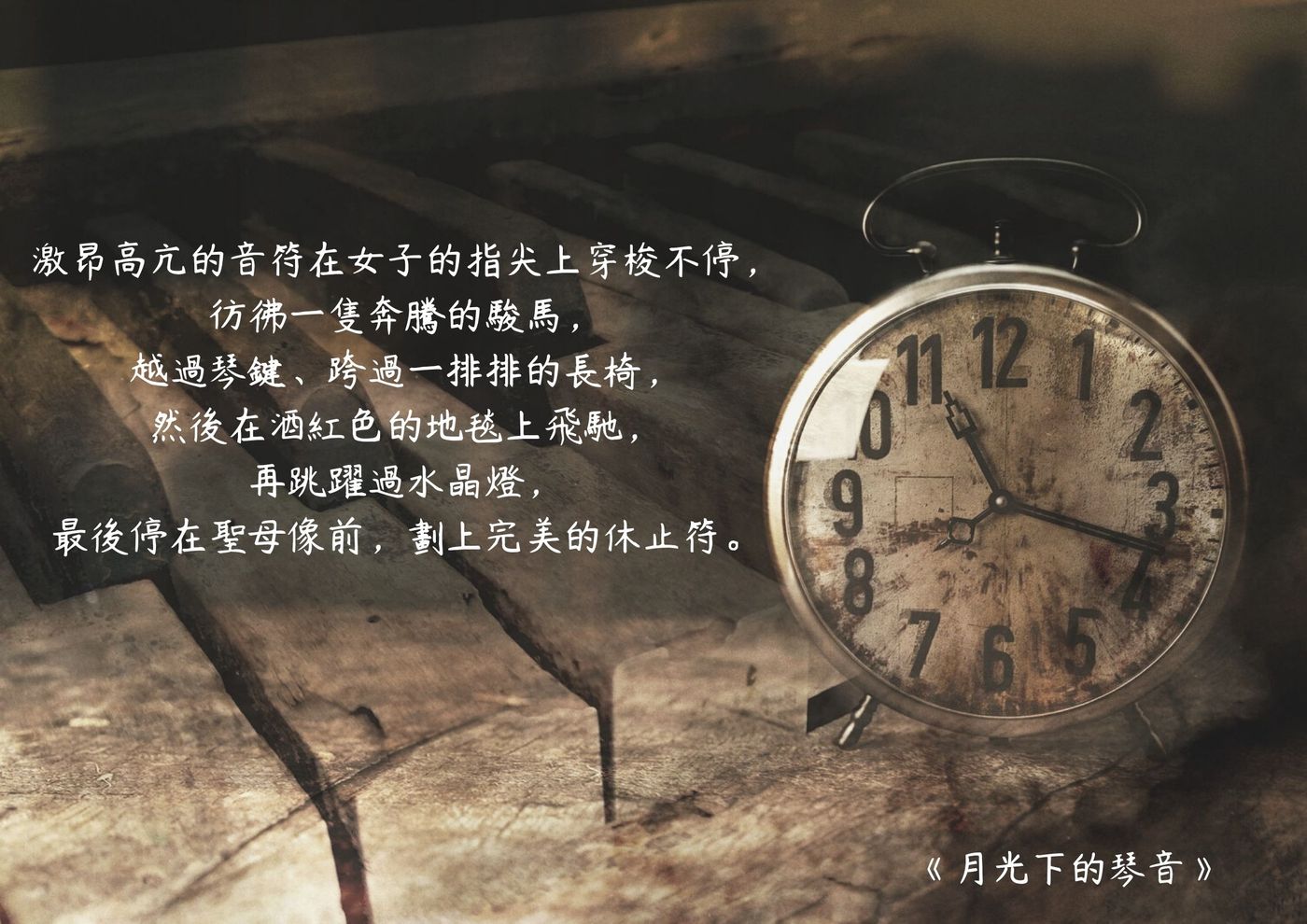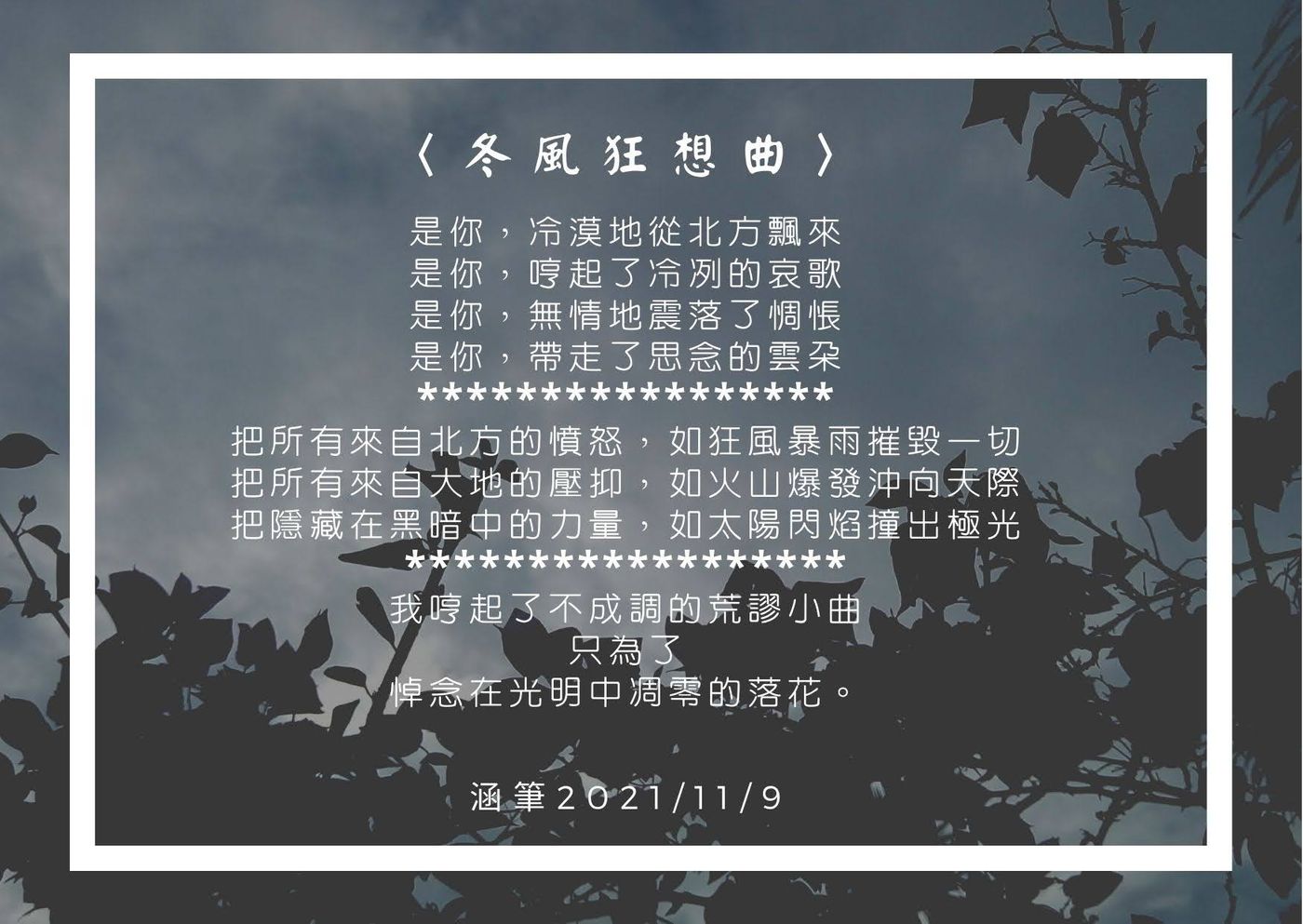伯牙絕弦,獨因琴聲僅為子期奏。
琴,從頭至尾沒有為自己說話,不過是受人撩撥而已。調音師和諧了演奏者與鋼琴之間的對話,傾聽人與琴的共鳴,調音師自以為被捲入人與琴的拉鋸,實則上調音師將一切拉進了自己的故事。
郭強生這本小說書寫了孤獨,鋼琴家問邱老師「你覺得你的家到底在哪裡?」(p.186),年輕的邱老師回答不了,邱老師的鄉愁是埋頭苦練的時光、是沒有天分的遺憾,調音師胡以魯的遺憾是鋼琴家的背叛、是林桑的約定,調音師的鄉愁是無端被撩撥卻不成旋律的感情。
靈魂被騙進肉體,失去自由,肉體失效以後,音樂休止。林桑認為關係建立在供需平衡,調音師感受到背叛,先行離開而讓鋼琴家沒有履行約定的機會,關係失衡破裂。林桑說的話不無道理,但靈魂透過肉體得到了音樂,肉體受動於靈魂,靈魂總想出離肉體,靈魂與肉體也是一種失衡的關係。
有平衡的關係嗎?
「靈魂本來是平等的,但是肉體不是,所以在人的世界裡,唯一的平等,只有靠藝術來完成」(p.167)
「鋼琴家那時的痛苦我終於能體會。他征服了鋼琴,征服了樂迷的耳朵,卻馴服不了自己的肉體。肉體只能用殘忍野蠻的方式去滿足它。」(p.168)
鋼琴家的痛苦是靈魂與肉體的失衡,但是,令鋼琴家痛苦的是靈魂而非肉體,鋼琴家用藝術征服鋼琴、征服樂迷的耳朵,鋼琴家的肉體實現了藝術,肉體被靈魂推動,並不是肉體不能滿足,肉體無法實現靈魂的欲求,才用了殘忍野蠻的方式滿足。
假設靈魂是平等的,肉體不是,並且肉體是因為欲求靈魂而運作,那麼,靈魂的孤獨就是因為沒有一副配得上自己的肉體,好讓靈魂可以忘卻一切,沉浸在真正的琴聲之中。
陪伴愛米麗近三十年的貝森朵夫、林桑買下的史坦威、鋼琴家那台外型損傷的史坦威、卡爾倉庫裡被拆分燒毀的二手鋼琴、李赫特故居兩架被展示的史坦威……
如果痛苦的只有肉體,或許還是比較好的。
「讓我們走進一座森林,然後在壯茂的林群中挑選出一棵,再由伐木工人將它砍下,送進木材廠。
接著,設計師開始為它規劃音箱與音響板,木匠與鍛冶師傅開始動工。一根弦接一根弦,一個螺絲接一個螺絲,擊弦系統有了,飾著渦漩花紋的琴身有了,然後是調音師出現,為它做最後的整音。
一架鋼琴於焉成形。」(p.59)
鋼琴是為了成為鋼琴而存在的。
鋼琴的身體是不平等的,或許因為原料不同、或許因為工匠的手藝之別,每一架鋼琴都是獨一無二的,但是,所有獨一無二的鋼琴都同樣是鋼琴,因為鋼琴的靈魂是一樣的,也就是說,所有鋼琴的身體,都是為了相同的鋼琴靈魂而存在的。我們不是從鋼琴的身體認出鋼琴的,是因為鋼琴有了靈魂,鋼琴才是鋼琴。
誰會在傾聽音樂的時候,仍舊記得鋼琴的身體呢?
靈魂離開身體,李赫特晚期用的鋼琴是山葉而非史坦威。
藝術在哪裡?
藝術是靈魂與肉體的調和,梅洛龐蒂也說過:「畫家把身體借給世界,才把世界改變為畫作。」靈魂最初是自由的,靈魂與世界同在,重新把身體借給世界的鋼琴,才能將世界改變為音樂,鋼琴是音樂的身體,音樂是鋼琴的靈魂。鋼琴作為音樂的身體讓音樂成為可能,演奏者因此能藉由鋼琴獲得音樂或靈魂,同時,演奏者也將自己的身體借給鋼琴,演奏者成就了音樂與藝術,如此才能重新在藝術中找到平等與自由。
藝術家出借自己的肉體,將靈魂改變為作品,作品已經是肉體與靈魂的產物。或許藝術是平等的,但當藝術成了藝術品,藝術品就獲得了自己的肉體,靈魂與肉體的關係再度失衡。
痛苦,屬於永遠失衡的關係。
小說的最後,調音師讓展示的琴保持在靜默之中。
琴是被用來演奏的,調音師讓琴靜靜沉睡,自己走入茫茫白雪之中,如同青年調音師在〈無言歌〉中想到的雪,鋼琴師說音樂讓我們聽見了時間、聽見了自己的影子,沉睡的琴,調音師的影子。
或許,靜默的琴才能展現真正的琴聲。
《呂氏春秋‧本味篇》伯牙在鍾子期死後破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呂不韋以此為喻,認為不能以禮待賢,則能人不能發揮所長。影子是肉體的延伸,或者更是超出肉體的靈魂,若我們能從影子認出一個人,那便意味著影子已經吸納了人的靈魂,如同琴聲回應了人的靈魂。透過琴聲聽見太山流水的子期聽見的是伯牙的影子,伯牙再也不能彈琴,是因為子期已經被吸納到伯牙的影子之中。
伯牙絕琴,因為琴聲再也無法承載伯牙的影子,子期的缺席換來更巨大的在場,只有琴聲靜默之時,子期的死亡才能喧嘩而至。琴聲無法回應伯牙的撩撥,呂不韋類比到賢人無法回應無禮的待遇,這種類比是因為死亡超出了琴聲而賢人的才能超出其待遇,回到郭強生的小說,則是調音師的孤獨超出了他的肉體。
調音師在卡爾的倉庫失控砸琴,年輕調音師在鋼琴家的琴留下刻痕,但真正的印記始終在調音師身上。
「我與偉大之間最近的距離不過就是,我也厭惡自己,如此而已。」(p.196)
這是調音師在看過《謎樣李赫特》全片以後的想法,靈魂的孤獨是永遠沒有回應的哀求,也是一個不曾擁有鋼琴的調音師,小說中人來人往,調音師的琴聲不為誰而奏。
調音師走進茫茫白雪,回到了自己的影子之中,調音師的肉體也感受過他人的擁抱,但那也不過是離別前的一種儀式,調音師孤身一人,調音師的懊悔、躁動、軟弱被調校為沉默。雪是調音詩的孤獨,也是調音師的鄉愁,那裡「是無限可能的、那種無法預測的、宛若如釋重負的沒有。」(p.219)
「起初,我們都只是靈魂,還沒有肉體。」(p.21)
最終,被折磨的是靈魂,不是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