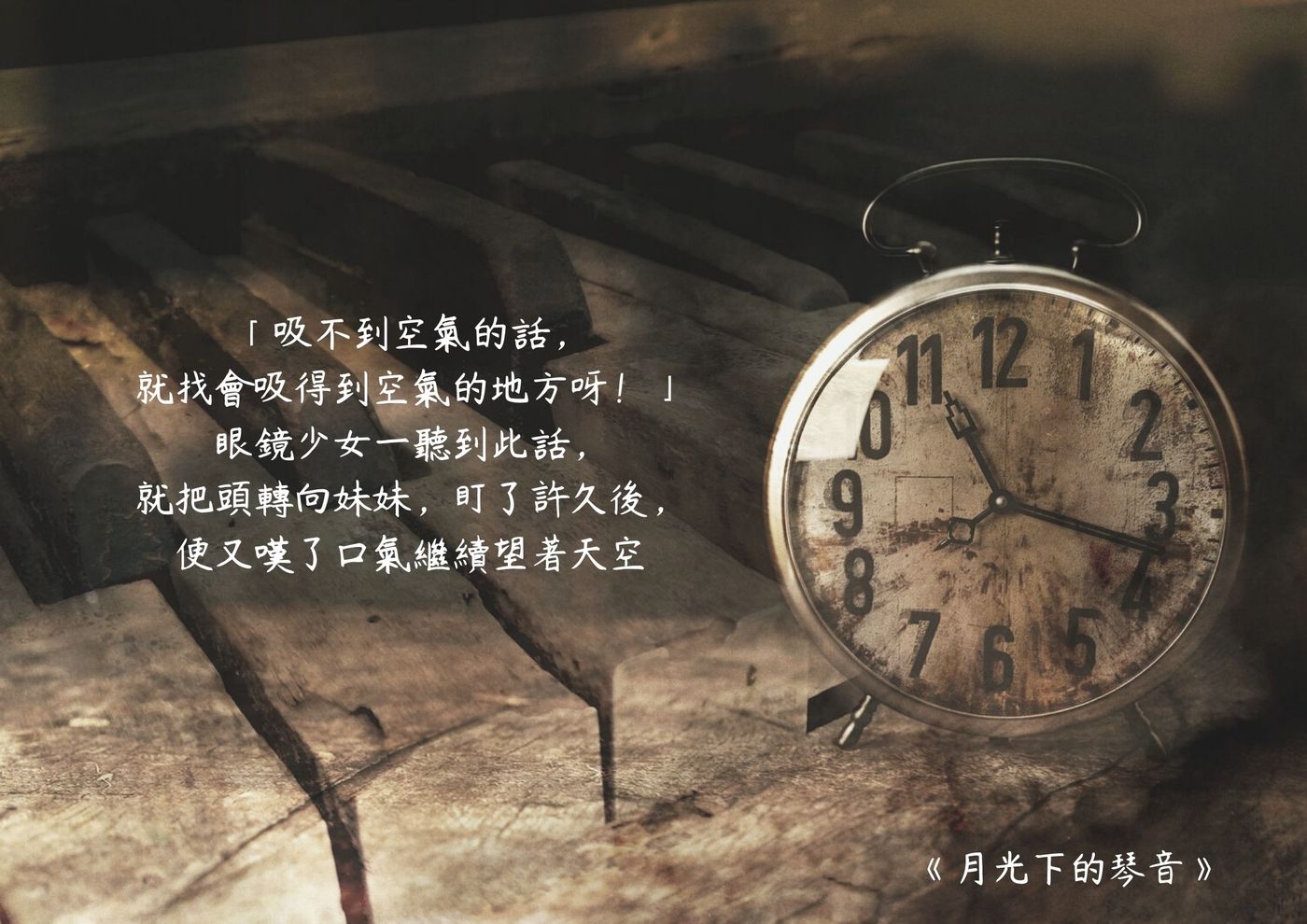那是個初夏,她端坐在窗邊,精神煥發的及膝短裙和高馬尾,玉手輕托著白裡透紅的臉蛋,朝陽篩落紗窗,細膩而溫暖,桌椅被曬得乾燥、溫煦,留香出色的木質調與她清新淡雅的氣質頗為相襯,一時看得出神,她驀然回首,相視而笑,一雙杏眼含苞待放,然而羞紅的粉杏,卻早已悄悄在少年臉頰盛開。
某日的下課,松榕和麗日的蟬鳴如常不斷重複播放,其他的男同學都跑去籃球場打球了。少年默默從參差書本間,抽出一張橫線筆記紙,雖然有點皺摺,但無妨;在墨水的流淌下,字字生花,少年將難以啟齒的話語都刻寫在字裡行間,筆尖滑行紙面,卻如觸寫心頭,不知不覺,他已蒔起一座花園。
心中溫軟的漣漪澆灌著情愫,少年信摺成紙飛機,試圖用幼稚的外表隱藏內心的情竇初開,所有心口不一的詩情畫意都打包成了客機上的行李。盡職的飛機應飛往兩地,可那架紙飛機、那份心意,卻始終只徘徊在抽屜裡。
那天的下午驟起午後雷陣雨,是雨滴濺起的旋律、放學的鐘聲喚醒了他。所有人收拾好東西就撐著傘回家了,卻有兩個人不曾離去——
一個在出門前忘記帶傘,一個帶了傘卻故意等雨。
那個她在屋簷下等待放晴,在朦朧的綠草如茵前,對著雨幕神遊,沒有發現身後走廊的長椅,也坐著一位為眼前對方痴迷的人,他幻想走廊積水的倒影,是她害羞的點頭;但他仍舊緘默,專心欣賞眼前的,雨。
少年不會承認,任由紙飛機在抽屜裡循環起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