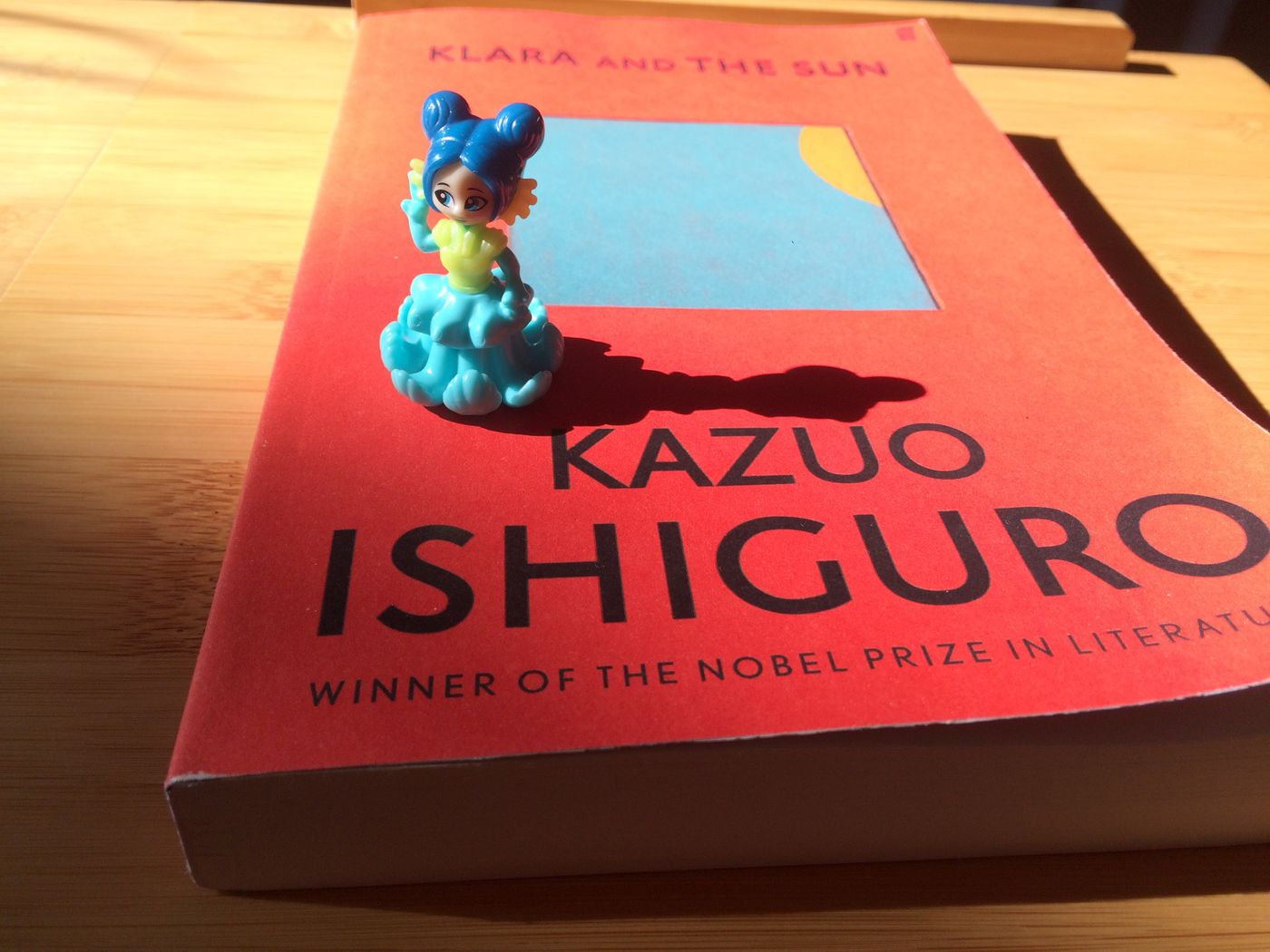影評| 《克拉瑪對克拉瑪》╴屬於父母的成年禮,家庭關係與自我實現的兩權相害。
閱讀時間約 3 分鐘
(涉及些許劇情內容,請斟酌閱讀)
如果是常駐在NETFLIX的各位影迷們,肯定對兩年前赤裸裸探究婚姻本質的《婚姻故事》毫不陌生,昔日幸福美滿且真心相愛的絕配夫妻,是如何走向互打離婚官司爭奪監護權的狼狽姿態,其充滿犀利的爭吵橋段與強迫製造對立的法庭攻防,都一再衝擊著觀眾對於愛情與婚姻的既定認知,而其實早在上世紀的1979年,《克拉瑪對克拉瑪》就已先於前者探討了組織家庭是否成為了阻擋自我實現的一大障礙? 以及對於父權社會下,不僅女性受到了無形壓迫而無從喘息,男性同樣也遭受刻板印象的束縛而無所適從。
【柴米油鹽才是維繫家庭的艱難之處】
《克拉瑪》的劇情極為簡單,平時男主外女主內的三人家庭,當母親離去後,「父代母職」成為戲中角色們的最大挑戰,由梅莉史翠普飾演的母親喬安娜在電影前半段幾乎沒有戲份,我們只能父親泰德與兒子比利的口中,得知母親究竟是甚麼樣的人,她的身影也充斥在這不大不小的公寓之中。
喬安娜無預警地離開,對泰德而言就像是顆空降飛彈砸向心頭,第二天一大早他帶著放不下的男性尊嚴,嘗試一邊為比利做法國吐司當早餐,一邊安撫著他聲稱母親只是暫時離開,原以為能處理的游刃有餘,不熟悉廚房操作的他最後卻把場面搞得一蹋糊塗,這平凡樸實卻一氣呵成的橋段,不需多餘的畫面說明,就能展現這家庭的全貌。
泰德確實是個勤於工作卻疏於陪伴的父親與丈夫,顧小孩與顧工作的泰德蠟燭兩頭燒,與比利的衝突也在日後的一場餐桌戲一次爆發,比利的焦慮來到極限,刻意的不聽話與父親產生爭吵,一來一往的互不相讓使戲劇張力無限增強,最後都以盛怒之下的幼稚話語「我恨你!」來結束爭吵,鏡頭剪接迅速窘迫且不安感隨時準備引爆,泰德乃至於父親這一身分無法察覺的盲點就在爭吵之中緩緩揭開。
【身分的互換,抑或是互通?】
冷靜下來的泰德,主動與兒子和解,比利這才敞開心胸說出自己的存在是不是就是母親會離開的主因,他叛逆打鬧、情緒不穩皆是源於孤獨與自我厭惡的循環所產生的結果,泰德這才明白家庭從來不是一個人的努力所能支撐的,在父權體制下,家庭的組成,是由母親投注時間心血與自我的犧牲,來換取父親在職場心無旁鶩的拚搏。
梅莉史翠普在揣摩角色時心想:
梅莉史翠普在揣摩角色時心想:
「我所有的朋友,在某個時間點都曾經想撒手不管,放下一切離開,嘗試看看有沒有另一種人生。」
顯然現代人光靠「愛」無法滿足地立於世間,喬安娜對於重塑自我的渴望,側面映照著70年代美國婦女紛紛投入職場的社會概況,先是成為了父親的女兒,接著是泰德的妻子,最終將以比利母親的身分度過餘生,厭倦「標籤」的她即使與泰德同樣深愛著比利,也免不了的踏上找尋「身分平衡點」的路途,與父親泰德的成長曲線相比,喬安娜的醒悟更顯得隱蔽私人。
泰德於法庭內的一席話則點出了社會對於男性本應強悍、專注於事業的期盼眼光
「我不知道有哪裡寫過,女人天生有母愛,男人對孩子的愛就一定比女人少。」
父親的愛就該顯現於經濟能力的成長,而不是柴米油鹽的平淡幸福,這對於深愛兒子比利的泰德顯然是非常不公平的,尤其是在經歷了相依為命的數個月後,母親與父親的身分互換,使兩人皆跳脫了原有的社會價值觀。
【遲來的自我覺醒課】
《克拉瑪對克拉瑪》與其說是拆解西方複雜多變的婚姻觀,更聚焦於家庭的本質是會隨著人們的意志與時代的變革而有所改變的,該如何在愛自己與愛他人之間找到屬於自己的平衡,是克拉瑪們所面對的難題,移轉到四十年後的現代仍舊適用。
泰德與喬安娜冰釋前嫌在電梯即將關上前的破涕而笑,除了與片頭的分道揚鑣相呼應之外,同樣代表著主角泰德已不再以相同的價值觀看待眼前的女人,她既是孩子的母親,也是那個勇於出走的喬安娜,「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12會員
12內容數
留言0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