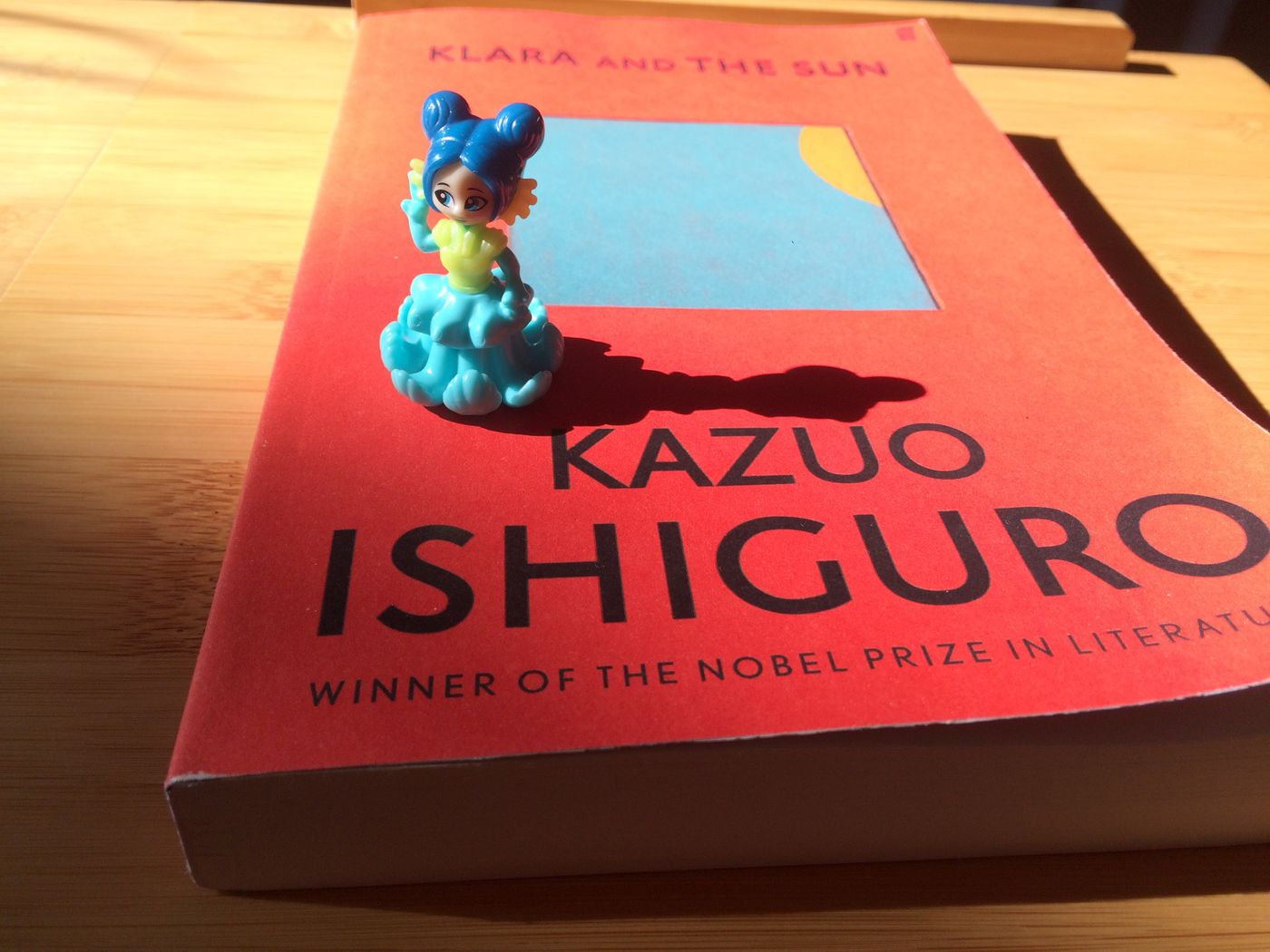石黑一雄的新作《克拉拉與太陽》(Klara and the Sun)讀來有熟悉之處,其筆尖有著慣常的疏淡間隙,陳述一個不難理解、甚至有些穩當無趣的故事,此種形式與他始終在探究的恆常命題有關:記憶,那些關於回憶與遺忘的渲染疊加,完好與筆法基底融合,使本書在模糊與清晰各有精采之處。然在記憶之外,它持續叩問的是這個記憶存在是不是永恆的印刻?甚至有沒有複製與替代的可能性?主體之外的擴展延伸,正是關於人和人之間的運作謎底。

克拉拉是一位依靠太陽能運作的人工智慧,書中譯為「愛芙」(AF, Artificial Friend),它們是用於陪伴、照顧人類的家庭夥伴。克拉拉日復一日於店中櫥窗觀望街道熙攘、觀察對街大樓映射太陽的角度,直到女孩裘西來到店裡,克拉拉被她的母親挑中,一同前往那座可以望見整片鄉野的宅邸。克拉拉、裘西和母親之間的對話及關係編織成主要重點,當克拉拉詮釋的「我」牽引讀者看往那些未曾注視的點,我們到底會從中看出什麼呢?
當「我」相信一件荒誕的事為什麼書中會以克拉拉為主要敘事者、即以克拉拉的「我」進入故事主體呢?首章便可察覺如此設計所帶來的獨特偏重感,在她眼中,店裡重要的事情有兩件:一是每組愛芙都可能輪換到的櫥窗位置,他們可以透過透明玻璃觀看人類社會的表層樣態,包括建築形式、行人舉措以及他們對於自己投射出的目光,所有片段線索拼湊成愛芙理解世界的孔隙,其中克拉拉又展現出更濃郁的好奇:
「我看得越多,就會想要知道更多事情,而且不同於羅莎(另一位愛芙),路人對我們流露的神祕情緒讓我感到茫然不解,也越來越讓我心醉神馳。我知道如果我沒有多少理解這些諱莫如深的現象,到時候我就無法盡責地照顧我的孩子。」
克拉拉的觀察有其目的性,她所收攝到各種場景和互動最終都會化為可編寫素材,幫助她更理解人類是如何運作的、怎麼樣傳遞彼此之間的喜好和厭惡,近似於新生兒被拋擲到社會中重新社會化的過程。但她並沒有實質意義上的父母,沒有先行者帶領她漸次熟悉,於是那些自行捕捉的觀察和推論,反倒顯影出那些習以為常的陌生之處,毋寧說,克拉拉依循著單純的經驗法則建構了一個外於慣常人類體系的體驗視角。好比說,那兩個計程車司機為什麼可以在大打出手之後,又各自回到車上在同一條路上等待同一個號誌?為什麼雨衣男會跑過穿越道跟咖啡杯女士擁抱?為什麼乞丐男和他的狗會在陽光下重新復活?
這一切推論的邏輯核心,又必須回到愛芙賴以為生的能量:陽光,這是在櫥窗中的克拉拉時常提到的另個元素。當然,科學證實地球生命起源與太陽有著重大關係,但那些間接隱微的能量傳遞早已不夠現代人將太陽供奉為神祇,反對克拉拉而言,太陽作為「養料」不僅是實際能量供輸,更狀似於古老世界觀的再次甦生,它是自身得以運作的生命起源,是能夠對之低聲祈願的高等存在。因此對讀者而言,克拉拉其實算是個非典型的不可靠敘事者,她並不是刻意隱瞞或思維錯亂,而是以獨特思維架構世界之聚散,各種事物之間有她相信的因果關係,縱使在我們眼中何其荒謬。
你能不能為我模仿她
當克拉拉越是進入她們的生活,裘西與母親之間的關係便越趨明朗,因裘西患有某種危及生命的疾病,母親言語行動中總是暗藏著緊張,懼怕她如另一位子女莎爾一樣過早擁抱死亡命運,那不完全是種平靜自在的關懷,一者傾瀉所有,一者恬然承接,那顯現出親密關係中隱然鋒利的爪牙,渴望保護的心情,有時竟無異於疼痛撕咬。
有一幕特別可以展現出克拉拉、裘西與母親三者各自的位置,那是某一個周日,裘西想去之前曾去過的摩根瀑布野餐,她興奮地希望克拉拉也能同行,母親也答應了。沒意料到即將出發那天,母親在庭院車道上準備出發時,她的神情卻突然凝重,對剛坐進車的裘西有些怒慍,「你以為你騙過我了嗎,是嗎?小女孩。」母親發覺女兒裘西有些不適,希望她留在家裡,裘西不從,但最終仍被趕下車,只剩下克拉拉和母親一車前往瀑布。
以克拉拉的視角觀之,她無法得知裘西的健康是否真的出現問題,先前行文觀察也都沒有特別提及,於是讀者可以理解母親此處的發難,是因關懷女兒而產生的細緻觀察,她看見了常人無法見到的生理細節。但亦有另一種解釋,是母親創造了裘西那脆弱易碎的生命樣態,她渴望女兒健康的慾望大過於真實情況,限制住親密家人,連一點疑慮汙染都不要有,反倒將愛詮釋成另一灘纏人泥淖。
母親和裘西的關係非常耐人尋味,甚至或許是某些罕病家庭的典型光景。她們之間絕對存在著愛,她們也都彼此倚賴和給予,但因那顯而易見、就逼近眼前的失去,那關係遂包括了各種形式的靜默、焦慮和隱瞞,像是母女二人在早餐時間的若即若離、城裡特別的畫像計畫,還有克拉拉來到家裡的原因。
母親和克拉拉來到摩根瀑布,他們閒談了一下,母親便要求克拉拉能不能模仿裘西,模仿她的微笑、模仿她有些歪斜的走路姿勢、模仿她說話的遣詞和音調。
「不對,那是克拉拉。我要的是裘西。」
乍看之下是簡單的日常話語,越去拆解卻越使人感到悚然,一團棉絮中的針。能不能為我模仿她,本質中蘊藉了一種深層暴力,為了他者置換自我的獨特性,意味著湮滅自我的外在表象,是否代表著屬於我的存在,也在那一步步的模擬中被覆寫與消滅了?
你能不能為我模仿他,或許是對所有人來說都萬用的句型,眼前所見的你是尚未完美的雛形,憑藉著我的渴望加工指點,藍圖是遙遠觀看或聽聞的美好他人,是我心中永不褪色的理型。並非所有的愛都能滿足這個邏輯,或者安於存放於各自定位,所以我們擁有成千上萬備著、用以汰換的你,而模仿比複製更殘酷的是,你的心中仍然有一個我,也同樣有著那個萬用句型。
在問「人真的可以被誰完美複製嗎」這老掉牙的聳動標題之前,首先要處理的是克拉拉到底是物體還是人類?若是物體,當然置換的道德包袱便較小,但有趣的是,克拉拉作為最貼近讀者的主要敘事者,我們在先前近百頁的敘述中體驗了她的觀察側重、情感運作和思考模式,在此前提下,我們願不願意讓她有反對被替換、被選擇的權利?當讀者進入了「我」面臨這個請求時,這個回答就不是那麼理所當然僅是劇情推進的單一選項,而層層掏翻出各種面向的思考:克拉拉召喚出來到底是一個人還是物,而讀者的我面對「我」這個物時,又應該有什麼解讀?
真實而永遠的愛
對於這一切,克拉拉是怎麼思考的?在摩根瀑布時,克拉拉沒有拒絕母親的要求,她短暫模仿了裘西,卻意外惹惱了情緒未穩的母親,克拉拉因此漸次萌生起想要幫助裘西的渴望,她想到了天上燦然閃耀的太陽,它象徵著豐沛生命,克拉拉希望它能夠解救羸弱的裘西,因而踏上了另一趟旅程。說是旅程,其實不過是從瑞克家走到原野彼端的穀倉,然這短短的距離,卻寄蘊著作者對於故事困境的某種重要解答。
瑞克是書中另一個重要角色,作為裘西的青梅竹馬,一起成長的過程中也培養出某種淡然曖昧,他關心臥病在床的裘西,會來到他的床邊,玩著填寫對話泡泡的遊戲,這亦是另一種呈現關係縮影的有趣方式,畫圖的裘西或許早已預設好泡泡中應該填入甚麼、他應該對我說什麼,一旦超出想像之外,裘西不免沮喪,瑞克也因此感到懷疑或不滿。克拉拉作為旁觀者,在一次前往瑞克家拜訪時提出請求:她希望能在太陽下山前到達遠方的穀倉。
縱使瑞克無法理解克拉拉為何想去,他仍然給予協助,促成克拉拉完成故事中最魔幻的時刻。她在廢棄無人的穀倉中對太陽說話,那虔誠姿態儼然近乎於祈禱,祈禱太陽能夠讓裘西度過難關,祈禱太陽能像對我灑下養料那般、也眷顧著我所照護的女孩。作為補償,她決意去消滅遮掩陽光、破壞環境的重型器械庫丁機,想當然,庫丁機的消滅與太陽的治癒完全沒關係,她進城去消滅一台庫丁機僅是徒然,於是克拉拉回家後再一次向太陽祈求,這一次,她拿出的籌碼是瑞克對裘西的愛,那真實而永遠的愛。
大可說這一段充斥著無可救藥的人文浪漫,過於童稚的因果連結,這種不切實際像極了失真童話,然一如上述,克拉拉能夠、也可以達成我們看來荒謬的請託,因為在她純粹響徹腦海的話語中,這的確是有可能發生的未來,太陽確實可能因為兩人之間的愛而護佑他們。此處我們看見了科技倒退回蒙昧的弔詭,高科技的仿生智慧竟然回頭信仰蠻荒時代的天文神話,或者是,人造科技帶我們在意義的黑夜繞了一大圈,最終的解答仍然那一輪自然光芒?
出乎意料,裘西的身體狀況在一次夕陽斜照之後開始好轉,可是作者也未全然歸結於愛的永恆。人無時無刻都在變動,相貌身材或話語思維,人難以擁有那個持續存在的內核,更遑論愛要定錨兩人,那就像是在飄盪浪頭的兩端搭建橋樑,真的有可能在時間變動之下建立某種永恆的關係嗎?尾聲,裘西即將上大學,瑞克反而不再執著於進入學院,克拉拉反倒有些困惑,那這樣的話,那時所聲稱的愛是不是還存在呢?作者藉由瑞克的回答,提出他對此的看法:
「裘西和我在某種層次上是永遠在一起的,一個更深邃的層次,即使我們奔向外面的世界而不再相見。我不能代表她說話。可是如果我到外面的世界,我知道我會不斷尋覓某個像她一樣的人。至少是像我曾經認識的那個裘西。」如此回答也間接解除了克拉拉最終對經理閒談中的困惑,「的確有個很特別的東西,可是不在裘西心裡,而是在所有愛她的人的心裡」。
原來人在時間中所留下的,也僅是一圈空蕩輪廓,從沒有誰能把握留存什麼,我們最為獨特的部分反倒如拼圖般切分,掌握在他人的記憶裡。換句話說,讓人得以永恆延續、不可替代的那層殊異性是由另一群愛你的人所賦予,群己鏈結不斷延伸下去,進而讓每個人都能在人際網中確知自己是不能被複製的,獨一無二的「我」。
是不是太高估愛的存在與作用了呢?現實經驗裡,凶險傷害永遠多過於溫馨懷抱,愛不過是另一則說出來會被笑的夢幻神話。而我喜歡這部作品的原因,正是石黑一雄讓克拉拉選擇相信、選擇讓她說出那些可笑的祈願和祝頌卻完全不覺得怪異,因為在她的世界裡,愛就是這樣運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