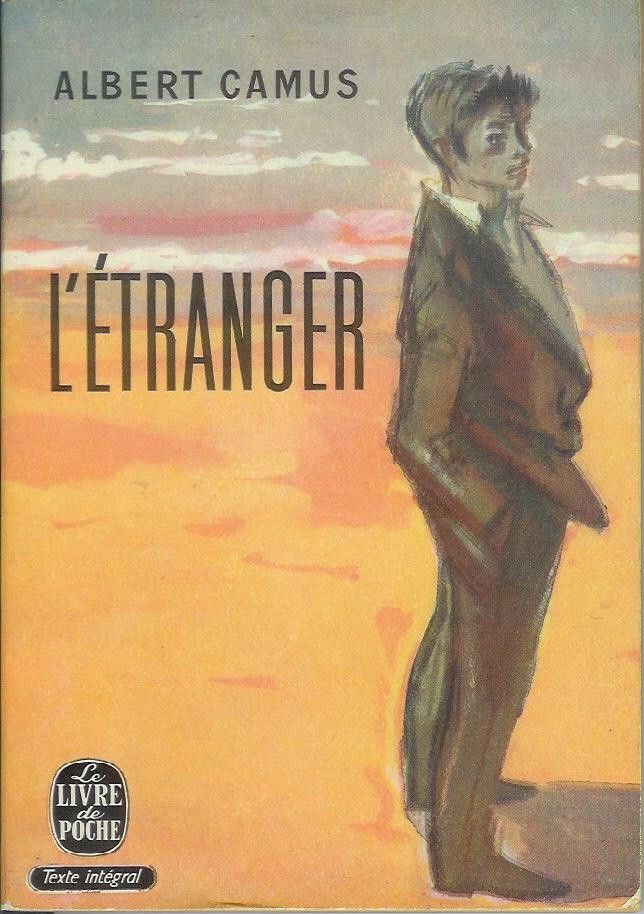永遠的異鄉人 八問卡謬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如果你身在黑暗中,你要習慣黑暗,還是要去找光?
如果你舉起火炬,已經習慣黑暗的人,會不會攻擊你的光?
我有問題想問卡繆。你為什麼在諾貝爾頒獎典禮上說:「不要在我後面,不要走在我前面,請走在我身邊」?
1957年10月17日,我44歲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是法國最年輕的得獎者。我當時飽受法國知名知識分子攻擊,帶頭的是沙特。他們狂熱信奉革命,認為要達到美好未來,任何犧牲在所不惜。就是為了炒一盤完美的炒蛋,打碎一千萬個蛋也值得!
我認為這太荒誕,蛋不是用來砸碎的,也不必只用大火炒,你可以用適當的溫度,把千千萬萬的蛋孵出來。
諾貝爾文學獎給我的獲獎評語是:「他熱情而冷靜的文學,闡明當代人良心所面對的問題……他遠遠超越虛無主義,以嚴肅的沉思,重建已被摧毀的東西,使正義在沒有正義的世界,成為可能……毫無疑問,符合諾貝爾獎所設立的理想主義目標」!
這讓我得到一面盾牌,但我的手中沒有劍。我在得獎演說中說:「不要走在我後面,因為我可能不會引路;不要走在我前面,因為我可能不會跟隨;請走在我的身邊,做我的朋友」!
你的童年快樂嗎?
1913年,我出生在法屬阿爾及利亞的勞工家庭。爸爸是法國人,死在一戰的馬恩河戰役,我來不及認識他。媽媽來自西班牙,不認識字,丈夫死後無依無靠,帶著我投靠在阿爾及爾的娘家。
家境窮苦,身上有法國血統,卻出生在殖民地阿爾及利亞,我被叫做「黑腳」pied-noir,社會地位勉強比阿拉伯人和柏柏人(Berber)好一點。我念貧民區的小學,畢業後本應立刻工作。但老師鼓勵我升學,幫助我努力拿到獎學金,考上中學。
獎學金讓我能吃免費早餐,在中學,遇到不同背景的孩子,學校要我填媽媽的職業,我填了「家庭主婦」,覺得丟臉,又為有這想法的自己感到羞愧。
我轉念一想,覺得不需掩藏自己的平凡,需要找尋的是自己「到底是誰」?果然學校生活變快樂,我文武雙全,喜歡游泳和踢球。
什麼人帶你走出困境?
17歲時,我被診斷出肺結核,醫生認為我活不下去。這時,我讀到皮柯提特斯(Épictète)的作品:「疾病對身體是一種障礙,但是對意志不是,除非意志變弱。」我領悟真正會殺死人的是絕望。
希望跟著升起,我搬去跟做肉販的叔叔住。一來避免傳染給家人,二來能多吃叔叔宰的紅肉,住在高山上養病。叔叔外表看不出是屠夫,更像世家子弟,他自修自學,家裡有大量文學藏書,巴爾札克、雨果、左拉,還有無政府主義的政治書。我大開眼界,開始學叔叔穿著,打扮脫俗,思想跟著明亮,不再自卑,整個人自信起來。
什麼改變你的政治動向?
我遇到另一個貴人格勒尼埃(Jean Grenier)老師。老師教哲學,我因此吸取古希臘思想和尼采,開始在文學雜誌發表文章。我半工半讀,但心靈富足,常跟朋友到咖啡廳大聊文學、詩和政治。
20歲,進阿爾及爾大學,三年拿到哲學學位。拿到教師執照,但我沒有去教書,受到格勒尼埃影響,我加入共產黨,希望幫助人們不再痛苦。
我發現阿爾及利亞的共產黨,越來越像他們最反對的法西斯主義。我公然批評史達林,1937年如願被開除黨籍。
做記者對你有什麼影響?
1938年,我到報社當記者,看到更多不公不義,寫出多篇尖銳評論。同時開始寫著名的「荒謬系列」,小說《異鄉人》、哲學隨筆《薛西弗斯的神話》和劇本《卡里古拉》。
二戰爆發,我想加入軍隊,但因為有肺結核病史被拒絕。我宣揚左派和平主義,發表文章反戰爭、反希特勒、反史達林、反阿爾及利亞當局。1940年,政府禁掉我任職的報社,我離開家鄉前往巴黎。
你和沙特怎麼相識?
1941年,法國投降,我投入反納粹運動。1942年出版《異鄉人》,故事描述一名年輕人,意外捲入兩場死亡事件,最後因為他無所謂的態度,而被荒謬判死刑。
沙特讀完,寫書評推崇,我也讚賞沙特的小說《牆》和《嘔吐》。法國身陷黑暗,我們兩個英雄相惜,為黑暗中的法國年輕人點亮火炬。
你為什麼和沙特決裂?
但我們在戰後出現分歧,沙特沉醉在共產主義的革命願景,相信革命帶來自由。但我看過人性百態,警覺背後的瘋狂與失控。
1951年,我寫了《反抗者》,拆穿革命、虛無主義、辯證法、普遍主義、歷史決定論的荒謬,揭發革命的罪惡與暴力。
沙特不在邏輯上辯論,他用人身攻擊,嘲笑我知識淺薄,沒讀過深奧的哲學。同樣含金湯匙出身,巴黎高師畢業的高級知識分子,西蒙波娃、梅洛龐帝、阿隆(Raymond Aron)也全部一面倒攻擊我,我在巴黎文壇被孤立成局外人。
為什麼你不熱衷「革命」?
1954年,阿爾及利亞戰爭爆發。我一面痛批法國在北非的殖民政策,一面反對獨立運動盲目的恐怖暴力。我想到,他們向電車發射炮彈,我媽媽可能剛好坐在電車裡。如果那就是正義,我會偏向我的媽媽。
當時「革命」是最時髦的口號,「切格拉瓦」是最被崇拜的英雄。我批判資本主義不公平,也要求社會主義要寬容,我夾在中間,備受來自摯友的譏諷,處境孤獨而荒誕,如同唐吉軻德。
卡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搬到普羅旺斯的小村莊獨居生活,東西極簡,只有床、書桌和文具盒。1960年1月4日,他在鄉下死於車禍意外,隨身公事包裡,除了日記、信件、護照以外,還有一百多頁未完成的《第一人》手稿。對世界這麼有重量的靈魂,身體卻如此輕輕碎去。最不該死的人,死在最不該的原因。荒謬叫人無言。
卡繆一生都在問自己是誰?是法國人還是阿爾及利亞人?是貧窮或富有?身體虛弱,肺結核纏身。他很接近死亡,所以一直探討為何存在?
「作家不該為製造歷史的人服務,要為承受歷史的人服務」!他察覺到世界種種荒謬,沒有絕望,而是用力活著,點燃人道主義的火炬,反抗光明旗幟背後的黑暗!
為什麼會看到廣告
375會員
960內容數
當心中的夢想火苗燃起,需要的是「燃料」去推動夢想,但是去哪裡取燃料呢?媒體只能告訴你,誰成功了,只有表面,沒有深入。學校也一樣,只能告訴你那些人很偉大;沒辦法告訴你,他們是「如何」成功的?「為什麼」他們可以有不一樣的人生?
留言0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