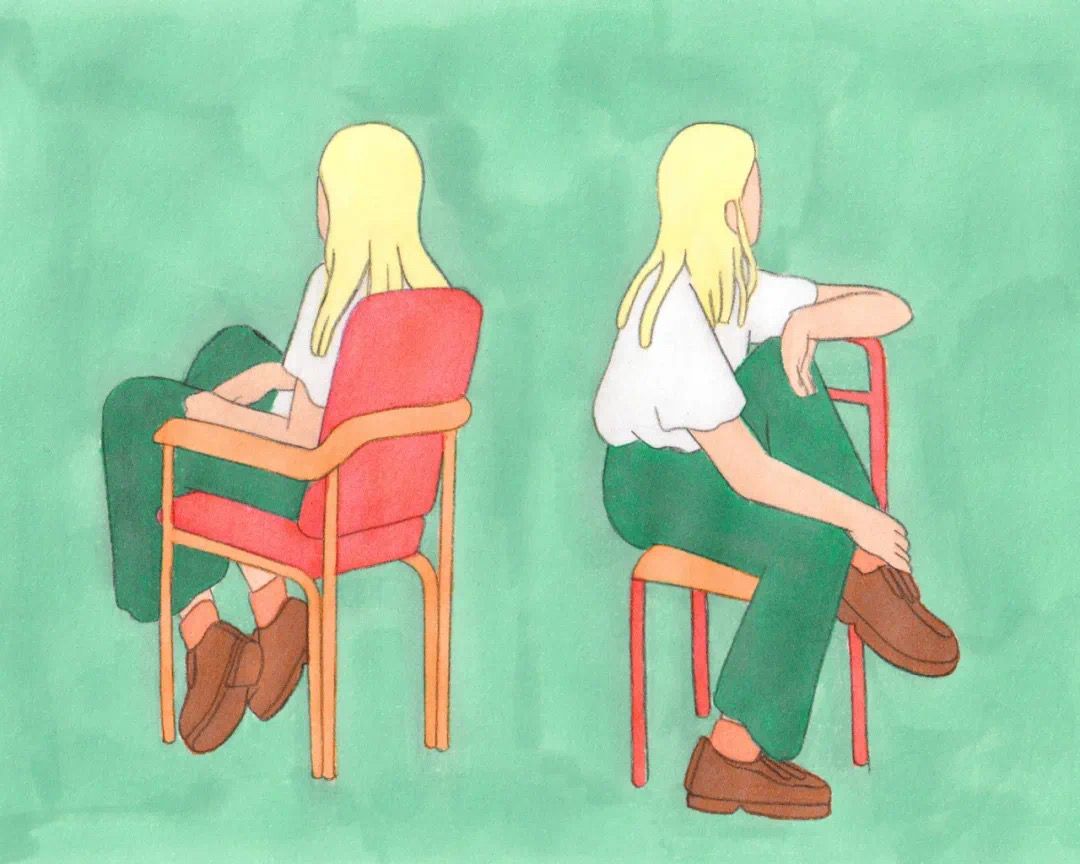一個名叫郭慨的男人(上)
閱讀時間約 30 分鐘
柳絮從來沒想到過,三四十隻貓狗聚集在一起會鬧成這樣,簡直像在房裏扔了一億響的連珠鞭炮,翻來覆去地炸。
這是她發起的一個救助遺棄貓狗的公益活動。任何看見網絡公告的人都可以來參加,要求帶一份給貓狗的禮物,並和這些小動物玩一會兒,如果能認領回去則更好。從早上到現在,禮物收得不少,但很少有人會在救助站待超過半小時,因爲實在是太吵了。好在已經有兩隻狗一隻貓被收養,這讓柳絮覺得費心組織這場活動還算值得。
一個矮胖的男人推門進來,初秋漂亮的陽光在玻璃門上一閃,照得柳絮偏過頭去。大金毛在第一時間撲到他身上。他倒不怕,拍拍狗腦袋要推開,但金毛死抱着他大腿不松爪。他問柳絮可不可以直接給它們喫,然後從塑料袋裏拿出七八根豬大骨往旁邊一扔,所有的狗都衝了過去。他抬起頭,對柳絮笑笑,說我們有四年沒見了吧。
柳絮剛纔就覺得似曾相識,但她被貓狗們弄得腦仁發漲,一時間反應不過來。
「我是郭慨。」
爭搶肉骨頭的時候,狗叫聲反倒輕了一些。柳絮聽了個大概,她往前走了兩步,好聽得清楚些,然後她忽然反應了過來,這竟是郭慨。
郭慨原本是個精瘦的人,現在看起來比從前胖了至少三十斤,整體形象全不一樣了。
「你怎麼會來這裏?」
「前幾天,局裏新來個同事。」郭慨起了個頭便停下來,看着柳絮。
兩個人之間陷入短暫的沉默,貓和狗在旁邊吵個不停,但有一瞬間,他們都感覺到了異樣的安靜。
「她也叫柳絮,和你的名字一模一樣。」郭慨說,「我忽然就想來看看你最近怎麼樣,在網上一搜,就看見了你搞的這個活動。你好嗎?」
「還好,挺好的。」柳絮想起從前自己很不愛看見郭慨,但四年沒有見面,再見時那些情緒都沒有了。時光的沙漏裏,已經落下去的沙子飛舞起來,閃起舊日的光芒,彷彿要再回到上層似的。
柳絮向同伴打了個招呼,就和郭慨一起在附近找了個咖啡館坐下說話。
「你變了很多。」
「是說我胖嗎?這些年喫得多動得少。你倒是一點都沒變。」
柳絮笑笑,沒變嗎?快三十的人,哪能沒變?郭慨現在說起客氣話倒是自然多了,全不像當年的生澀少年。時間之下,沒有人能不變。
「當刑警不是應該很累的嗎,怎麼會胖?難道你升職成領導了?」柳絮開了個玩笑。
「啊,不再是刑警了。」郭慨停頓了一下,展開緬懷的笑容,像是對舊日理想的致意,「你婚禮那一次,喝成急性肝損傷,就不能太累了,領導考慮我已經不適合刑偵崗位,調離了。」
柳絮覺得很尷尬。她知道郭慨那次被送進了醫院,沒料到情況這麼嚴重。
喝酒致急性肝損傷並不常見,但一發生就無可挽回,對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來說,幾乎就是半殘了。
「啊,我不知道後來居然這樣,真的是……那你現在做哪方面的工作?」
「戶籍警,家那兒的派出所,方便,走路上下班。每天走這家串那家,都是幾十年的老鄰居,哈哈。輕鬆得很。」
郭慨語氣溫和,他現在整個人的氣質都是和和氣氣的,活脫脫一副老好人的模樣,做戶籍警真是再合適不過。但柳絮心裏卻一陣悸動,她不由得想起了從前的那個郭慨,那個小時候在馬路上攔車嚇她的郭慨,那個在弄堂裏呼嘯着幹架的郭慨,那個戴着警帽在病牀前打拳的郭慨。那是另一個郭慨,另一個人。因爲肝損傷,他不能成爲一直以來的那個人了。小時候她覺得讀書最要緊,瞧不上郭慨這樣的壞孩子,現在年歲漸長,卻不這麼想了。關鍵是郭慨那天爲什麼會喝那麼多酒,柳絮心裏明鏡似的。
我就是個掃把星啊,和我沾上的人都不妙。柳絮這樣想的時候,露出勉強的笑容,笨拙地想要換個話題,便問:「你結婚了嗎?」
這話一問出口她就後悔了,她在心裏指望着郭慨能說自己已經結婚了,或者有個穩定的照顧他的女朋友。
「沒,一直單着呢。」郭慨說。
自己真是蠢,柳絮想。
「你呢,這幾年還好嗎?」郭慨幫她岔開了話題,他體諒得全然不似記憶中的他,這更叫柳絮不好受。
於是柳絮開始努力地聊自己。聊她這些年做的公益,除了流浪貓狗的工作,還去貧困山區支過教;聊她每天早上一小時的跑步和每週三次的健身房運動;聊她對心理學的興趣並準備報班考一個心理諮詢師執照;聊她作爲一個全職太太的幸福感。
郭慨一開始笑呵呵聽着,但慢慢地,一些細微的小動作讓柳絮感覺到他有些不自在,好像有什麼事讓他待不住似的。於是柳絮說自己該回去了,她是活動的發起人,離開太久不好,以後常聯繫。郭慨說好。
柳絮上完洗手間回來,郭慨已經把賬結了。他坐在那兒看她,眼神有些複雜。柳絮等着他一同出門互道珍重,郭慨慢慢站起來,猶猶豫豫地問了一句。
「你……還好嗎?」
在救助站裏重逢時郭慨就問了聲「你好嗎」,剛纔也問過這幾年好不好,現在他又問了第三次。
當然,我很好,前面不是都聊過了嗎?柳絮這樣想着,也準備這樣回答。可是忽然之間,那些話噎在喉中,吐不出來。
「你的黑眼圈很重。你真的還好嗎?」
「我有些失眠。」柳絮說。她開始閃躲郭慨的眼神,但終究還是要碰上,彷彿被一道光照進心裏,但一點都不亮堂,反有種被灼傷的痛苦。
「有點失眠。」她又喃喃重複了一句。但爲什麼失眠呢?該怎麼說呢?神經衰弱嗎?爲什麼會神經衰弱呢?都過得這麼幸福了,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呢?她說得出口嗎?
「你有事情憋着啊。」郭慨指指她的心口。
柳絮被他這麼一指,許許多多的東西剋制不住地從心底裏翻起來。她心裏叫着糟糕糟糕,但眼淚已經止不住地流了下來。她慢慢地坐回到椅子上,自己卻根本沒有留意到這點。
「我有過一個孩子。」柳絮說,「沒人知道,其實我在婚禮那天喝了酒。是我殺了她,這是我的報應。」
她開始談這個孩子的事,開始懺悔,這件事已經在她心裏憋了很久,連費志剛也不知道婚禮時她喝過酒。而在那之後,她再也沒有能懷上過。
郭慨只是在旁邊聽着,他知道柳絮只是需要一個樹洞說說話。等柳絮停下來的時候,臉上的眼淚已經幹了。
「現在感覺好多了?」郭慨問。
「謝謝你。」柳絮說,「你真是個好人。」
郭慨苦笑:「你從前可不是這麼覺得的吧。」
「但你是怎麼看出我不開心的,有那麼明顯嗎?」
「你先前說的那些,公益、運動、心理學,這麼多能調節心情的事情,你每一樣都那麼拼命去做,太辛苦了。我終歸做過刑警,基本素養還剩下一點。」
柳絮沉默了一會兒,說:「其實這些年我過得很糟糕,並不僅僅因爲那個孩子。我以爲辭了職待在家裏,一切會慢慢變好,時間會把記憶帶走,把她帶走。你知道那時我爲什麼辭職嗎?」
「聽說……是出了醫療事故,因爲暈血?」
柳絮搖搖頭:「記得我讀大學三年級的時候,摔進屍池住院,你來看我的事嗎?」
「當然記得。」
又是長長的沉默。然而她終於下定了決心。那陰影一步步迫近,就快要把她吞噬。做錯了事就要付出代價,但這代價實在太過沉重,四年前的醫療事故是報應,和父親決裂是報應,小孩流產也是報應,柳絮甚至有預感,她這一輩子都不會再有孩子了,自己這樣一個坐視好友被毒殺的人,是不配當母親的。然而她終究是渴望有一個人能安慰自己的,在心底裏,柳絮隱約曉得,對面這個男人,大概是除了母親之外,唯一一個在知曉了全部事情之後,不會指責她的人。
「那時我應該對你說的。如果說了,事情應該會不同。」
於是柳絮開始說文秀娟的事。她打開了那個閥門,陰寒的氣息從心底的黑洞中吹出來,讓她一陣一陣地發冷,說到後來,整個人都發起抖來。
她的神情讓郭慨爲她擔心,他握住她的手,那手冷得像冰,讓他覺得自己無法溫暖她。
柳絮的手被包裹住的時候,心頭跳了一下,她知道郭慨並沒有別的意思,甚至她覺得手被這樣握住,心裏多少安定了一些。
但這總歸不合適。
可是抽出來又顯得不禮貌了,或許再稍稍停留一會兒。她有多長時間沒感覺到安定了,哪怕只有一絲一毫,這讓她有些依戀。柳絮想到了費志剛,臉燒起來,這是因爲自己最大的祕密被他知道了纔會有的特殊情緒吧,並不意味着別的,只是情緒宣泄後的副作用,柳絮用她僅有的一點點心理學知識胡亂分析着。
郭慨鬆開了手。
「交給我吧。」他說。
「啊?」
「我來查。」
柳絮嚇了一跳。她只是傾訴一下,但郭慨居然……她忽然意識到,這就是郭慨啊,他還是那個人。
「可是事情已經過去那麼多年。」
「還在刑事追溯期內。有機會的,至少,嫌疑人的範圍就這麼大,我一定能把他抓出來。柳絮,你的病根在那兒,如果不去管它,你一輩子都不會開心的,得把這根刺拔掉纔行。給你朋友一個交代,也給你自己一個交代。」
柳絮傻傻地瞧着郭慨,又有些想哭。當年如果告訴他,該有多好,她再一次這樣想。那時候,自己真是太小了。
郭慨衝她笑笑:「感動個啥,別瞧我說得好聽,其實你知道我這幾年戶籍警當得有多無聊嗎?醜話說在前頭,我只能業餘去查,進程不會太快,你呢也彆着急。這樣,我們每星期碰個頭,我向你彙報進展。」
柳絮還能說什麼,只有點頭。
接下來郭慨詳問了當年的諸多細節,記在隨身的小本子上,直到天色暗下來,才道別離開。
臨走,已經走到了店門外,郭慨對柳絮說,其實這些年我常去你家的。柳絮嗯了一聲。郭慨又說,你爸爸他年紀大了,背也駝了。柳絮不說話。最後郭慨說,其實你結婚那天,我和你爸一起去的,只是他沒進酒店,就站在對面馬路那兒看着。柳絮怔怔出了會兒神,然後嘆了口氣。
柳絮醒來的時候,看見文秀娟在旁邊專心地瞧着她,烏黑的長髮蔓延過兩隻枕頭間的空隙。
你去圖書館嗎?柳絮問。
哦對了,你已經死了。
能告訴我是誰殺了你嗎?
哦對了,你也不知道。
長髮漸枯。
柳絮忽地又看不見文秀娟的臉了,她好似並沒在看着她,而是把頭埋在枕頭裏。
她緩緩抬起臉。
柳絮醒了。
旁邊沒有人,柳絮盯着枕頭,上面也無印痕。原來費志剛昨晚沒回家。她拿過牀頭的手機,上面有一條未讀短信。
「今晚不回來。」
沒寫理由,但總歸是病人的事情。
這些年費志剛進步很快,三年前就轉爲主治醫師,上個月則升爲副主任醫師,並且已經是上海心胸外科學術委員會的青年委員,在國際一線的醫學雜誌上陸續發表了三篇論文,儼然醫學新星。代價則是平均每週兩個晚上回不了家。
兩年前費志剛貸款買了這套房子,裏面從傢俱到軟裝,每一樣都是柳絮親手購置。可每次睜開眼睛,柳絮依然覺得陌生。家是陌生的,世界也是陌生的,所有的東西和她之間都隔着層膜,費志剛也不例外。好像自從和父親鬧翻,搬出家去,這世上就已經沒有了她的家,她成了遊客,成了陌生人。倒是有時候看見文秀娟,在恐懼噴湧出來的前一秒鐘裏,會覺得自然,覺得觸手可及。這種和死亡的親切感時時讓她後怕。她知道自己的精神不正常,就像昨天郭慨說的,病根不除,源頭不清,她的問題就會越來越嚴重,終有一天掩飾不住。
回想昨天和郭慨重逢,竟覺熟悉親切和一份踏實。大約是朋友實在太少的原因吧,柳絮想。然後她一轉念,又覺得,是自己從前太少不更事,郭慨這樣的男人,至少做朋友是很合適的。男女之間會有真正的友誼嗎?柳絮記起昨天郭慨出現時說的話,一個和她同名同姓的人,於是想着來看她一眼,看她好不好。她心中悸動,有股子過電的感覺。然後,她把一切都壓了下去。
費志剛是個好丈夫,柳絮告訴自己。大家都是這麼說的,他前途無量。
關於前途無量,其實也不僅僅是費志剛。
進入和生的九個人,全都是工作起來不管不顧的拼命三郎,副主任級的提了三個,其餘也快了。他們才三十歲,這速度簡直不可思議,但全都是實打實拼上來的,要實績有實績,要理論有理論。如今和生其他醫生,都已經開始用「委培系」來稱呼這九個人了。
如果文秀娟沒有死,那麼委培系就是十個人。不,加上柳絮,十一個人。當然,文秀娟一定是最傑出的那一個。
郭慨能找出那個人嗎?
柳絮忽然意識到自己在想文秀娟。這麼多年來,這是頭一次。她一次次地在夢裏見到文秀娟,有時也會在突如其來的淺夢——好吧,誠實一點,在那些輕度幻覺裏見到文秀娟,可是她一直都在逃,一直告訴自己一切都過去了,一切都無法挽回,不要再去想那個名字。
但她剛纔想到文秀娟了,無比自然。
是郭慨給了自己再度面對她的勇氣。
柳絮想起了和郭慨每週碰面的約定。在他的牽引下,她要再度回到九年前了,回到那個七人寢室裏,回到那張先是清秀繼而浮腫的面目之前。許許多多的往事在這一刻翻滾起來,之前的幾年裏,文秀娟是柳絮的夢魘,而現在,她回覆成了最初的那個人,那個謙遜溫婉的聰慧女子,讓柳絮交心又仰視的密友。
因爲自己的過錯,竟然在回憶裏將她污成了猙獰的妖魔。
柳絮赤足在窗前站了很久,終於長長嘆了口氣。然後她趿上拖鞋,轉身走出臥室,來到客廳的茶几前。
茶几上放着個盛糖果的茶盤,還有兩本雜誌。柳絮把它們擱到地上,掀開下面的藍紋印花粗布。這是個古舊的大皮箱子,有幾十年歲數了,柳絮從古舊傢俱店裏把它淘來,擺在客廳裏當茶几。
柳絮單膝跪在地上,抽出銅插銷翻開鎖釦,扶住箱蓋兩端,向上一提,翻開了蓋子。
裏面是些平日裏用不着,又捨不得丟掉的東西。撥開布偶、老式相機和一些卡帶,柳絮從底下抽出根棗紅色的長條皮套。她把箱子恢復成茶几,坐在沙發上,把皮套端在眼前。
已經不是記憶裏的模樣了,紅不再鮮豔,皮也沒了光澤,不知道里面的那管簫,是否也和這皮殼一樣老去。大約,早已經跟着主人一起死掉,沒有當年的魂靈了吧。
文秀娟死前留了口信,說把這管簫給她。文秀娟的父親來寢室整理遺物的時候,把簫交在她手上,但這麼多年來,柳絮從來都把它放在箱底下,甚至連皮套子都沒打開過。一直到今天,她纔有了正視的勇氣。
柳絮摩挲了一陣,把皮套打開,將簫取出。
簫未老,色青黃,如昨日。
昨日似可追。
柳絮將簫放在嘴邊,手指隨意按住兩個孔,提氣一吹。文秀娟曾經教過柳絮吹簫,但柳絮氣息不夠,憋得臉紅耳赤也不成調,想起來,那情形就在眼前。
沒有吹響。柳絮又試了一次,發現不是氣息的問題。簫堵了。她把簫豎着拿在眼前,望進中空的竹管子。裏頭塞滿了細細捲起來的紙。
她的心跳了起來。
這是文秀娟寫給她的信嗎?
如果不是因爲害怕,早在九年之前,她就該發現的。
柳絮去廚房拿了根筷子,把塞在裏面的紙捅了出來。
紙微脆,她慢慢展開。
她一張一張地看,看得手足冰涼、血液凍結。
的確是信,卻不是寫給她的,也不是文秀娟寫的。
這是兩個謀殺者之間的通信!
你一定很驚訝吧,我也是。很高興能與你通信。我是鼓起了很大勇氣的,請你別有不必要的顧慮。當我意識到你的存在時,特別高興,這也算是志同道合吧,雖然我們正在做的事情危險且不合法律。但不管怎麼樣,她該當受到報應,否則太不公平!
我以這樣的方式來作自我介紹。文秀娟現在正在醫院裏,你一定以爲這是一場意外,因爲這一次你並沒有動手。現在我告知你,這並非意外,而是我一手造成。當然,這只是一次教訓,我並不指望能把她怎麼樣,她總是能被救回來並再次回到我們中間的,時間甚至不會很久。但這是個開始,我加入進來了,未來還長得很,我打算和你一樣慢慢來。至於我真正的身份,我想你也不會輕易探究,就像我不會那麼冒失地詢問你的名字一樣。反正我們每天都會見面,會打招呼,都是這委培班裏的一員。
……
你不需要知道我的辦法。你這次的手段愚蠢又沒意義,別自己被抓住還拖累我。醫學院學生想不出好辦法?專業這麼差,下一個被甄別掉的一定就是你!
文秀娟日子不多了。有沒有你都一樣。
謝謝你回應我。很高興,真心的。
接受你的批評,但事實上,我已經有一個計劃的雛形了,還需要完善。在沒能想明白之前,我不會再動手。你一定用了某種近乎完美的手段,我根據文秀娟表現出的症狀查閱了許多資料,卻無法判斷你用的方式。這讓我有點崇拜你了。
想和你說點心裏話,希望你別覺得我太囉嗦。有些話沒有第二個人可以說。
每一次看見文秀娟,我都越發地感覺她的討厭,很多時候我幾乎無法掩飾自己的情緒,而那樣的時刻,我會想自己會否過於極端了呢。不過我倒很難想象,居然有一個人,比我更加地恨她。
……
十六頁信紙,十四封信。
信在兩張方桌併攏的木檯面上擺了兩排,上排八封信下排六封,分屬兩人。這是兩個彼此並不知道對方真實身份的謀殺者之間的通信,在最後一封信之前,他們一邊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自己身份的祕密,一邊共同商量,該怎麼給文秀娟下毒,宛如一場接力,文秀娟就是他們手中的接力棒,直到把文秀娟的性命送上終點。
信紙薄而脆,一封封都卷着,無法展平,彷彿承載不住上面的罪惡。
如果說之前郭慨對柳絮的故事多少還有些未表現出的疑慮的話,那麼十四封信攤在面前,足以讓他明白,九年前醫學院裏的那段過往,遠比柳絮昨天所說的更陰冷惡毒。
郭慨並沒有說「學校裏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或者「竟然有兩個下毒者」之類的話,他長久不語。柳絮也沒有話,從早上發現這些信開始,同學的一張張面孔就走馬燈一樣在腦子裏輪轉。起初,不論是誰,她都覺得不敢相信,現在,哪一張面孔,都陰惻惻地似笑非笑。
郭慨先是坐直了身子,遠遠地端詳着兩個謀殺者之間的通信,後來他慢慢彎下腰,湊近了一些。但他的手一直沒再碰它們。忽然,他動了一下,彷彿從某種情境裏掙脫了出來。
「這些信一會兒給我複印一下。」他說。
「好的。」
「她是個怎樣的人呢,文秀娟?」
「她是個非常優秀的人,學習好人也好,有一股子寧靜的氣質……」
「不。」郭慨搖搖頭,「這些你昨天都說過,但是,她應該不僅僅是你說的那樣。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更何況是謀殺。而現在,有兩個不約而同的謀殺者。」
「不是的,你沒有見過她,你不知道,她真的是個完美的女人。」
柳絮開始講述文秀娟的好,儘可能地把那個心底裏完美無缺的形象傳遞給郭慨。然而她翻來覆去都是些主觀形容,記憶裏的細節模糊了,她很難講清楚是些怎樣的行爲把文秀娟在她心中的地位堆砌得如此崇高。或許有些皮毛的東西,比如口氣、笑容和恩惠,當年覺得是實實在在折射出個人品質的,現在拿出來說,又覺得淺了。
柳絮終於停下來。她低頭去看那些信,說:「我不知道這兩個人爲什麼那麼恨她。我能感覺到,班裏有很多人都不太喜歡她,我不知道爲什麼,我覺得以她的爲人處世這很沒道理。」
柳絮忽然嘆了口氣。
「我其實並不算了解她。」她說。
「之後那些年幾乎沒人談論她,只零零星星聽見過幾嘴,一隻手都數得出來。也難怪,出了那事情,大家都不想再提起了。這對我再好不過,那時我的狀態,是隻要和她有關的東西都不去聽不去想,遠遠逃開。所以說起來,我也只和她相處了幾個月,看到的是那幾個月裏她的狀態。我的確算不上很瞭解她。」
郭慨點點頭,說:「也許你的好朋友並沒有你想的那麼完美,沒人是完美的,是人就會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可不管有怎樣的缺點,發生在她身上的事都太可怕了,我一定要把殺人的傢伙抓出來。」
「那這些信,你看出什麼線索來了嗎?」
「有很多,但現在都是亂麻,頭緒要一點點理。」郭慨搖了搖頭,似乎就想到此爲止,隨即反應過來,衝柳絮抱歉一笑。
「哦對不起,搞得我像是還在刑隊查案似的。沒什麼好保密的,我就把我看到的說說,你也參詳參詳。比如說呢……」
郭慨用手指指信件:「這些都不是原件。」
「你是說這是手抄的,文秀娟抄的嗎?但不是她的筆跡啊。」
「不,我說的是上面這排。你注意到了嗎?紙上那些藍色的印跡。」
柳絮取了封信細看。上下兩排信用的紙張都是一模一樣的,是有醫學院抬頭的信紙,學校的小賣部可以買到,基本上每個學生都會用,在課桌裏也時常可以撿到,所以從紙張的出處上是查不出線索的。但經郭慨這麼一提醒,果然發覺紙上有薄薄一層藍色,粗看像是紙張本身的花紋,甚而不注意都發現不了,但細瞧的話,可以看出是後來染上的。並不僅這一封,第一排所有八封信或多或少都有這樣的藍痕,而第二排「另一個同學」的信紙上就沒有這種現象。
這藍痕讓柳絮有些熟悉,但一下子還抓不住重點,既然郭慨指出來,想必是已經知曉了究竟,柳絮就直接開口問他這是什麼。
「是藍印紙。」
柳絮一下子明白過來。這種用來複寫的紙在八九十年代是再常見不過的辦公用具,但近幾年不太見到,所以她才反應得慢了。
「所以這是複寫件,並非原信。但爲什麼會是複寫件,原信去了哪裏,這就不知道了。」
「如果這就是原信呢,我是說,也許寄出的就是複寫件。」
郭慨眉頭一挑,略顯意外地瞧了柳絮一眼,說:「倒也有這種可能,你的思路還挺合適搞偵破的。這樣說的話,寄複寫件也是有好處的,隔了一層,判斷筆跡會稍困難些,因爲有更多幹擾的因素。如果真是這個原因,寫信的人心思是很細了。」
他撓了撓頭,又說:「但也只是稍困難些,其實並沒有特別大的差別。我相信這兩個人用的都不會是慣常的筆跡,你看這些字都寫得很彆扭,如果說要再加上一層雙保險的話,嗯,聊勝於無。」
郭慨看起來對柳絮的這個推測持懷疑態度,但一時之間,他也想不到合理的解釋。
「文秀娟會有這些信就很奇怪了,無論如何她都不該有這些信的。即便她通過某種目前我們無法想到的方式,得到了這些信,那爲什麼她還是被毒死了呢?信是藏在特意留給你的遺物中的,如果她希望你能找出真相,那麼無疑這已經是她能掌握的全部線索了,這意味着她雖然得到了這些信,卻並不知道寫信人的真實身份。」
郭慨又搖了搖頭。
「想不通啊。難道說這信已經被調包了,並不是文秀娟留給你的。也許她僅僅只留給了你一支簫,也許她留在簫裏的是其他線索,被先取走了,換了這些信來誤導你。可如果是這樣的話,動機又很難解釋,爲什麼要多費這麼一番周折,讓事情儘快平息下去不是最好的嗎?除非你被誤導之後,會做出什麼兇手樂於看見的事情。」
柳絮搖頭說:「我覺得我什麼都不會做。我被徹底嚇怕了,我就是個膽小鬼。如果我在當年就看到了這些信,甚至都不會報警。」
「那麼這又是一個現在解不開的線頭。不過沒關係,一開始總是這樣,慢慢地線頭總會解開。你看,這才一天,就有了這樣大的進展。」郭慨衝柳絮笑笑,他知道自己這些年臉圓了許多,都說他笑起來能讓人安定下來,調解家庭矛盾的效率特別高。
柳絮卻覺得這笑容是一種溫柔。她不知道溫柔是笑容裏本來就藏着的,還是她自己附加上去的。
「這信裏有很多疑點,比如對兩個彼此不知身份的人來說,最初的通信是怎麼發生的,發信人把第一封信放在了哪裏,才讓第二個人收到。但在疑點之外,也有許多值得分析的地方。第一封信發出是在什麼時間點,最後一封又是在什麼時間,這在信中雖然沒有明示,卻提到了一些有明確時間標識的事件。第一封信裏提到文秀娟因爲一件看似意外的事情而住院,你還記得這件事嗎?」
柳絮當然記得。關於文秀娟的一切,在她刻意的忘卻中越來越清晰。而她對時間的特殊記憶力,讓那個日子立刻在腦海中跳出來。
那是週二。
1997年11月11日,週二。沒下雨。文秀娟趁着午休時間去做了一次靜脈給藥的藥試,下午去抽第二管血的時候出現噁心,隨即就嘔吐,立刻去醫院,住了兩天才緩過來.說是藥物過敏反應。留院觀察一天後,週四文秀娟回校正常上課。藥試中這樣的事情偶有發生,並不算罕見。然而,就第一封信的內容來看,這竟是一次蓄意的投毒。
柳絮自己沒做過藥試,所以具體怎樣的流程,其中有哪些環節存在漏洞容易被人利用,這些都說不清楚,只能有賴於郭慨自去調查,看能否在九年後查到線索。這自然是極不容易的事,但郭慨提問的重點,在於確認了第一封信寫就併發出的時間,就在1997年11月11日、12日這兩天裏。另一個座標,在第七封信裏。這封信裏提到了那瓶有針孔的礦泉水,正是從那天開始,柳絮完全介入到了這場毒殺案中,這一天,是1997年的11月26日。
第三個座標,在第九封信裏。這封信中提到了柳絮在進行的調查,那場短暫的調查一共只持續了三天,在第三天的晚上,柳絮跌入屍池。這封信中說柳絮已經和好幾人談過話,那麼應該是調查第二天寫的,也就是12月2日。也可能是第三天。
最初兩週的時間裏通了七封信,平均兩天一封。第八、第九封信要長一些,三到四天一封。第十封信很可能是柳絮出事後當天寫的,第十一封中,以肯定的口氣提到了柳絮的「吸取教訓」,那就應該是柳絮精神穩定了一段時間後,仍沒有表現出任何要追查的意圖時才能下的結論,以此來看,至少是住院三五天後。
兩個謀殺者在十幾封信的試探之後,終於決定見面,他們在最後一封信裏說定了碰面地點,就這樣結束了這場罪惡的通信。在兩個謀殺者碰面後不久,文秀娟就死了。見面的時間是「本週三」,爲了給取信留出時間,穩妥的投信時間應該在週日或週一。結合之前的信件往返時間,兩個謀殺者會面的這個週三,不是12月17日,就是12月24日,不會更早或更晚。文秀娟死於27日。
這兩個時間點,從過往通信頻率算,似乎24日更可能,但郭慨卻傾向於17日。
「如果是24日的話,也許在信裏會註明聖誕夜。」郭慨說,「當然這也作不得準,最主要的,是從之前的通信看,主要下毒者是第二封信的作者,我們叫他案犯B,他採用的投毒方式是多次的小劑量投毒,而案犯A則像是B的崇拜者,兩個人碰頭之後,應該不會改變這個投毒方針。而文秀娟是12月26日在解剖課上倒下,27日死亡,如果兩人24日晚上才接上頭,留給他們的磨合時間似乎略少。當然,毒性累積後的突然爆發可以在任何時間,但我還是覺得,17日夜裏碰頭,在接下來的九天裏兩人合作多次下毒,使文秀娟在26日毒發,這樣的可能性更大。」
「17號,那是我出院的日子。」
在她出院的當晚,兩個謀殺者見了面。這個時間讓柳絮覺得,這世界的運轉,有着一種讓她冰寒徹骨的規律。
「17號和24號這兩個晚上,有誰是和你在一起的?」
「24號聖誕夜,費志剛和我看完電影后就回去看他生病的媽媽了,至於其他人,全過聖誕去了,到很晚纔回宿舍的。對了,我看見文秀娟了,她從松樹林裏跑出來,當時臉色很差。最後一封信的見面地點就在松樹林裏,難道說她看見那兩個投毒的人了?所以兩天後她就被毒死了?」
郭慨搖搖頭:「還是那個老問題,如果她知道了誰是投毒者,爲什麼不報警?至少她也可以報告給學校。那麼,17號呢?」
「我是下午出院的,先回家裏住了一晚,直到第二天中午纔去的學校。」郭慨嘆了口氣,本想用排除法縮小嫌疑人範圍,沒想到連一個都排除不掉。不過,確定了這些信件的大概時間線,等於有了座標,總有需要對照的時候。
「但17號晚上我和費志剛打了很長時間電話。肯定打到了9點多,有可能超過9點半。」柳絮說,「當然了,文秀娟早就說過了不可能是費志剛。我和他生活了那麼多年,他是清白的。」
郭慨點點頭,想說什麼又咽回去。
「你是覺得他有嫌疑?」柳絮有些訝異地問。
「總是有的人嫌疑大,有的人嫌疑小。你先生肯定是嫌疑最小的。但是從偵破角度說,是不是就完全排除了,我還不敢說。文秀娟這個受害人的話,未必就是正確的,因爲現在不知道她是出於什麼原因下這樣的判斷。倒是你說他和你打電話到很晚,這條更有力。但時隔多年,記憶上也許有誤差。又或者我的判斷有誤,其實見面是24號晚。我這樣說,你一定會不開心,但我的建議是,沒有調查清楚前,同學裏你誰都別信。」
柳絮沉默。
「你和你先生說過,你要調查文秀娟的死因嗎?」
柳絮搖搖頭。
「那最好就別說了,我們單線聯繫。這倒不是說防他是兇手,但每個人都有特別信任的人。你特別信任他,他也肯定有特別信任的某幾個同學。如果最終兇手知道了你在調查他的話,你會有危險的。」
「我知道了。」
郭慨看着柳絮。說實話他有些擔心,並且懷疑自己重新調查這件事,到底是否明智。原本覺得查明真相,會對柳絮的精神狀態有所幫助。但整件事慢慢展開,卻變成了一個旋渦,讓人漸漸要站不住腳。柳絮現在所承受的心理壓力,明顯要比之前更重了。
郭慨看了看錶,下午2點20分。上午柳絮給她打電話,電話裏沒說具體的事情,只說有非常重要的線索,一定要趕快見面。原本打算出來個把小時就回去的,現在麼……郭慨打了兩個電話,安排了工作上的事,讓自己可以在外面多待些時候。他覺得自己需要和柳絮多處會兒,倒不爲了分析信件,這方面柳絮幫不到他,無非他說她聽,而是柳絮現在得有個能說說話的人,討論討論,心理上有個支撐。否則一個人在家裏,對着這十四封信,難受。
接下來郭慨開始分析字跡。
「你看看這些信上的字。」郭慨指給柳絮看。
兩個人的字都不好看,一筆一畫的,全無架構可言。這說明他們都刻意不用自己原本的習慣寫字。
「案犯A的字還好些,你看B的字,有一個特點發現沒有,橫劃總是左高右低,收筆有時收不好,還有偶爾一行字會越寫越往右下方偏移,如果不是信紙每行有橫紋,相信最後一個特徵還會明顯很多。」
「這說明什麼?」柳絮問。
「最典型的左手非利手字。就是說寫信人慣用右手寫字,但故意用了左手,就出現這些特徵。這兩個人的信任是一點一點達成的,他們很清楚一旦被抓住會有什麼後果,所以開始接觸時小心翼翼,避免透露出能查到自己身份的任何信息。既然他們如此小心,那麼展現出來的身份信息,都有可能是誤導。比如案犯B說話簡單直接,可能只是因左手寫信不便故意如此,而他表現出的粗魯,更和一個醫學院學生的身份不符。你有哪一個同學平時說話,就是這麼粗魯的嗎?」
柳絮搖頭說沒有。
「這就對了,難道這個人平時都裝得斯斯文文,卻在這樣危險的通信裏把本性暴露出來嗎?當然不可能的,所以他在裝。裝字體,裝性格,那麼有沒有可能裝性別呢?」
「你是說,行文粗魯的那個是女的?」
「就下毒便利方面說,兩個都是女性的可能性最高,都是男性的可能性最低。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如果你照着信裏表現出的寫信人形象去在同學裏尋找,會誤入歧途。」
「啊,我還在根據信裏的性格在同學裏一個個猜呢。」
「按圖索驥在這裏是行不通的。身份信息不能相信,但是其他信息的可信度就要高很多。比如信裏關於毒物的描述,這很可能是真的。在第十二封信裏,案犯A說自己用的是一種不太方便下的毒,無法下在中草藥裏,說明不會是粉末顆粒的,多半是液態的。案犯B的毒就不同,成分穩定,不容易和其他毒相互作用,並且很可能就是粉末顆粒狀的。這個方面,你比較懂行,可以想一想有哪些毒符合。在你們學校容易獲取的毒,優先考慮。」
柳絮點點頭,說:「醫學院的學生,只要有心,能拿到的毒挺多的。其實只要有一些專業知識,從藥店裏也能買到。」
「也是,殺人和救人,要懂的東西是差不多的。」郭慨開了個玩笑,但柳絮並沒有接到,沉着臉看着這些信。
到了郭慨必須要走的時間,柳絮把攤在桌上的信一張一張地收起來。
她收得很慢,收幾張就停一停。
「別忘了這些給我複印一下,一會兒出去在附近找個地方。」郭慨說。
柳絮怔了一下,然後說「哦」。
「你在想什麼呢?」
柳絮加快速度把所有的信收好,摞齊,交到郭慨手上。郭慨發現她的眼眶有點紅。
「我在想,不管文秀娟是怎麼得來這些信件的,當她看到這些信時,是怎樣的心情啊?」
為什麼會看到廣告
留言0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