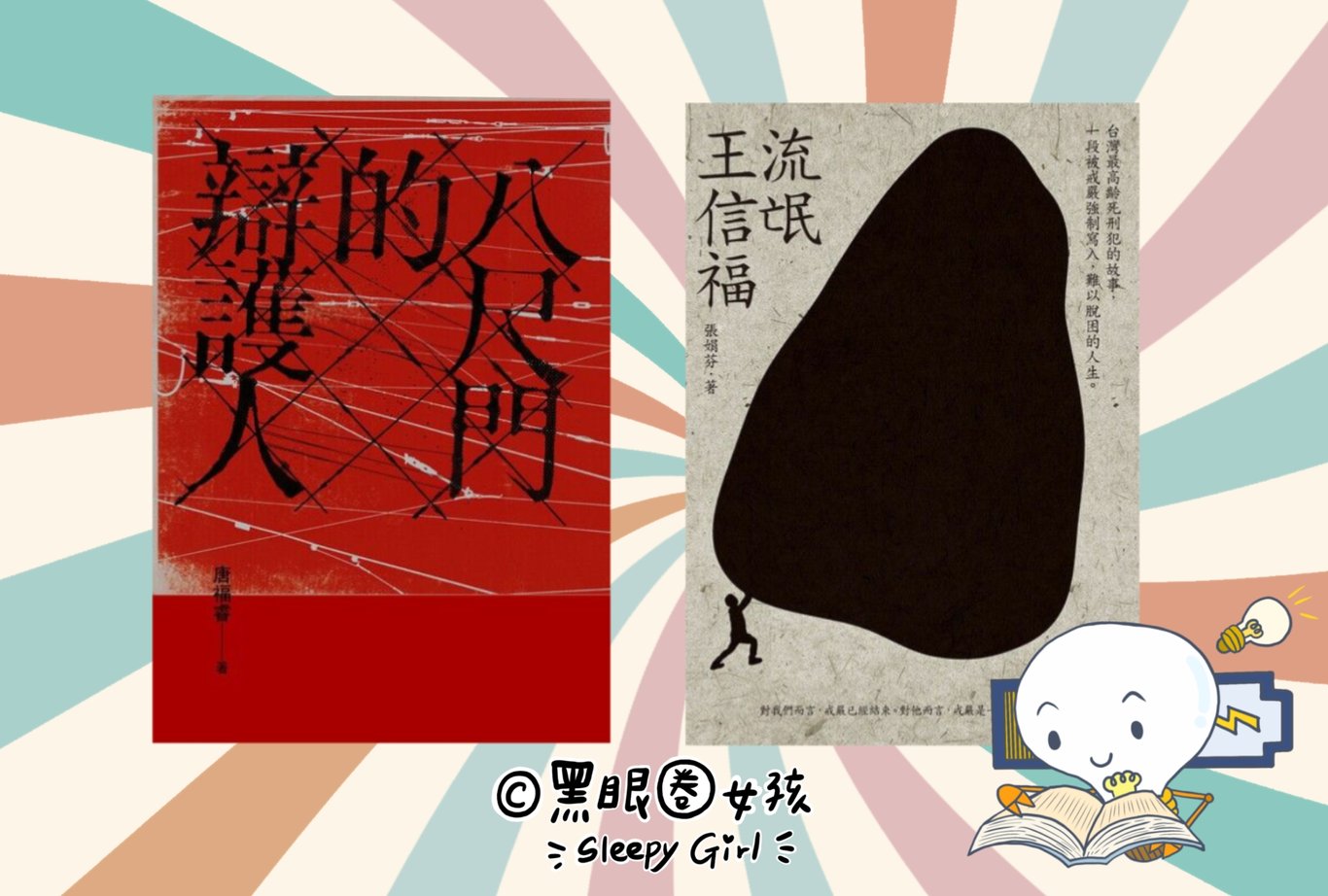2015年新雨出版社出版、紅色封面的《生死場》裡,收錄了蕭紅從1934年開始連載的中篇小說<生死場>、1935年所寫的四十一篇散文<商市街>,以及1933年發表的<棄兒>,書末另附蕭紅年表 。
<生死場>
什麼最痛苦,說不出的痛苦最痛苦。以東北農村為背景,從平時到戰時,道出窮困農村裡的人們如何為了生存受盡磨難。窮,讓人沒有尊嚴,而女人更甚。那個時代的男尊女卑,女人要點尊重都嫌貪心。蕭紅的筆下,訴盡女性的總總苦難、卑微、麻木與寂寥。
讀完<生死場>這篇,我深感挫折。
全篇沒有非常明確的主角,感覺是作者刻意模糊化故事裡的角色,帶出一種眾生皆苦的氛圍(?)。所以剛閱讀時就在辨別人物上遇到很大的障礙,老是分不清到底誰跟誰是什麼關係,只好打開手機做人物簡表。
釐清了人物關係後,我仍舊進不去蕭紅的敘事裡。主要原因在於文章裡的用字過於陌生,閱讀起來極卡,原以為慢慢熟悉用詞遣字後會漸入佳境,卻從頭到尾被文字絆住,閱讀節奏不順暢,每一段都要想一下或看個兩次,不斷停下來思考文字的意思,閱讀障礙發作導致情感投入受阻,所以進不去這個故事,也沒有情感上的代入。有種被擋在故事外圍看著那個時代的人們(女人)像在受罰般在底層掙扎,內容很悲戚,但我的情緒很淡然……。
我其實是超容易入戲的人,通常這類描寫底層社會小民苦難的內容都會讓我揪心不已,再加上後面的戰時背景,感受往往隨著堆疊而放大好幾倍。但是隨著故事推進到日軍侵入的後半段,我的內心仍平淡無波,自己都深感意外。
於是我得出了一個結論:不是故事不好,而是我個人對蕭紅的文字消化不良......。
(若不是共讀書目,恐怕早已棄書投降……)<商市街>
走吧!還是走,若生為流水一般的命運,為何又希求著安息!
一對愛意似乎不太對等的男女,在貧窮中挨餓受凍過著寂寞的日子。男的郎華無疑是蕭軍,女的悄吟便是蕭紅了。
在<商市街>一篇篇半自傳性的散文中,我終於走進了蕭紅的文字裡。
我感受著文字傳來陣陣刺骨的冷,天氣的冷,窮困的冷,飢腸轆轆的冷,愛情卑微的冷,寂寞的冷。當她說著冷,我也覺得寒了起來,當她說著餓,我也好像被感染了飢餓感,當她喊著痛,我都不禁蜷曲起身體,好像肚子劇痛的是我。
夜間,他睡覺醒也不醒轉來,我感到非常孤獨了!白晝使我對著一些家俱默坐 ,我雖生著嘴,也不言語;我雖生著腿,也不能走動;我雖生著手,而也沒有什麼做,和一個廢人一般,有多麼寂寞!連視線都被牆壁截止住,連看一看窗前的麻雀也不能夠,什麼也不能夠,玻璃生滿厚的和絨毛一般的霜雪。這就是「家」,沒有陽光,沒有暖,沒有聲,沒有色,寂寞的家,窮的家,不生毛草荒涼的廣場。
<商市街>裡寫著愛,卻也道盡孤獨。
渴望愛、為愛而生的蕭紅,依附在男性身邊做著浪費自己才華的瑣事。她那雪亮的眼睛又怎麼會看不清身邊男人的寒涼呢?從文裡也流露出對男性的不滿與怨懟,只可惜看得清不見得放得下,再加上經濟上的弱勢,更是強化不對等的關係,時常低姿態討好,處處委屈自己。苦苦追求的幾段感情,愛得荒腔走板,最終都沒能修成正果。歷經窮苦、病痛(分娩痛)與愛情的幻滅,仍是掙脫不了悲苦的宿命,年紀輕輕(才三十一歲呀)孤伶伶死去,也難怪會留下「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這樣悲憤的話了……
除了愛情,也從悄吟的視角帶出那個時代哈爾濱小民的生活、貧富差距、知識分子的熱誠、矛盾與時局動盪中的驚惶。
我格外喜歡<廣告員的夢想>、<同命運的小魚>、<春意掛上了樹梢>與<小偷、車夫和老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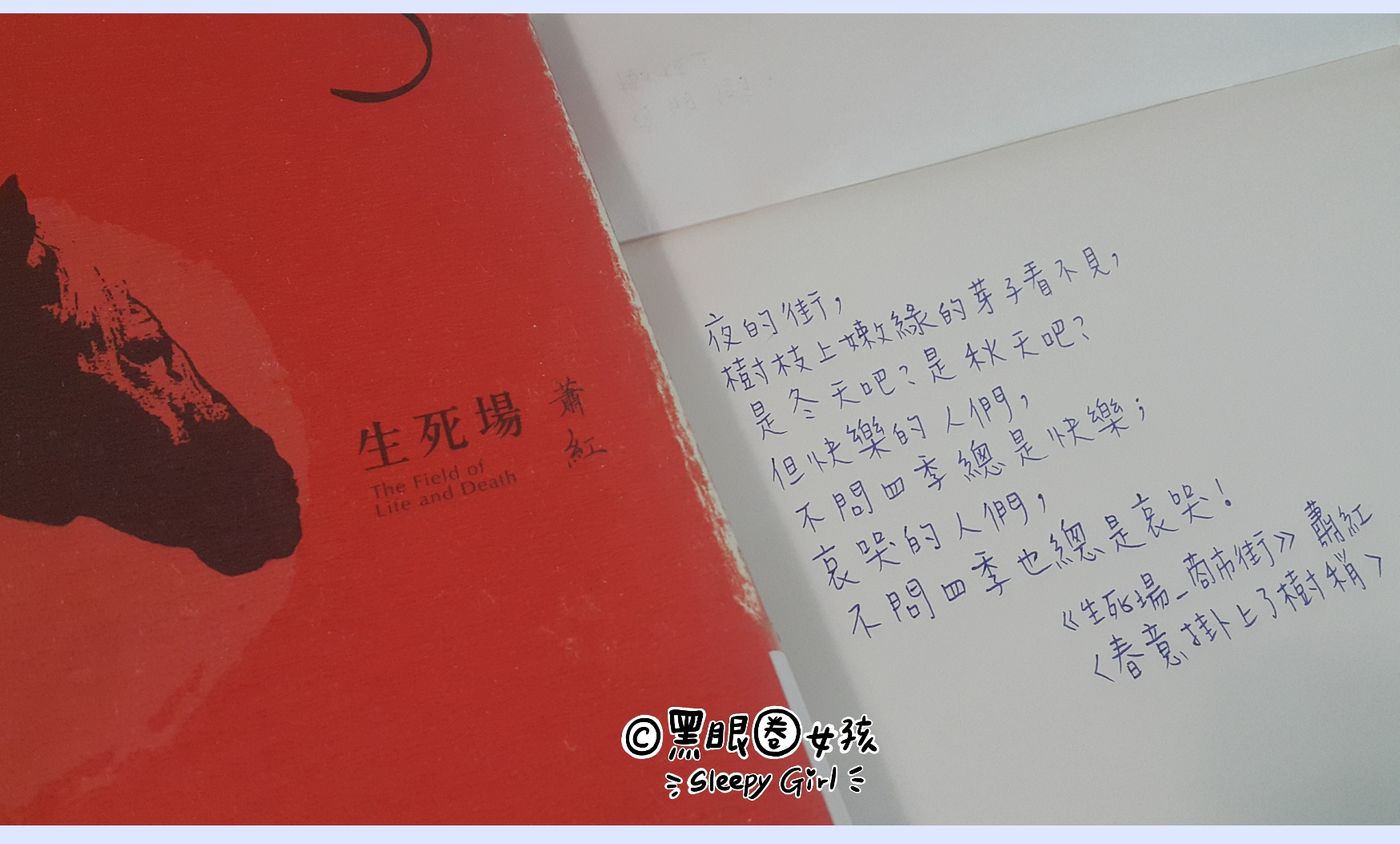
<棄兒>
今後將不再流淚了,不是我心中沒有悲哀,而是這狂妄的人間迷惘了我了。
身懷六甲的女子芹遭愛人棄於旅館,面臨旅館主人討要房費而付不出的窘境。松花江決堤後,投靠新識的愛人蓓力......(芹是蕭紅,始亂終棄的愛人是汪恩甲,蓓力便是蕭軍了。)
當生下不久的孩子往芹的方向推來時,她搖動著手說「不要!不......不要......我不要呀!」,後來又說「我捨得,小孩子沒有用處,你把她抱去吧。」
在了解蕭紅的生平後,我從原本的滿腹疑惑漸漸轉為理解。
未曾感受父愛母愛,一生渴愛追愛卻從未真正擁有愛,這樣的女人,要怎麼去擁抱新的小生命?(何況是拋棄她的男人之子)她的確不是符合社會期待的母親,卻是男尊女卑社會下極度缺愛的產物。
讀完全書後,我再回頭讀了一次<生死場>,不再受到文字所困,終於有了較深切的感受。
那個時代的窮困讓每個人都過得水深火熱,父權社會底下的女子更是「生,不如死」。從戲份較多的四對夫妻(二里半與麻面婆、王婆與趙三、福發與福發嬸、成業與金枝)相處的模式再再展露出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不堪。患了癱病的美人月英、服毒的王婆,男人的殘酷赤裸得難以直視,女人的淒慘境遇在我腦中揮之不去。
活著太難了,幾乎一腳踏進棺材裡的生產更加艱難。所以原本該是代表希望與喜悅的新生兒出生,卻成了絕望與磨難。無論是<生死場>還是<棄兒>,文中嬰兒的下場都很悲慘,不是意外摔死(王婆的孩子)就是被人為摔死(金枝的孩子),又或者出生不久便送人(芹的孩子)。
孩子可能是女人的索命咒,無疑是經濟負擔,也可能是開啟另一段生活的阻礙。貧窮,限縮了親情
貧窮,也讓人麻木而失了靈魂。<生死場>裡金枝的母親也說她愛著女兒呢,但拿心中那把秤惦了惦,作物的價值還是遠勝於女兒。所以手上握著女兒帶回來的鈔票時,讓她全然看不見眼前遭受欺辱、回來尋求慰藉的女兒的痛苦。蕭紅文裡的母愛成分極其稀薄。母愛,不是與生俱來的。
另外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便是蕭紅故事裡時常出現動物,像一種隱喻,如文中所說,「在鄉村,人和動物一樣忙著生,忙著死......」,無論是<生死場>裡認命滾壓麥穗的老馬、走進屠場的老馬,還是<商市街>裡同命運的小魚,都輕輕牽動著我的心。
半夜郎華起來看,說它一點也不動了,但是不怕,那一定是又在休息。我招呼郎華不要動它,小魚在養病,不要攪擾它。亮天看它還在休息,吃過早飯看它還在休息。又把飯粒丟到盆中。我的腳踏起地板來也放輕些,只怕把它驚醒,我說小魚是在睡覺。這睡覺就再沒有醒。我用報紙包它起來,魚鱗沁著血,一隻眼睛一定是在地板上掙跳時弄破的。就這樣吧,我送它到垃圾箱去。

<生死場>後半段加入了抗日主題,譜出大時代如泣如訴的哀歌,因而成為蕭紅的成名作。可惜,那些抗日橋段並未讓我有太多情感上的代入,反而是著眼於小人物如螻蟻般苟活的百態更打動我,而<商市街>與<棄兒>在女性身體與情感面的書寫也更具吸引力,也許是因為,裡面蘊含著蕭紅內心情感的投射。在二十幾歲就用盡全力去反抗、去愛,我一方面心疼、惋惜,一方面又佩服這個女子。
蕭紅說,「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簿的,而身邊的累贅又是笨重的!...不錯,我要飛,但同時覺得...會掉下來。」女性被時代折殘的翅膀,終是無力掙脫時代的牢籠。
(幸好是共讀書目,讓我沒有半途而廢,堅持讀完這本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