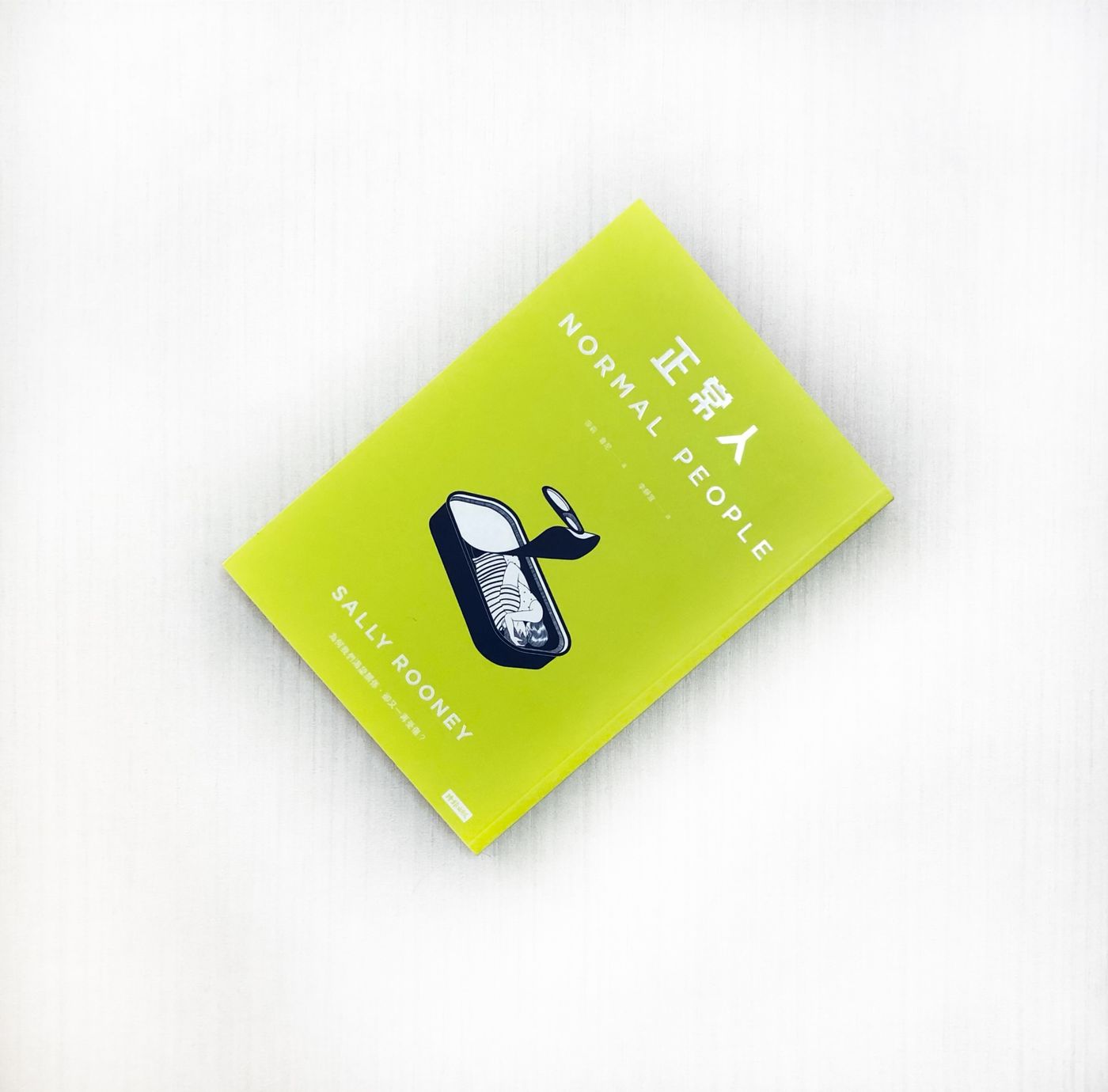二○二○年六月
「你應該去的,我永遠都在這裡,你知道的。」
女演員臉上帶著輕淺的笑容,看進對方深邃清澈的眼眸。影集在兩人對視的長鏡頭下走向結局,工作人員名單開始跑過轉黑的畫面。
通常這時,身為朋友口中的影癡應該習於拆解畫面配置、剖析角色內心,但是,一口氣看完影集的那天凌晨一點三十四分記憶猶新,我發覺自己遍尋不著適切的言詞形容眼底翻湧的心緒,似乎就連以毫不相干的觀者身分,試圖拆解任何一絲所謂「正常」的表象與關係,都顯得多餘。
不過,其實這個時間的我根本就不應該還醒著吧。
明明在不到一週之後,早已被強制喊卡的青春年歲,即將隨著死板制式的篩選落幕。畢業典禮的句號像個幌子,畢竟劃過紙面的紅筆還不停、堆疊的試卷與教科書也還無盡,追逐誰眼中的認同、還在嘗試理解自身的悲傷,之於關係樣貌的想像云云,在這段時日裡都被擱置一旁。夜晚將自己拋進影集與書頁的時刻,成為讓自己不被數字與光環綁架的浮木,也才能將這些旁人看來縹緲的渴盼,短暫封藏。
只是今晚,影集終幕的那段對視,似乎牽動了心中所有躁動的想望。
「讓思緒奔騰一晚也好。」
關於世代,關於社會,關於認可,關於那些脆弱與愛,所有強行封閉的迷茫與紛亂一次湧上——那會是我嚮往的模樣嗎?是什麼樣無聲無形的相擁,稱為純粹的愛情太過膚淺,卻同時解釋了一種超越一切友誼可以概括的關係?
這是我與《正常人》影集的初次相遇,在指考前一週渴望失眠的夜晚。

二個星期之後(二○二○年七月)
獨自走在臺北街頭,踏著慣性的步伐,出了捷運站五號出口右轉走兩分鐘,看見便利商店後就轉彎,再經過兩個路口——高中放學後最常造訪的獨立書店就在左手邊。踏進店裡,清脆的響鈴、熟悉的氣味伴隨記憶湧上,小小的書店乘載了高中時期還青澀的愁緒。總對世界抱有各式期待、無法理解外在,更無法理解情緒的小小的我一如既往坐在角落的木椅,從書頁中抬起頭看向我。
高一時的我不愛說話。過度天真地以為來到所謂明星學校,就能更輕巧地抓住人際間微妙的頻率平衡,而實驗結果不如預設,博取嬉鬧的距離或是掛上合宜的微笑從來不是解答。「今天放學要考完數學再回家喔。」於是學會和母親謊報返家時間,只為多在人車繁雜的臺北閒晃一陣,或到書店裡埋首文字,好像只有這樣,才能找回一點正常的樣子。
「例如他們不需要去假裝,只需要做好自己。我覺得我像是在到處嘗試,嘗試一百個不同版本的自己。」
康諾悄聲在小小的我耳邊這麼說。
「是啊,康諾。我們如何才能直面自己真實的模樣呢。」
初識彼此,康諾在梅黎安身上看見在彼此認知中相異的樣貌,而這種不同來自這樣私密、一來一往之間的觸發的動能。會不會性格的本質只是依附著際遇變動之下的結果,而理解從來不是,也不會是必然——但是在他們身上,理解卻變得純粹了啊。一邊思考著影集中主角的對白與情感的交織,我走向書店的文學小說區。
《正常人》擺在架上要說是十分顯眼,不如說是格格不入——就跟他們一樣——帶點黃色調的草綠,接近螢光色的書封在深藍書腰的對比之下,就連邊緣一行白色小字都清晰可見:「英國《衛報》:一部代表未來的經典。」明明是看過影集,在網路書店上早已瀏覽過數次的評價,真正捧在手上仍不住再讀過一遍:「西方文壇公認第一位足以代表二十一世紀未來的作家」、「《時代雜誌》次世代百大影響人物」。畢竟,是這樣的作者寫出了牽動、定義整個世代的文字,使那些在關係中歷盡孤獨的靈魂顫動共鳴啊。
書封兩具在罐頭裡擁抱的靈魂,許是為整段故事下了最貼近的註解。在這個世代,這樣的社會、所處的關係中,我們究竟是害怕面對世界,還是面對自己?一個個罐頭相似、制式、易於辨認,躲在空殼裡的靈魂究竟是壓抑、疏離還是逃避?康諾與梅黎安有各自的脆弱掙扎,在狹小的時空捍衛情緒的波瀾、遍尋一種理解的方式,嘗試削去稜角符合常態的規準……,最終發現看進一個人的眼眸也許並非無比偉大或遙遠,一次相擁就足夠拯救。如同久別重逢,梅黎安在舉辦喪禮的教堂擁抱潰堤的康諾,那樣的無聲療癒。
買了《正常人》和一本在二手書區翻找到的絕版詩集。
「妹妹,妳不一樣了喔。」
臨走前推開書店的玻璃門,從高一到現在除了結帳之外,不曾和我說超過十句話的老闆,她這麼對我說。

四個月後(二○二○年十一月)
步入新的階段已經跨越一個季節,生活約莫也是如此,夏季的躁動不安、繁茂生長的樣態來到飽和轉捩點。第一道秋風拂過臉龐之際,我終究慣性回望一切看似完滿圓融的關係,終究,要直面一道透明的隔閡。想起康諾進入大學,面對人際地位轉換的一番訴說
「要了解活生生的人,和他們建立親密關係,就必須運用像閱讀小說這樣的想像力。」
閱讀總是比影像來地隱晦,卻更加飽滿,當初看見許多無以名狀的眼神,在文字中長出意識,兩人的形象從線條交融成圓,再化作立體的輪廓。
我開始將《正常人》當成逃離的暫時居所,每讀完一次,沒過多久就再度回首確認,然後再重複一次。我不知道循環究竟為了證明什麼,無可否認的卻是,它在每個迷茫輾轉的夜,總能為我指出一條朦朧的路途。
如果康諾讀《愛瑪》,那之於我呢?
「像閱讀小說般的想像力啊……。」
我告訴自己。大約是《傲慢與偏見》吧。對他人超出水平的冀望加乘視差遮蔽了視線,身處其中卻說不出自己嚮往的關係是什麼模樣。大概我更自私一點,即使不擅拿捏,我也只希望恪守一段安全的距離。總覺得比起梅黎安,我與康諾或許更為相似,尋求人與環境的認可,卻只願看見良善的面向而非不盡契合的現實;清楚認知卻下意識撇開任何人際都是政治的通則。
想起來《正常人》也是政治的。哲學、歷史、階級、資本主義,又或者性愛,權力關係在互動間顯然可見。萬人迷康諾與邊緣人梅黎安,最初的戀愛是不平等的,物質天秤的失衡卻是全然相反——考上全額獎學金對康諾來說是生活價值的升級,給予他走過一趟歐洲,擁有整個下午面對藝術作品的餘裕;之於經濟無虞的梅黎安卻是一種認同的再確認,證明她足夠聰明,足夠值得被愛的證據。
「我多希望自己可以永遠和其他人站在同一邊,那樣我的生活就會容易地多了。」
她說。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就不能像正常人一樣,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沒辦法讓別人愛我。」
梅黎安總在那些分崩離析的時刻在我的身側呢喃。
權力的幽微的轉換在幾次熾熱的交合,沒有誰能真正掌控誰的選擇,兩人之於對方全然裸裎,她內心的自卑太深而他完全懂得,而這也是為何康諾確信自己能對梅黎安做出任何行為時,如此深刻地顫抖恐懼。
他們不擁有彼此,卻持有彼此的脆弱。
如果說,我對所愛(或即將成為所愛)持有過度期望,那麼我想康諾對梅黎安是沒有想像的,倒不如說,是沒有期待的。不見得每一次都穩穩接住那些思維,但是這種理解的動人之處在於,即使在不知所措之際,康諾也能告訴梅黎安,關係中唯一值得相信的,還有愛。這種愛不遠不近,保有遙遠的共感,不必轟轟烈烈,沒有猜忌懷疑。也許這才是閱讀兩人關係時,多少次揪心喘息真正的理由。
康諾與梅黎安幾次錯過彼此,也幾次承認內心的破碎與毀壞。曾聽人說過,愛是相信。我想,之於那些關係的追求與矛盾的眼光,在兩人的友誼與愛情中,多少看見了一種現實與理想並存的關係樣態。
貼近卻不介入。
大約就是截然不同的靈魂共享彼此感知,最完美距離了吧。

六個月後(二○二一年五月)
將近一年後,那段過渡的日子看來不遠不近,只是如今,我終能不再將它視為救贖般的出口。在某個夏日夜晚一時興起再度重讀,在那些碰觸心間的文句左側畫上一條一條歪斜的路途,期待什麼時候(或許是下個階段)再讀,就彷彿再走過一次心底的刻痕。
凌晨兩點五十二分,終於闔上書頁,橘紅色的廉價標籤紙對比鮮綠封面,就像在兩人身上看見隱藏的脆弱不堪,竟有個投遞的所在而如此張揚。比起影集,比起視線初次掃過那些直擊感觸的文字,如今的感動更是一種坦然。
關係的樣態在如今或許不再有一條規準的界線,而康諾與梅黎安與我們共享的世代背景,解釋了這樣的擺盪。
一向不喜歡在人們口中被分類,卻無可避免。我們是「零零後」,是「千禧世代」,好像處於這個時空世界的某些人,遭逢一切挑戰就必定依循著既定模式。所以我們進步、混亂、善變且漂泊不定,終將背負著空洞的形容詞跨越世代的衝擊。
我們正共享一種躁動的理想,無論它以什麼面貌出現在世人眼前。
「我」的意識強大卻在模糊,還不懂得看清脆弱的來向,世界與意識就同步向前奔去。許多結構性的物事仍在歷史的洪流中難以撼動,只是經歷著這些的我們,在前所未有的速度之下被推送著、迫使著,直面那些理性與感性的難關。
與影集初次相遇的那晚不同,關上床頭的夜燈,承認身上的傷口也好,走在一條變動的路途上也好,擁有幾段模糊的關係也好。
我享受這種認知自身狀態的時刻,就像身上的所有脆弱都長出生命,藉著康諾與梅黎安的際遇在故事裡,重新活過一遍。
「你應該去的,我永遠都在這裡,你知道的。」

後記
過了一陣子再翻出這篇文章重讀,然後決定發佈。直至現在仍能感受當時的自己,身上與康諾、梅黎安共享著那樣的矛盾與內心的躁動。文章裡下的標題故意與小說的分段方式相同,許是當時的執意與傻勁,時間,洪流般推動這些「我」的個體與青春切割,然後成長,血淋淋地直面世界的結構性現實。
每每讀完總要深呼一口氣。呼,我還在這裡呢。還學習與這個還年輕、並且仍然狂妄的世界社會共存,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