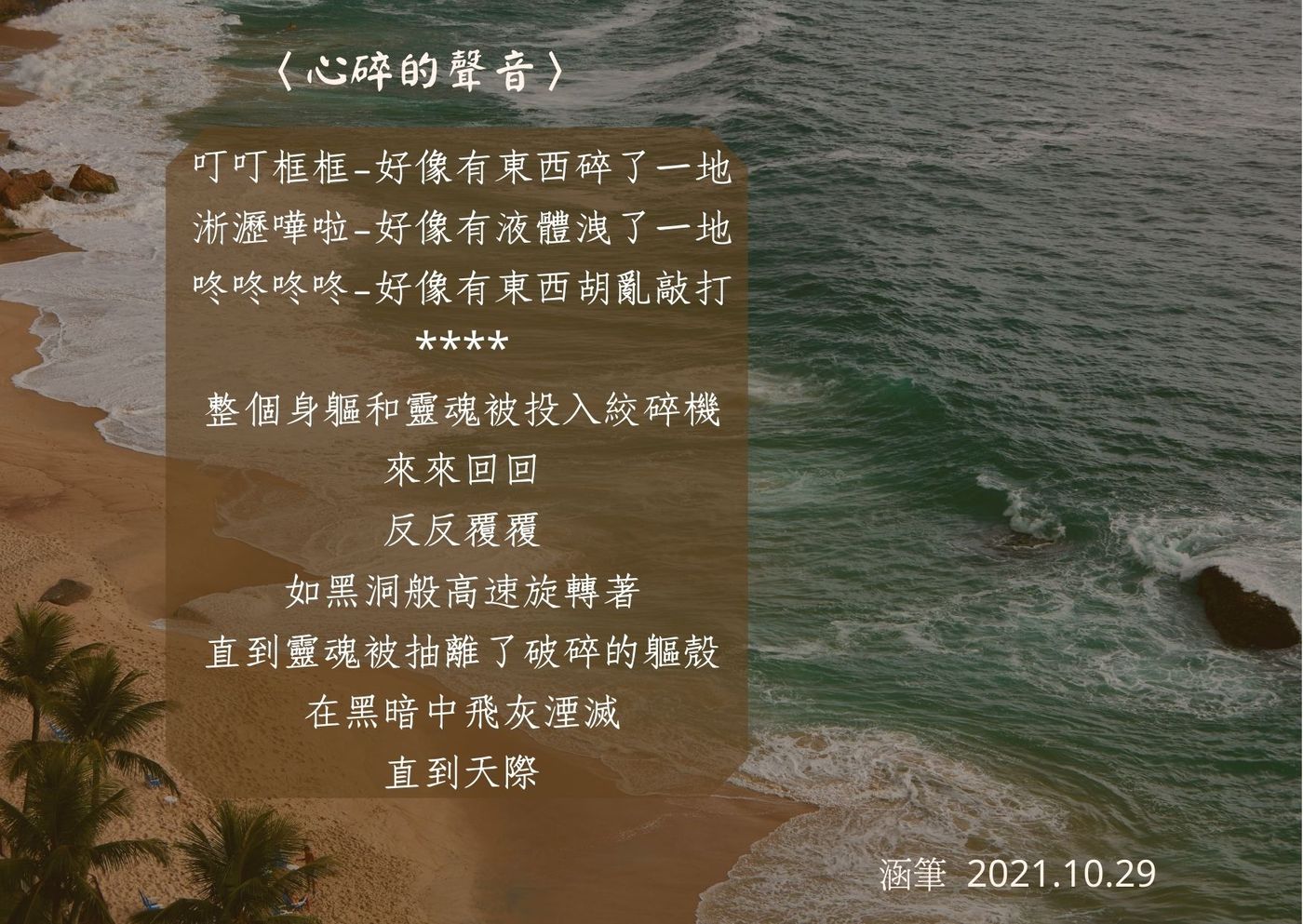文 : 5 月 圖 : 熟齡文青
三年半過去,我沒有再見過張威一面。我的心被他啃噬掉的那一塊,一直沒有復原。偶爾還隱隱作痛。我無法結交新的男朋友。父母親安排許多相親活動,都徒勞無功,因為那個創傷一直在那兒,無法結疤。
剛學英語時,老師解釋wound(傷口)和 trauma (創傷)的不同,她說,wound 癒合後就不見了,但trauma 卻會留一個疤,一輩子都不會消失的疤。張威對我的傷害,是trauma。
我常常想起Steve。感謝他在倫敦時陪我看的展覽,莎劇和靈與肉的理論。我把哈姆雷特票根放在皮夾裡,好像是一種護身符,提醒我復仇不是最佳解藥。離開倫敦時,我沒有勇氣問表姊更多關於他的事。我甚至不知他的中文名字。
我已經和小劉和解。不只是因為他們很快就分手了,主要是我了解到,即使不是小劉,也會有其他的女生。我慢慢接受小劉的說法,她勾引張威是幫我測試。只是沒想到張威如此不堪一試。
我和小劉的情誼,曾黏膩到我懷疑自己是不是同性戀。我的青春期,在父母慢慢成為陌生人,身體的變化,讓我茫然和躁鬱,許多強說愁的情緒時,只有小劉,完全擁抱我。
從國中到高中的日子,每一天都有她,也幸虧有她,我才平安,快樂的度過那個危險年齡。她是我沒有血緣的姊妹。我們相愛相殺。她背叛了我,但也幫我認清了張威。
小劉知道我沒什麼朋友,疫情期間,每個月會視訊一兩次。講話的總是她,她講她的新豔遇,她的工作,追的韓劇。我們從來不提張威。
但我和小劉,也不可能回到以前的友誼。我們之間有一條鴻溝。她的努力,只是維持鴻溝的距離不再擴大。
Steve和我約在信義區的一家牛排館見面。
三年半不見,Steve變得老成。他雙鬢少年白,身材碩壯,穿著合身的鐵灰色西裝,白色襯衫,打著暗紅灰紋的領帶。有英國紳士的品味。
我想起那個穿著皮大衣,在泰特美術館觀景台,和我討論薩德和斯多葛的博士生。為這個讓我盼了三年多終於聯絡上的人,我今天穿上了淡粉色的洋裝。我讓長髮披肩,噴上Chanel No5,對自己的嫵媚成熟,相當有自信。我要讓這一次的敘舊,變成第一次的約會。
Steve 已拿到博士學位,他現在一家上市的製藥公司當高級研究員。我們在互報近況後。他看著我,嚴肅地問,
「那個背叛的故事,後來怎麼結束的。」
「我從倫敦回來後,就再也沒見過那個前男友。如你所預料,他們很快就分手了。」
他輕輕地笑了,然後說:
「你和閨蜜也復合了。」
「喔,只是再成朋友,普通的朋友。但你怎麼猜到的。」
「我以前看過一齣日本偶像劇,就有這樣的劇情。情人關係是愛或不愛,是黑白的。但閨蜜間,則是更複雜的依存,有時像家人一樣,又愛又恨。」
他邊說邊得意地笑著。我很難想像,這樣一個知識分子,也看日本偶像劇。
但我和小劉的關係,正如他說的,的確是複雜的依存。這個Steve,太厲害了。
「所以那個案子已經結束歸檔了? 你心中了無芥蒂? 有新男朋友了?」
他一口氣問了三個問題。
「案子早結束歸檔了,但心中的傷痕還在,怕是好不了。」
他抿了一下嘴唇,並沒有說話,好像要等我把三個問題回答完,才再開口。
「一直沒有新男友。可能緣分未到吧。」
為了讓他接話,我把三個問題都回答了。
「我以前聽說過一個理論,把一段戀情,乾淨清楚的結束,下一段戀情才能順利展開。」
我不知如何接話。自從撞見他們炒飯。我沒再和張威講過一句話。他曾到家裡找我,我都避開了。打的電話,寫的e-mail我都沒接。後來他就放棄了。
我突然明白,為甚麼自己還一直在這個傷痕中。因為我沒有真的去處理他,我沒有去和張威說清楚,我沒有給他一個機會辯解,當然也沒有好好地說再見。
我不想再和Steve 討論張威的事,於是說:
「該我問了。你有女朋友嗎? 上回換石頭的女孩,真的就結束了嗎?」
「你離開倫敦不久,Covid-19 就開始流行。有兩年多的時間,我就住在實驗室。沒有社交生活,當然不可能有新女朋友。」

Steve 送我回到家門口。他說,
「我把手套還給你了。見你的藉口沒有了,怎麼辦?」
「今天是你作東,下星期該我回請了吧?」
「我喜歡這個答案。」
待續
2023/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