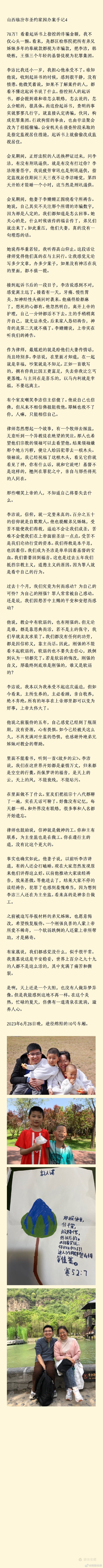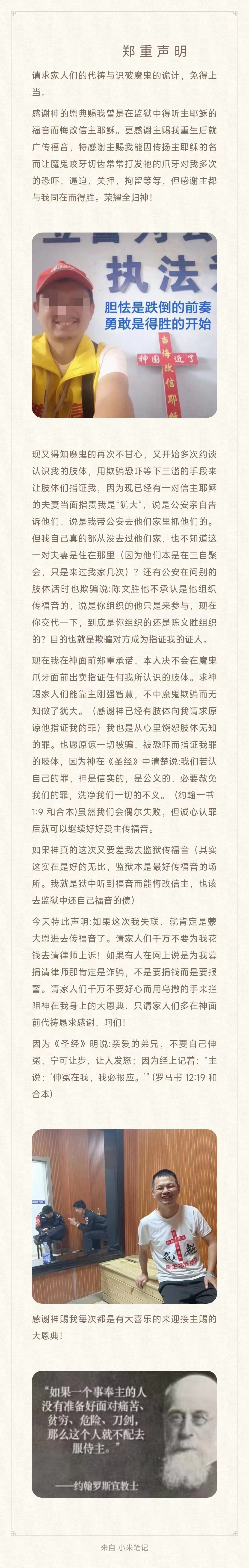戴志超传道May 19, 2023

还能唱歌真好,不能表达现在,那么唱一唱老歌应该是安全的。只是这种安全感,其实也可能瞬间发生改变。想起一个段子,“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这是八零年代的回忆。
艺术有无穷的感染力,言词一旦进入人心,就构成了集体的记忆,成为共同的喜怒哀乐。
我的小时候,在我们那个小镇上,我最有印象的艺术表演家,就是一个流浪汉,有点疯癫,吹得一手好笛子,总是在傍晚的时候,在镇上的中央车站,响起了悠扬的笛声。最高潮的时候,还会有一个不知哪里跑来的女人,跟着笛声的节奏翩翩起舞。人群中就爆发出欢乐的笑声。
看着这两个最落魄的人,却是那么的自由和释放,人群也得到了满足感。这种满足感,一种是因为对比他们的落魄而有的优越感,我想也有一种对他们的自由洒脱的向往。这是那一个灰色的小镇上,在日复一日单调重复的生活之中,我们所拥有的彩色回忆。
我的父母也是文艺爱好者,我们会一起在田间地头歌唱。从小我就听着港台的流行音乐,唱歌是我们家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我自己来说,我还有一个特质,就是爱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总是在笑,在该笑的时候笑,在不该笑的时候也笑。
我的妻子说,当初就是因为我的笑容吸引了她。今天我们看了一个“不能搞笑”的脱口秀,我们谈论起笑声,谈论着不会笑的同胞,看着那个脱口秀片段,我们笑着笑着就哭了。我们感到悲哀,又感到幸运。
我想起我在看守所时的笑容,仿佛我一个人在美丽新世界;在所有的囚犯之中,仿佛只有我是自由人。
在我被羁押一个月,在煎熬中等待是否批准“逮捕”还是“释放”的时候,我被带入了审讯室,坐在我对面的不再是熟悉的办案警官,而是两名和我年岁相当的年轻人,一男一女,面容姣好,原来是检察院的职员。
在那位女生向我宣读我被逮捕的文件的时候,我忍不住地笑起来,在我看来,这个场景确实很荒诞。她感觉有些莫名其妙,又似乎觉得被冒犯了,对我严肃地说:“有什么好笑的吗?”我连忙道歉:“我不是在笑你,我只是觉得太搞笑了。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当然,我心里是喜乐的,我现在回忆的时候都能感受到那种喜乐,因为我被这个世界逮捕了,也是被基督逮捕了,这是只有基督徒才懂的喜乐,也是我和主的约定:“主啊,如果你还愿意使用我,那就让我被逮捕吧,不要让我成为一个逃兵。”主垂听了我的祷告。
在仔细体会那个场景的时候,我看到我和对面的同龄人走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他们逮捕了一个人,只是在完成一个工作流程,仿佛一颗螺丝钉,完全没有自己的情感和判断。而作为被逮捕的一个囚犯,我却有作为人的全部的情感和自由的喜乐。
在这几年的颠沛流离之中,在人们被困于疫情之中,歌声却充满在这样的一群人之中;他们被这个世界视为麻烦,到处被驱赶的时候,人们可能认为他们一定过得不好,但是当你置身在他们之间的时候,你会发现在那里充满笑声和赞美。
人们以为他们要逮捕的是一群凶神恶煞的亡命之徒,近了才发现原来是在逮捕笑声,逮捕人性,逮捕幸福,以及逮捕自由。我想这些都不得不让他们开始痛苦的反思:噢,我究竟在做什么?我的世界出了什么问题?
我想,现在就是整个民族痛苦反思的时候,当我们在逮捕别人实际上却在逮捕自己的时候,当我们被困在自己的囚笼之中的时候,那真正的自由和欢笑在哪里?自由的边界在哪里?笑声的边界在哪里?而这一切又由谁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