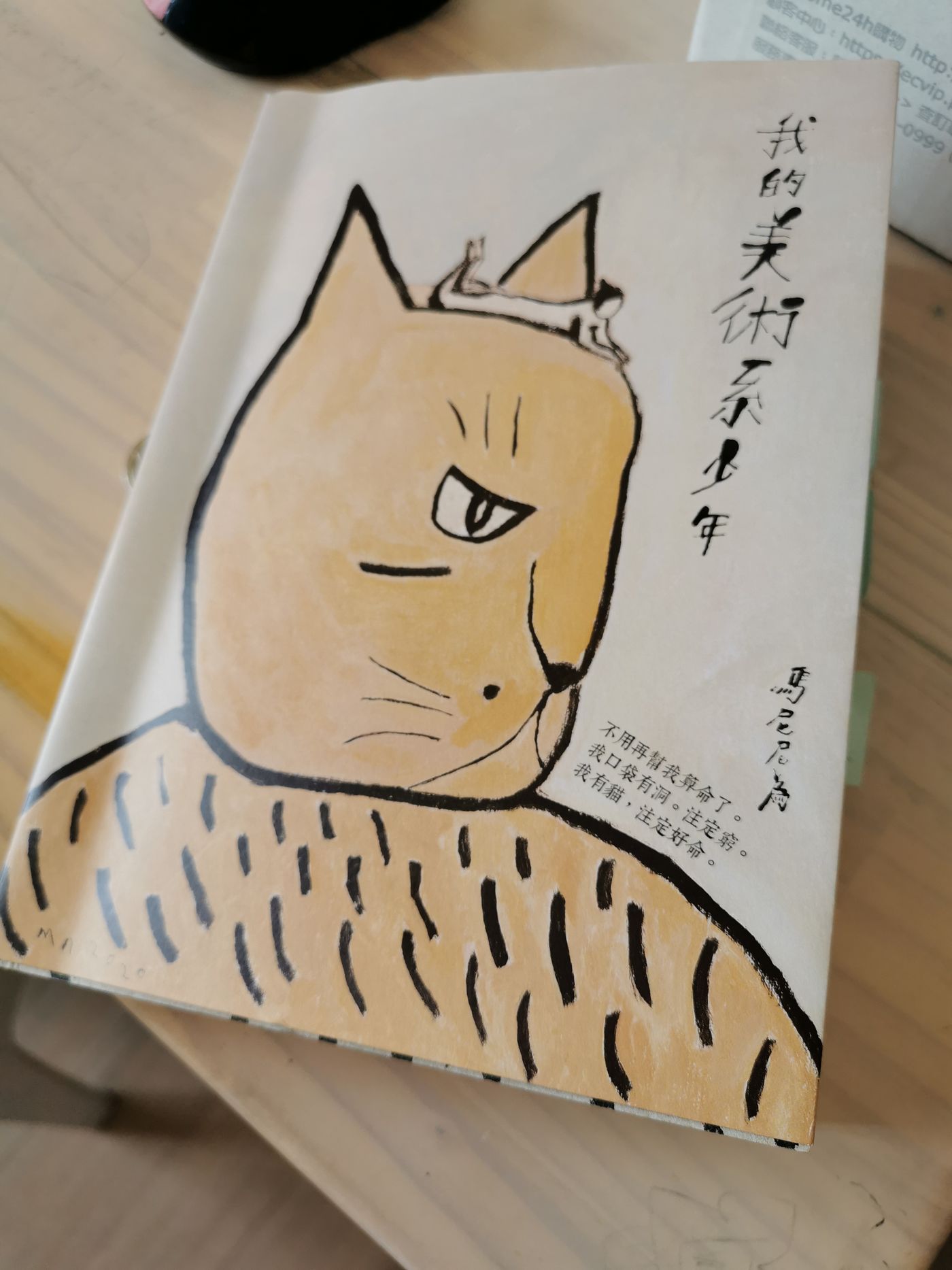真正的自由是什麼呢?
如同人生,每個人必然有不同答案。對我而言,是有餘裕不停探索與體驗。
近來讀行為藝術教母-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的自傳<疼痛是一道我穿越了的牆>,感悟藝術家的人生,真是超乎常人想像,卻又與大眾並無二致。超乎想像的地方在於,你難以體會她究竟經歷了什麼,儘管她在書中極端理性地、鉅細靡遺地坦率剖開了,她生命中的許多重大事件,但你卻始終無法體會,她在每個行為藝術裡,真正體驗到的是什麼。他人的人生,儘管能像Youtuber呈現出來的如何繽紛多彩,也仍與旅行本身相同,唯有親身踏上,方知其中冷暖。
瑪莉娜與大眾相同的地方,則在於情感上。所有人類自始至終,都是需要某種精神上的連結,以維繫自己的身心健康。瑪莉娜因為有一對極端的父母,成長於缺乏愛,卻又非常被嚴格管制的童年甚至青年,於是她踏上了極端的追求自由之路。
瑪麗娜最廣為人知的演出《Rhythm 0》
關於瑪莉娜最知名的表演,莫過於《Rhythm 0》。這場演出在1974年於義大利進行,瑪莉娜在桌上擺滿72種物品,從口紅、香水、剪刀,以及一把裝有一顆子彈的手槍。
開演前瑪莉娜向觀眾表示,自己將麻醉身體6小時,這段時間任何人都能隨意對她做任何事,且不會被追究責任。一開始,觀眾們只是將她肢體擺弄,做些無傷大雅的動作。漸漸地,人們發現瑪莉娜真的沒有任何反抗後,開始用口紅在她身上塗鴉、剪碎她的衣服,甚至有人用刀劃破她的皮膚,直到有一個人用上膛的手槍抵住她的頭部,最後被另一名觀眾制止。
在被人施暴的過程中,瑪莉娜的眼眶盈滿淚水,但並未做出更進一步的反應。表演結束,瑪莉娜站起來走向人群,所有人擔心遭到報復,紛紛嚇得開始四處逃散,沒人敢面對自己剛才的行為。演出結束後隔天,瑪莉娜聽說有很多觀眾打給藝廊致歉,表示就連他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做出那些事。
瑪莉娜表示:「這次經歷讓我發現,如果你把決定權交給公眾,離喪命也就不遠了。」
若你把自己所有的自由給予他人,你究竟會失去所有,還是會真正自由?但這世界已沒有第二次《Rhythm 0》,答案我們也無從得知。
瑪莉娜的情史
瑪莉娜的情史說不上複雜,她傷害過人,但她被傷害得更多。她年輕時為了擺脫母親的操控以得到自由,與第一任丈夫內薩結了婚,卻在婚後四年,認識了烏雷而出軌離了婚。
但那不過是她漫長辛酸情史的開始。她與烏雷形影不離,一起旅行、生活、傾心創作,共同完成了許多演出,直到十二年後,她總算親眼去直視對方,長期以來不斷出軌的真實:而她用的極端方法便是,答應對方三人行,然後眼睜睜地看著兩人狂歡。
自此之後,瑪莉娜終於死了心,最後與烏雷各自從長城兩端,走往與對方相會後分手,多麼轟轟烈烈,充滿傳奇。
後來的瑪莉娜與保羅,踏上了另一個十二年的情分,最終仍以同樣的戲碼收尾。那年,她已六十二歲。瑪莉娜的情史,是書中最貼近凡人的部分,卻側面完整了這位藝術教母的全部人生,她永遠在跌跌撞撞與改變,證明她確實活得傾盡心力。她也始終沒有放棄,去愛與被愛。
與烏雷分別22年後的2010年,瑪莉娜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舉辦她的個人藝術回顧展<藝術家在場>。64歲的瑪莉娜,在兩個半月中靜坐了736小時,與超過1500人沒有對話,只是互相凝視。
漫長的演出中,直到烏雷也坐上,位於瑪莉娜對面的那張椅子,自始至終不動如山的瑪莉娜,首次打破了規則,伸出了她的雙手。而在那之前,她早已哭成淚人兒。
當兩人在他們都最熟悉的場域中重逢,空氣凝結,徒留下了英國詩人拜倫的詩句:「事隔經年,若他日相逢,我該如何祝福你?以眼淚,以沉默。」
行為藝術家與旅人
讀完本書,除了閱歷了瑪莉娜傳奇的一生,另一方面,我也驚覺其實行為藝術家跟旅人,竟有很大程度的相似。
當瑪莉娜還正與烏雷熱戀的那幾年,他們曾買了一台二手的雪鐵龍小型貨車,過了三年的旅居生活,並寫下了他們的新生活宣言:
《藝術之必需》
不依地而居 機動能量
恆動 沒有彩排
直接接觸 沒有預期之結果
在地關係 沒有重複
自我選擇 延伸的脆弱
越過極限 接觸機會
冒險 原始反應
書中並未對這項宣言有任何解釋,但當我讀到這些短句,卻有深刻的共鳴。
不依地而居、機動能量、恆動-我的人生目前剛好旅行過30個國家,在這每一個美好的相遇中,我並沒有遇見一個,讓我想留下來一輩子的國家,包括台灣。更極端地說,若要我抉擇一輩子只能生活在台灣,或一輩子只能流浪在世界各處,我想我會選擇後者。而我當然愛台灣,我說的僅是極端狀況下的抉擇,而我的抉擇,乃是基於對人生自由的追求。
沒有彩排、直接接觸、沒有預期之結果、在地關係、沒有重複-這些完全可套進我對旅行的想法。即使是去同個地方,沒有一趟旅行是一模一樣的,連生活本身也是。唯獨不再預期地全心體驗,才可能在一次次看似重複的生活當中,體會到真正不斷在重複的,只有那不再能用初心看待一切的自我。
自我選擇、延伸的脆弱、越過極限、接觸機會、冒險、原始反應-遠行是自我追求的選擇,而其延伸的脆弱,便是當初我覺得生活在台灣,面對各種人事物,已讓我感到窒息。而渺小如我,所能想到的方法,唯有踏上不知歸期的旅程,去越過自己的極限,增加與人接觸的機會。在一次次的冒險中,理解真正的自己。
原來旅行,可以是一種行為藝術、一種創作,可以是你付出全部生命,所編織的一幅,獻給生活的藍圖。而當你傾盡所有,自由也就唾手可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