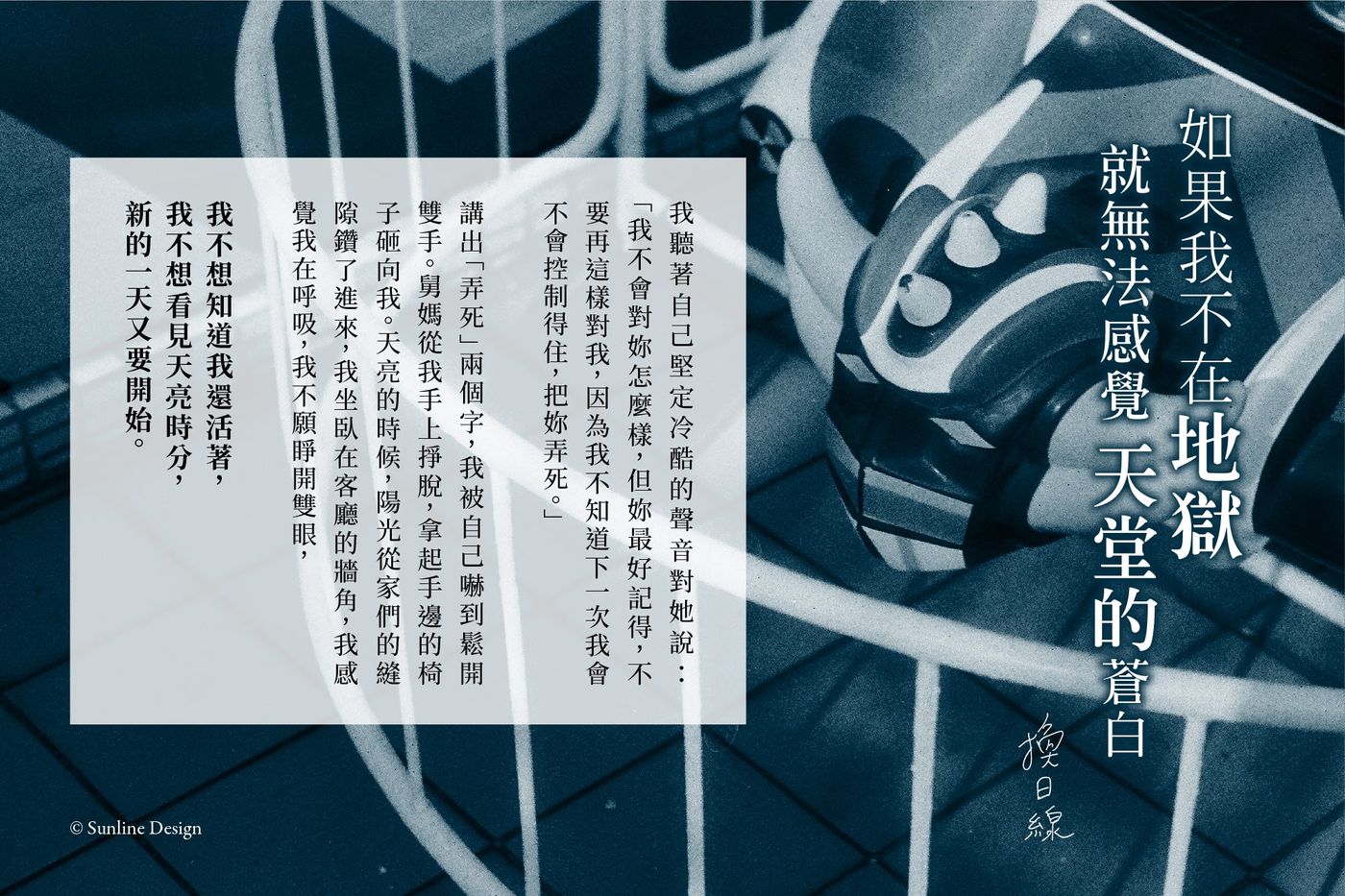從病到病態的家庭裏,呈現最血肉模糊的狀態。文中母親是隱藏整個過程當中,陰暗的那面,在處理小說元素而言非常自然,「妳的女兒很孝順喔!」很直接透過說話來反映社會對子女的重視,逐步拆解刻丈夫中風,伴隨著失禁或便秘的症狀,描述男性角色在此刻是在弱勢位置,「脫肛」是連貫起丈夫中風與安弟童年。就在這幾段便可以知道這個家庭的基礎狀況,我在閱讀的當下曾以為女兒就是安弟,但很快就知道兩者之間是獨立的身分。
「豔紅色的腸肉被擠出肛門,拔了毛的兔尾巴似的的垂在屁股上」是把敍事角度投射回以前,「兔子」這意象鮮明,跟父親現在的處境切入。作者以翹起屁股排便的男人和安弟小時候養的兔子類比,更具創造與現代性。按著把時空拉回「養兔子的觀察」——宣示權力與發情之間遊走。P.27「公兔子快速抖動臀部」「完事後公兔子僵直在一旁」從兔子的性慾切入到探討自己作品的核心問題。到小兔子被母兔咬死,興奮到死寂是作者在家庭裏轉變的過程,再度在安弟養兔子中看見現在丈夫的模樣,作為描述病與環境,作者一直都保持距離,像安弟走後,她再驚覺很久沒有用溫柔的語調對家人對話。這些都是簡短的文字而帶著強烈的情緒。女人以「報應」來形容中自己的丈夫也是挺吸引閱讀。
透過醫院的外籍看護再回到過往。安弟與外傭阿新有關洗澡與肉體的描寫,如:阿新豐滿胸脯,幫他洗澡的時候都會撞他的雞雞。直至女人觀察她如何幫安弟洗澡,「獨苗」「絕子絕孫」等形容,也可以看得出某些傳統思想,這種顧慮也讓作者在小說裏面更加豐富。整篇小說是以家庭中的女性成為脊椎,把亡子跟女兒交錯而寫,她作為國文老師的刻板行為與女兒的叛逆行為——P.30「我很早就壞掉了啦!妳不知道而已」埋下伏筆。其實女人也是有觀察到女兒與他們夫妻的不親,尤其是與父親的抵觸,「生辰與算命仙,父母緣離」但在迷信背後是更加悲慘,而且講到希望知道女兒上輩子是什麼,女人想要的是早夭兒子的投胎;而算命仙則以為是女人想要聽到「女兒是父親前世的情人」,這恰到好處的諷刺,落差比割裂出「姿媛」和「安弟」。在作者眼裏女人仍然是私我的傳統母親。
到P.32才把篇名有關的電梯搬了出來。「穿過大廳,她按下電梯鈕」對女兒她以為自己是無私奉獻的母親,雖然對於家庭是有所虧欠的,但還是覺得自己的好,我從文中發現作者對女性角色的塑造是具個人特色的。母親曾經在學校被性騷擾,讓她對於電梯的恐懼,我認為從電梯這個局限空間裏作者聯繫到許多過往的情節,母女的默契,到帶出電梯與故事線的不斷推移。在二樓進來的孕婦與小男孩逐漸帶出「安弟的死」——小男生在外面玩,多少也會有些傷口疤痕,女人隨口說的「要小心一點」是否是對自己的叮囑,又或許是那年警察的話。
「安弟的身體軟軟地被裝進屍袋裡,脖子上的割口血液已凝成紅褐色的血痂,一個猙獰的笑裂在安弟脆弱的脖頸……上身衣著完整,下身赤裸,股間帶血,她看見安弟腿間的陰莖像一隻夭折的幼兔癱伏。」描述得入木三分,再次扣回兔子的習慣——少年見網友約炮慘死公廁(我略過了一些形容,但整體我覺得這部分是第一次的高潮)作者從家庭裏處理許多議題,例如:移工、傳統觀念、新聞媒體、疾病,同性戀、愛情婚姻,甚至到後面的出軌、性侵、亂淪、性玩具等等,請反覆看P.33–38
丈夫把責任完全推向女人,新聞刊登後的輿論壓力使後來把她拉進深淵。作者描寫的這個母親具所有亞洲母親的特點,並且加以放大,用控制的愛來保護才是最大的傷害。但其實說愛也許並非完全的愛,她知道丈夫出軌而用孩子來約束,也是為自己而生。摘除子宮與剪掉頭髮,誰是真正的對錯,是作者保留給讀者的最重要問題。像文中的「後來,像是補破網那般,她和丈夫想把兒子生回來」但最後還是女兒,她描述的「為什麼是女兒呢?為什麼偏偏是女兒呢?她對自己生下女兒一事感到極端恐懼。」這恐懼是因為不是兒子,難以傳宗接代,還是怕女兒也受到性的影響?因此女人從出生開始便嚴格控制,防備許多事情,要求女兒變得平庸,甚至醜陋,在最渴望美的瞬間,扼殺。剪掉的頭髮會重新長回來,但碎掉的心並不會。灌輸錯誤觀念,把漂亮的女生形容隨便。回到電梯這空間,五樓進來的艷麗女人,跟自己的比較,再回憶至安弟死後,丈夫出軌。
離婚是傳統婦女較難接受的那部分。「把孩子生回來就好了」P.40描寫丈夫與女人的交媾跟兔子毫無差別,最諷刺的是為了虛偽的關係來保存他,事實上他還是出軌,而她繼續假裝看不見,對女兒埋怨丈夫的不對,第二次高潮作者用極簡短的筆觸寫出這個家庭最黑暗的事「媛媛告訴她兩件事,一是她有乖乖把爸爸留在家𥚃;二是她的妞妞不舒服」
——電梯上樓,電梯上樓。「女兒把按摩捧插在丈夫的肛門𥚃。哼著搖籃曲,強者淪於弱者的屈辱是等待後最精彩的報復。」;「她忘了女兒打從國小開始就自己洗澡了」我已經不知道所描繪的是否太輕?在社會上的黑暗比我們想像的來得更多,像這種潛伏的凌辱,也許是一種對病態社會的出口。P.45對女兒與丈夫的切換,強烈侮辱他是女人畫面中呈現的小白兔,在慾望面前,可愛是最好的偽裝。不斷深入的情節,挖出腐爛發臭的肉,咬死可能是最好的選擇,如果那時候女人決定離婚,可能對曾經的家庭都是好的發展,但既然作者要描述家庭中極致的黑,這篇小說是適合呈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