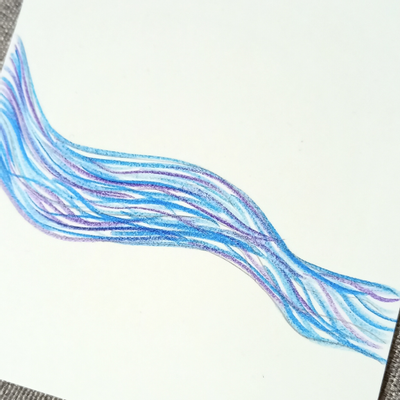夜暮又一次降臨,我獨自一人走在回家的路上。
所謂的家,確切地說,對我而言,只不過是遮蔽黑夜的地方。
走在每天都在穿梭的羊腸小道上,從天剛矇矇亮出發,到夜幕低垂才歸。
那個山坳中的國小只設有四年級,五年級開始,我便得每天清晨走將近十公里的山路,前往另一處的總校念書。
也許是那個年代某些封閉政策所致,學生不足、資源短缺,我們這群孩子只能集中唸高年級。國中起更是要離家住宿。
每天念完書,再走十公里回家。
那時並不覺得苦,反而是更多新鮮的事物與希望。
現在回頭想,也覺得神奇──那時沒有手機、沒有鬧鐘,每天只聽到雞鳴就能自然醒。
不像現在的孩子,媽媽在門口叫半天,他們還「嗯嗯啊啊」不肯起床。
我家位於學區邊陲的分水嶺,所以我不是「開路先鋒」,就是「壓隊後衛」──
出發時獨自一人,慢慢與別人結隊而行,回程時又是一人收尾。
耳邊是山裡呼呼的風聲,夾雜此起彼伏的雞鳴狗吠。
當世界的風雨聲與煙火氣漸與腳步重疊,歸於寂靜,
你會發現:
每天回家的屋子,總是黑的;
學校裡的午餐,只能吃幾口熱白飯;
自己守著自己,無人提醒,也無人等待。
那時的我,也許有那麼一點懵懂與慶幸。
孤獨與自由,大概是我最早的兩個朋友。
我家左邊有一片大菜園。媽媽離開後,那菜園也逐漸荒蕪。
菜園左上角,有一棵非常挺拔的大棗樹。
外婆和大舅住在隔壁,中間隔著那棵棗樹、一片竹林(那裡原本是一處墳地)和那片菜園。
外婆常常站在棗樹下,手裡端著一個大碗公,裝著熱飯菜。
等我點上煤油燈、坐下準備寫功課時,就會聽到外婆喊:
「阿妹啊~阿妹啊~」
我會快步跑過去,接過飯菜,蹲在棗樹下吃個不停。
吃完後,外婆會拍拍我說:「妳很乖啊~要加油喔~」
等她轉身回屋,我則靜靜躲在他們廚房牆外,聽著大舅數落她:
「又去送飯啦?就妳多事!」
聽完,我穿過那片竹林──有時覺得身後有黑影,像電影裡的妖怪──
我會逃也似地狂奔回家,把門一關,像在關上整個世界。
—
後來,我和外婆有了默契。每天放學後,我會先望向那棵大棗樹,等她從屋裡走出來,對我招手。
我常常想,也許她心裡有對媽媽的歉疚,也有對我的憐憫。
媽媽總責怪她:「不該包辦我那段婚姻。」
那是那個年代的苦與灰,那代人特有的命運轉折。
他們,一個是資本家的背景,一個是新社會的黨員;
外公是地主,被「鬥地主」鬥得一貧如洗。
媽媽總說外婆為了整個家,犧牲了她的一生。
或許外婆也有她逼不得已的苦衷吧。
當風穿過那棵老棗樹的枝葉時,我總覺得,那些沒說出口的故事與心事,也仍然在風裡。
靜靜地陪著我。
這裡,是「風無聲」──
是我故事開始的地方。
謝謝你,願意來聽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