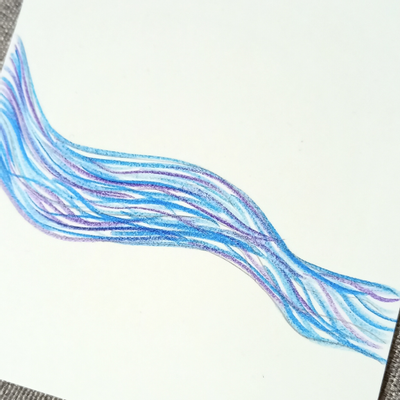鐵梯的鐵鏽味嗆鼻,我扶著欄桿往下爬。
頭頂的光線越來越遠,直到只剩老兵手上的打火機微弱的火星,
那火光不穩定,像是呼吸般一明一滅。「這裡…通到哪?」我壓低聲音問。
「你想知道的真相都在裡面。」
老兵沒有回頭,聲音像被濕氣吞沒。
下到底部時,一陣低沉的嗡鳴聲傳來。
我不確定是風還是什麼在呻吟。
鐵門微微開著,冷風從縫隙中鑽出。
我掏出口袋裡的地圖對照,這條通道確實在地圖上,但末端沒有標註出口,只畫了個模糊的圈。
「你母親…」老兵突然開口,「她不是死在兵工廠火災裡的。」
我心臟猛跳:「那她———」
「是被逼進門裡的。」
———門?
那個在母親信裡反覆出現的字眼。
鐵門被推開的瞬間,我看見牆壁閃過一片鮮紅。
那不是血,是旗。
日本旭日旗掛滿坑道兩側,火把搖晃,有士兵的腳步聲在逼近———
但下一秒,所有旗幟都消失,牆壁恢復冰冷的石灰色。
「你剛剛…看到了嗎?」我低聲問老兵。
「看到什麼?」他回頭,眼神空洞,「這裡從來沒掛過旗。」
我們沿著坑道深入,地面越來越濕,水珠滴落聲像是滴答的時鐘。
老兵忽然停下腳步,用手指著牆上一段模糊的刻痕。
那是一串日文———「守れ、門を開けるな」。
(守住,不要打開門。)
我呼吸急促,手指顫抖著摸過那些刻痕,它們很新,像是昨天才刻上去的。
「這不是四十幾年前的字跡。」我喃喃道。
老兵沒回答,只是繼續往前走。
越往裡走,聲音越多。哭聲、鐵鏈聲、日語命令聲交雜在一起,像整段歷史在耳邊同時播放。
我開始分不清自己是在聽幻覺,還是聽見過去的回聲。
突然———
腳下的地面一空,一股失重感讓我整個人猛然跌落!
墜落的失重感與撞擊的痛烈,充斥著我的神經,我的大腦。
「川!」老兵的叫聲在上方模糊消散。
我狠狠撞在濕滑的泥地,胸口傳來劇痛,耳朵嗡嗡作響。
抬起頭時,我看見坑道盡頭有一道鐵門,門縫滲出暗紅的光。
那光像呼吸一樣,一下一下———
然後,我聽見母親的聲音從裡面傳來。
「川…你來了。」
我爬起來,渾身是血。
鐵門後傳來鎖鏈拖動的聲音,接著是低沉的咆哮———
不像人聲,也不像野獸。
頭頂傳來老兵的喊聲:「不要打開!那不是給活人走的!」
可下一秒,鐵門自己發出輕微的「喀噠」聲,鎖鏈鬆開了一截。
就好像…正在等我推開。
鐵門後的暗紅光越來越強,像是深海裡呼吸的生物,脈動著吸引我的視線。
我扶著冰冷的牆壁站起來,血從額頭順著眼角滑落。
耳邊傳來混亂的聲音———
母親的哭喊、日本軍的口令、孩童的笑聲———
全擠在一起,像牆壁本身在說話。
「川……你要看嗎?」
聲音近在耳邊,卻不是母親,也不是老兵。
那是一種空洞的低語,像風鑽進骨縫裡。
鐵門緩緩打開,沒有一絲聲響。
眼前的坑道忽然亮起昏黃火光。
我看見穿著舊式日軍軍服的士兵正押著一群台灣工人往前走,
母親的身影混在其中,她低著頭,手腕被鐵鏈束縛。
但我知道母親那時還只是個女孩。
「這是…怎麼回事?」我低聲喃喃。
老兵站在我身後,臉色陰暗:「你不是想知道真相嗎?這就是。」
場景閃爍不穩,像斷訊的電視。
士兵的臉忽然模糊,忽然清晰,有人大笑、有人尖叫,有人被拖進更深的黑暗裡。
我看見爺爺也在其中他抱著一個箱子,滿頭鮮血,眼神瘋狂地盯著「門」的方向。
「守れ、守住門!不要讓他們出來!」
「黃金先運走!其他的……埋掉!」
吵雜的喊聲混亂交織,而坑道裡的空氣開始變得冰冷刺骨。
我退後一步,腳下的泥水卻濺起血色水花,再退一步,水又變回普通的泥濘。
「這些…是真的嗎?」我轉頭看老兵。
他低著頭,嘴角微微抽動,像在笑?但笑容極度僵硬,眼睛死死盯著我。
「你覺得呢?」
鐵門另一端,母親抬起頭,眼神對上我,那不是幻覺..那眼神太真實,真實到我胸口劇痛。
她的嘴唇微微動了幾下,沒有發出聲音。
我看懂了口型———
「別相信他。」
「川!」
頭頂傳來另一道聲音是父親的叫喊!
我猛地抬頭,卻看見上方的坑道已經空無一人老兵不見了,鐵梯也消失了,整條通道只剩我和那扇半開的鐵門。
而鐵門後方的紅光逐漸褪去,只剩下黑暗。
我聽到女孩的聲音,但我知道這是母親,而她在笑。
當我再次睜開眼時,坑道已經不見。
我躺在市場後巷的泥地上,雨聲和人聲混雜,有人叫我也有人問我是不是喝醉了。
我想張口解釋,卻只吐出一口血。
那扇鐵門,還在我腦海裡發光。
林老三死後,警局將他的遺物退回給家屬,但因為他無親無故,東西被送到兵工廠舊宿舍。
我冒著雨翻找破爛的櫃子,最終找到一本油漬斑斑的筆記。
筆記的封面寫著:「岡山坑道 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