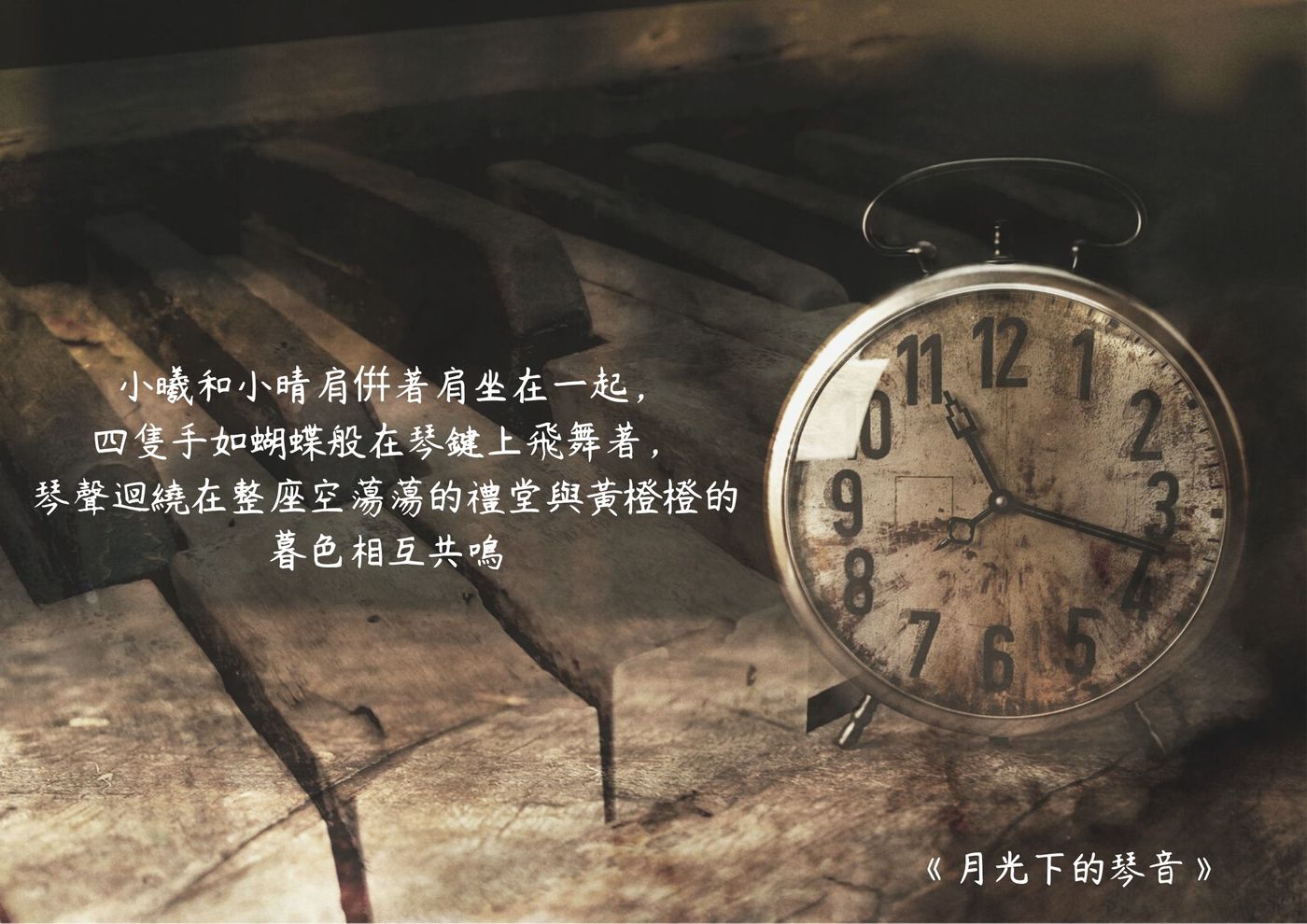一、
午後雷陣雨剛停了不久。白金色的雲層邊沿落了一滴陽光,針一樣地扎進地上的水窪裡斷了。十四歲的她將目光從窗外拉回來,盯著黑板上的筆記在課本裡依樣畫葫蘆地劃拉出一顆歪扭的心型,再分成三等份。
老師在三個格子裡寫下「本我」、「自我」、「超我」。
「……我們的心就像色彩的三原色,混在一起看起來會像是貼近黑色的灰色。」粉筆劃過黑板的尖銳聽起來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某座城堡壞掉的鐘聲。「如果在成長的過程裡失去調節,讓自我意識變得混亂,就會——」
-
『——就會怎樣?』
她偏了偏頭,清脆的鈴響喚回她的注意。她站在那幢普通的宅子前,身前的影子踮著腳尖、綁著凌亂的兩隻馬尾,正將手裡的風鈴掛上門前的廊簷。那風鈴是玻璃製的,精工細緻地刻著小巧的花型圖騰。那花是小蒼蘭,她還記得。
「……忘了。」她把書包丟在角落,繞到吧檯後方,把她的高中制服從抽屜最底層使勁拖了出來。襯衫與百褶裙疊得整齊乾淨,連一絲摺痕都沒有。
『是哦是哦。』影子看起來很感興趣,笑得開懷跳下了凳子,走進了吧檯——不,現在或許應該稱那個東西為祭壇。她走向吧檯前那只屬於她的塑膠馬克杯,廉價果汁嘗起來有化學合成的異常甜味。窗外的陽光被窗框切成一柄十字架,利劍一樣穿透他倆的身軀,在積滿灰塵的木地板上投映出一個巨大的十字型。
『今天要點什麼呢?試試看來一杯紅茶怎麼樣?』影子從吧檯邊上拿下一只瓷製馬克杯,巨大的茶桶被它踩在腳下。
「好。」她說。沒有加糖的紅茶是略帶苦澀的,與記憶中眼淚的味兒有些類似;吞下半冷的茶液時,她知道影子正踱步到她的身後,打量似地繞著她轉了一圈,飄渺如薄霧似的雙手輕輕摀住她的耳。
『那今天的祭品就是這個囉。』影子像個惡作劇後要逃跑的小女孩一樣笑開了。
-
她把參考書闔上,推到書桌的左側堆疊起來,覺得腦袋有些發昏。旁邊好像有誰正在說話,近在鄰桌幾個吱吱喳喳天南地北的同窗、遠一點在放學回家的街道上、更遠的來自隔著幾層螢幕閃過面前的、不同語言的跑馬燈。那並不造成困擾,只是偶爾令她有些暈眩;聽起來像某種兇惡的蟲鳴,如果她聽得懂節肢動物的語言,也許會想當一隻毛毛蟲,而後用繭絲將自己包藏在蛹殼裡,應該安寧得多。
她偶爾也會覺得或許她該靠近一點點,去聽那些聲音在說些什麼。但她到底是在帳幕前止住了腳步
她差點忘了她把聽力當作祭品交出去了。
於是她充耳不聞。
高中二年級開學第一天,早餐的桌上有父親的報紙、哥哥和母親時大時小的爭執聲。她將糖罐推到一邊,在自己的茶杯裡加入茶冰球。
「妹妹,你應該沒有跟你同學跑去搞什麼社團吧?」母親探頭過來,將她的作業簿檢查了一回後收進書包。
她沉默了一下,差點推翻了糖罐。「沒有。學生的本分是讀書。」
母親看起來很滿意,將書包和餐盒交給她準備送她出門。「妹妹長大啦,跟國中比起來讓人放心多了。」
她沒有回答,將腳塞進有些過窄的皮鞋裡,後跟鈍鈍地疼。推開家門時頂上清脆的鈴響伴隨口中塞滿食物的兄長含糊的疑問撞進她的背影裡。
「欸,你不綁雙馬尾了嗎?」
二、
「喂,你覺得無知是一種幸福嗎?」
她終於將這句話問出口時,影子正隨意地坐在舖子一角的乾草堆裡,腳邊還有顆咬了一口的半腐蘋果。影子抬起頭來,那張看不見眼睛的面龐只有笑容的弧度,如瀑的長髮在它一躍而下時飛散開來,像閃過夜幕的詭異陰影。
影子將手裡編好的花環戴在她頭上。『真是的,這是什麼問題?不可以撒謊唷,只有真相才是正義對吧?』
「……」她沉默了下去,從手邊的籃子裡抓起另一顆蘋果。鮮紅光亮的表皮深處隱約嗅得著一股腐味。她咬了一口,吞下尚且甘美多汁的外層果肉,瞇著眼盯住蘋果芯處生滿黑斑的內層與果核周圍,還能看見米白色的細小蛆蟲蠕動的樣子,衰敗的腐臭竄入鼻腔,而她動也不動。
隨後她依樣畫葫蘆地將蘋果丟在了乾草堆裡。
『別吃蘋果了啦,你是來要點喝的不是嗎?』影子開懷笑著跳進了吧檯……應該說祭壇裡,踮著腳裝模作樣地轉了個圈,一腳踢到了門上。門紋絲不動,連輕微的搖晃聲響也無,倒是簷上的風鈴惹禍似地發出叮噹脆響。
『糖罐已經不是你可以用的了唷。今天就來點苦澀的液體吧?』它從最底下的櫥櫃裡掏出一只平底玻璃杯,散了點淡香的黑咖啡伴隨幾顆冰塊叮叮咚咚落入杯中。若說從前,她也許會覺得這醇香真是完美得誘人,但此刻她只是維持沉默,像是被麻醉了一樣面無表情地、一口一口不間斷地將深棕近黑的清澈液體倒入胃與大腦。
『你想要覺得幸福嗎?』
她原先以為面前一片漆黑是因為咖啡淹沒視線,後知後覺地發現影子的雙手覆在了她的眼前。『那麼這個就當作今天的祭品留在我這裡吧。如果你想要這樣的話……』
-
她將褪色的制服與堆疊到腰際那麼高的考卷塞進同一個紙箱裡,覺得自己像是正看著某個一會兒就要被燒掉的古代遺物,有些悲壯過頭。
「喂,還沒好嗎?該上路啦。」哥哥將房門開了條縫探頭進來,發現她正蹲在中學時代的舊物旁不發一語,莫名其妙地皺了皺眉。「今天是你大學的報到日耶。好不容易考上了最好的學校,錯過報到就好笑囉。」
「……來了。」她拐了拐手腕腳踝站起身,一回頭看見哥哥的背影,張了張口想說些什麼又吞了回去。她覺得自己像一台被遺忘在陳舊年代的故障留聲機。不過也許這樣子最好。
「大學生啊,要成熟點,別在外頭惹事生非,知道嗎?」
她坐在副駕駛座上,偏頭看向握著方向盤絮絮叨叨的父親,點了點頭。 「以後你就會知道當學生多幸福啦,學校生活是很單純的。」父親在高速公路上換了個車道,繼續說。「外頭有很多並不是非黑即白的事,灰色地帶的事最麻煩啦,很多東西沒有是非對錯,像爸爸一樣活得久一點就會看得多……」
「那要怎麼辦?」她沉默了一下,開口問道。
「所以說,明哲保身很重要啦。」中年男人轉過頭,眉間光陰的刻痕裡寫滿真摯的語重心長。「出社會之後啊,什麼是真的一點都不重要啦,什麼能讓你過得好才要緊啦。」
她抬起頭,擋風玻璃外一片晴空萬里。她忽然覺得大腦裡颳起旋風,又急又猛地像是要把整片天空吸入頭蓋骨裡那麼兇猛。
-
後來她知道父親說的是真的。
她覺得她或許可以伸手去觸碰,撩開布幕的一角或是像那些飛蛾撲火的傻子一樣奮力地揭開。但她到底是放下了手。
她差點忘了她把視力當作祭品獻出去了。
於是她視而不見。
今天的腦殼裡裝的是陰天。她在鏡子前拿起剪刀,盯著手腕上縫線一樣的紅色痕跡好一會兒之後並沒有一如往常地反手刺進去。清脆的喀擦一聲,好像有人稱讚過的如瀑黑髮連同天空的倒影一塊兒碎裂散落在地。桌子上的手機叮咚響了起來,她偏個頭,看見哥哥傳來的訊息,說他近來工作有了空檔,要不要找時間吃個飯。
「欸,你把頭髮剪掉了啊!」青年喝了一大口檸檬紅茶,看著她的模樣驚奇地叫了一聲。
「……是啊。夏天很熱。」她沉默了半晌,將吸管插進透明玻璃杯中,杯內盛著深棕近黑的苦澀液體。她迫不及待地將麻醉藥納入四肢五臟六腑每一條血管內,覺得腦殼深處的疼痛似乎緩解了一些。
「欸,這不是咖啡嗎?我記得你以前說過咖啡很香但是很苦的吧?」
她停下攝入精神麻醉劑的動作,迎上手足的視線,忽然覺得自己像是個上了手銬的罪犯,隔著會客室的玻璃與家屬四目相交。「……現在喜歡了。」
「是嗎?」青年看起來很欣慰地拍了拍她的頭。「看你這個樣子,你真的長大了啊。」
她沒有回答,卻似乎聽見了某個熟悉的嗓音銀鈴般的笑聲。
- 本文作者
曦願,藍墨水文藝社第六屆副社長,現為國立台灣大學生化科技學系學生,曾於2014年暑假赴英國短暫留學。
喜歡說故事的平凡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