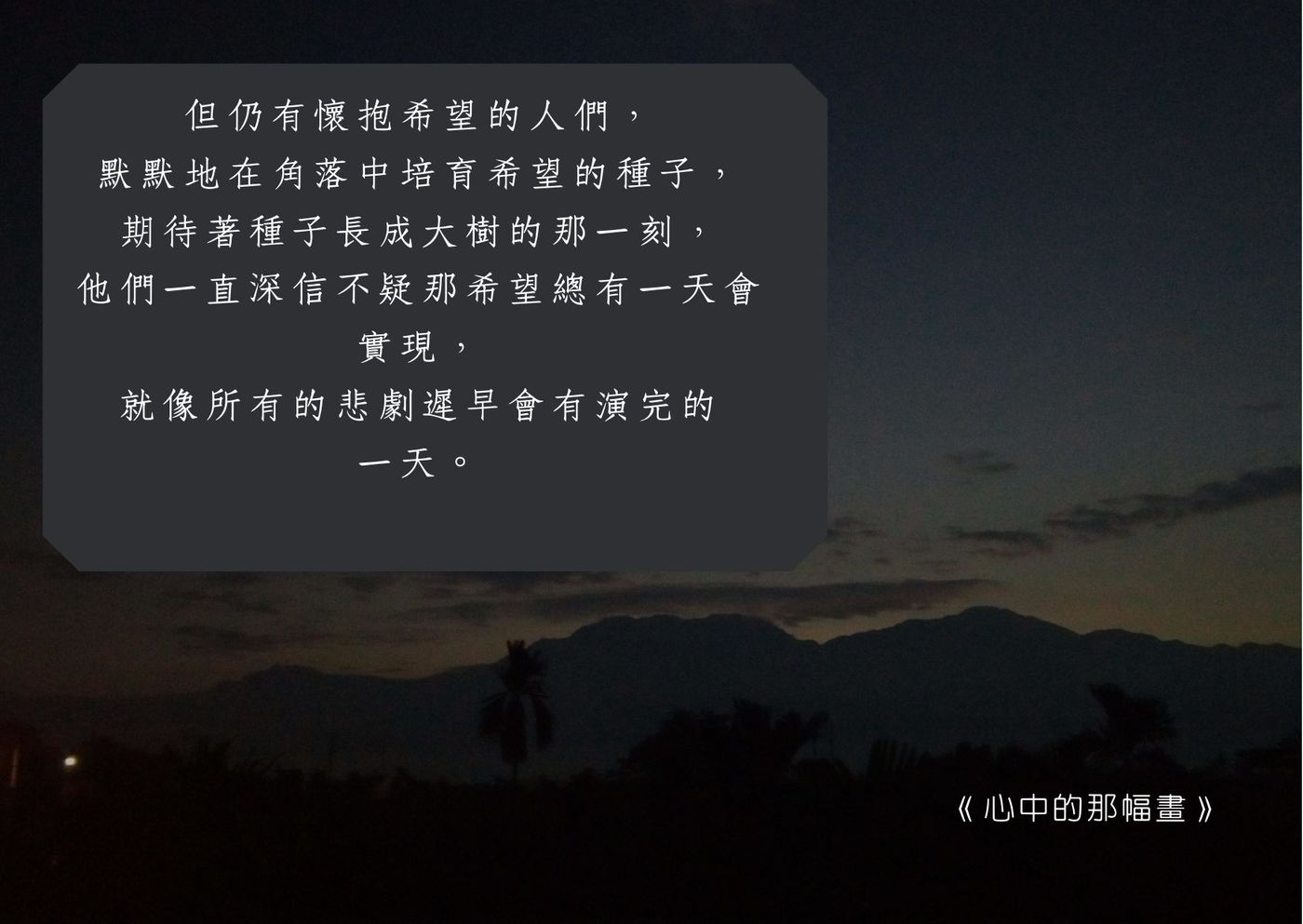《上邪》:「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為陵江水為絕,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上邪》漢朝古樂府 作者不詳
「『不論如何,我每天最少要幫一張底片上色。』」在Eliza Scidmore的作品背面,他叫我寫上這段話,當作他人生最後的註解。
星期一早上我去看他,換掉周末他前妻來看望他時帶來的那束隨手買的鮮花,瓶底的水已經乾了。我心想:「真的不該出這趟沒有意義的遠門」。移開花瓶,茶几上玻璃壓著的書簡從新獲得光明,上面是他年輕時充滿力氣的草書,寫著:「攝影是一種殘忍的發明,它可以記載一個人的體態從瘦到肥;看著歲月的侵蝕,讓人從生到死。(但是)照片上記載的回憶是恆古不變的。」他喚我。口中重複著「每天要幫一張底片上色」那句老話。
我走過去,扶他起來。
他擺擺手代替被痰卡住的「謝謝」。照顧他很長一段時間了,總還是覺得他略顯客氣。我拍拍他的背想辦法讓他舒服點,順順氣。他不停發抖的手嘗試把放大鏡掛到眼睛上,好不容易。枯枝般的手指緩慢、用力地旋開白色彩鉛水彩罐的蓋子,空氣中滲入油彩的味道,稍微中和了房間瀰漫的藥味。
我幫他把桌上的檯燈開關打開,從中和液中拿起最細的畫筆。雖然這場景每天再三發生,可是他還是發出沙啞的「謝謝」。「又是謝謝!」我心裡嘀咕著的同時,我撫順他的頭髮,把長時間臥床壓亂的髮型理順。心底,我關心他的病情和衰弱、消瘦的臉龐。
他的手抖得像枯枝被風不斷吹襲著,左右晃動。他透過掛在右眼上的放大鏡專注看著底片裡的世界,畫筆探進了油彩罐,很小心地沾上白色彩鉛。他看著我請求幫忙:「我只需要薄薄的一層。」因為手抖,他比平常更需要別人的協助。我握起他握筆的手刷去多餘的彩鉛。
他下了第一筆。
如果是以前,他會用教訓學徒般的口吻說道:「千萬要記得從攝影師的角度去體會他要表達抓住的瞬間,所以下第一筆時要去考量整體的景深、主題的焦點和配圖的占比。」年輕的時候他是如此的意氣風發,每天要花上許多時間接待上門求畫的攝影大腕和絡繹不絕上門求教、學底片手工上色的學徒。我環顧一眼同樣的房間,不同的是以前的熱鬧對比現在他的孤寂,就像窗外那顆白榆的四季分明。
他指著另一副放大鏡,意思叫我帶上。他倒轉畫筆,用筆尾對著花團錦簇的櫻花說:「Sakura~Sakura~」那是櫻花的日文,他有一股充滿回憶的表情看著Scidmore拍的底片,那表情難以形容,好像回春一般,如同底片裡藝妓臉上綻放的兩朵飛霞。「他想到什麼了?是我們一起在日本生活的那段日子嗎?」我不敢想太多。
我幫他旋開另外幾瓶彩鉛,他專心的調色。
他回頭看我,握著我的手說:「謝謝你,先生。」如往常地溫文儒雅。
這一瞬間,我想,我們是心意相通的。
桌邊還排放幾張Eliza Scidmore的底片等待他的手工上色,也許,這將陪伴他走完人生最後剩下的時光。
譯注:圖像是人類追求美感的過程,早期的黑白攝影作品需要透過人工上色的方法才能傳達出作者要表達的意境。以下照片均為Eliza Scidmore的作品,拍攝時間約在二十世紀初期,地點在日本。透過手工上色的模式展現人對美的追求。
--《自由的虛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