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中國論是反陷阱的陷阱
閱讀時間約 27 分鐘
中國社會學的先驅者之一,費孝通先生(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在1945年寫過一冊《鄉土中國》,1948年又出版了《鄉土重建》,試圖從社會的結構形態來分析中國的鄉村。
這原本是他講授「鄉村社會學」時所發展出來的講稿及意見,不料他在這兩本書中所描述的中國農村社會結構,卻成為爾後社會學界在分析中國文化特性時所常用的模型。
中國農村是一種並無具體目的、僅因大家在一起生長而發生的社會,可稱為「有機的團結」,所以是一種「禮俗社會」。
在這個社會中,人民很少遷徙移動,世代住在一塊土地上,附近全是生活在同一環境中的熟人與親戚,因此一切靠的不是法律,而是熟習所形成的禮俗。
西洋社會則不然,它主要是一種為了完成某任務而結合的社會,故需要契約、需要法律,屬於「機械的團結」,可稱為法理社會。
順著這種對比,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農村是靠著禮俗來構成秩序的長老統治形態。強調人治,重視血緣與地緣關係,由血緣地緣之親疏遠近來構成人與人的親疏判斷。
因此中國農村基本上是種「差序格局」,以自己為中心,一圈圈推出去。
反之,西洋社會是法理社會,人群以某些任務而組合,形成一個個團體。團體即其社會之單位,團體中人與團體外的人,分得很清楚,故為一種「團體格局」。
由於費先生的對比研究十分醒豁,文字又清新暢達,致使其差序格局、鄉土社會、長老統治、禮俗秩序等術語及概念大為流行。
他對中國社會的定性分析,也成為這幾十年來討論中國社會及傳統文化者的基本常識和許多論述的起點,影響異常深遠。
或者說,費先生對中國社會的描述,符合了大多數人對中國的印象。
例如說中國是個農業文明,中國人鄉土觀念濃厚、不輕易離鄉,而且家族關係深厚,尊重家族中長幼人倫秩序,家長族老的權威比較大……等等。
費先生的研究,乃是把這些一般人的通俗印象,以學術研究的架構和一些社會學術語予以表述出來罷了。所以提出來以後,立刻獲得認同,廣為學界所援用。
而且並不只社會學界引用其說,討論中國社會性質及中國傳統文化特性者,大抵都在基本論述框架上,運用了他的這些講法。
依此架構看中國社會,乃是「鄉土社會一禮俗社會一家法社會」三位一體的。
對於這樣的社會,費孝通希望予以改善。例如鄉土社會中人與人憑熟悉感與禮俗辦事,不需要文字,現在則須讓鄉村教育普及,鼓勵知識分子下鄉……。
也就是說:傳統的鄉土中國,應該改造成為西方式的法理社會。
一,看方法
鄉土中國論影響巨大,但接受費氏學說的學者,都沒有注意到這整個論述中間有個要命的錯誤:
「鄉土社會」只是費孝通在講授鄉村社會學時,針對中國農村的分析,因此他說的只是中國「農村社會」的基本性質,不是中國「社會」的基本性質。
費孝通在《鄉土重建》最後一篇《對於各家批評的總答覆》中已特別聲明:「因為我的知識偏重在鄉村方面,所以我看一個問題時也不免從這方面入手」。
又說:「我多年來研究的對象是中國的鄉村。鄉村只是整個中國社會的一部分,我從部分的認識中得來的看法,自不免亦有所偏。這一點讀者必須先知道的。」「我明白如果不了解鄉村以外各種性質的社區,很容易像瞎子把象形容成四個大柱子」。
這裡明確地說道:只從鄉村來分析中國,是一偏之見;惟因自己受知識所限,故僅能從這個角度來分析,希望讀者特別留意。
事實上,在寫《鄉土重建》時,他已開始對鄉村之外的城市社區進行初步探索了,後期他的研究也越來越重視城鄉關係。
但不幸的是:他的讀者顯然未注意聽他的警告,竟把他對中國鄉村性質的描述,視為是對中國整個社會的說明,抱著大腿說是大象,且說大象就如四根大柱子。
不但如此,後來沿用費孝通學說的人,也沒考慮到:費氏所進行的是社會學式的調查,調查的是抗戰前期大陸某些鄉村的情況。
這些民國時期的鄉村現象,是否能挪來作為歷史面的分析佐證,說明中國古代周秦漢唐宋元明清的社會性質,甚或文化性質?
要挪用,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進行「去歷史化」。
假設中國社會是不變動的,民國時之農村,即為先秦之農村。如此才能徑以孔子、墨子之言語來解釋中國家庭中的群己關係。
費氏本人即曾因此而錯誤地把中國農村界定為一種「歷世不移」也「不變」的凝固型社會。
後繼者更是完全忽略了此種做法與說法在方法學上的謬誤,未發現那種凝固不動的「歷世不遷」社會根本不可能存在、且根本是基於去歷史化之需要而被製造出來的(是把中國社會視為歷代不變的那種方法,讓我們看見了歷代不變的社會),實在也可說是缺乏方法學的警覺。
此外,費氏在描述此種社會時,用以對比的所謂西方社會,難道又真是西方歷史上的社會狀態嗎?
他為什麼不用西洋上古貴族奴隸社會或中古莊園社會來和中國農村相比較呢?
在那樣的社會中,所謂西方「法理社會」、「契約社會」又安在哉?
顯然,費氏在那兒,也是去歷史化的。把西方近世工業革命後的社會性質,當做西方社會的一般狀況,而拿來跟中國農村相比較。
如此衡量,在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傳統/現代」、「中/西」比較的變型,用以扭轉改變中國當時之現狀,促進中國的現代化而已。
費孝通在這兒,用了「血緣→地緣」、「身份→契約」、「欲望→需要」等區分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術語,且區分之中即表明了進程,強烈主張中國應走脫此種鄉土傳統社會形態,朝向新工業富裕經濟時代邁進。
後繼者因襲了這種意識形態,也套用著現代化論述,故亦不免把中國界定為「封建專制」,以相對於「民主法制」;為「宗法倫理」,以相對於「鄰人契約倫理」;為「農業鄉土社會」,以相對於「工商社會」,而希望打破那各種封建、宗法之宰制云云。
如此如此,從方法學上說,實乃錯亂不堪,但混雜了救世傷時之悲情與願力,有時還真是難以理喻。
二,看事實
在從事實層面看,中國社會不但不是農村鄉土社會,就連中國的農民也未必是定居於鄉土「安土重遷」。
費孝通自己曾談到過中國農村裡經常發生的「逃荒」現象說:
像我這種在太湖流域裡長大的孩子,絕不會忘記一年一度甚至幾度的「難民到了」的恐怖。這就是所謂「就食江南」。
……逃荒很可能是我們人口移動的經常原因。漢丁頓氏論中國民族性時特別重視這個現象。慷慨的、有同情心的人不容易不顧一切的就道,結果是被淘汰了。身體弱的、不容易適應別地水土的人在路上死了。留下的是代表著我們民族性的一輩肯低頭、自私、不康健卻也不容易死的難民們。
……災區裡的難民湧到了附近比較好的地方,如果這地方所有的糧食只夠自己吃的,經這批難民來一擠,也變成不夠吃的災區了,於是只有加入難民團體一起出外就食了。這些難民一方面是邊走、邊死,另一方面是邊走、邊增;一直要到有餘糧可以擋住他們前進的地方才停得下來。淮河流域的難民,逃荒可以一直逃到太湖流域。而且依我童年的記憶說,這是每年必有的現象。(《鄉土重建.天災和逃荒》)
他的描述實在非常生動,當時逃荒的規模實在也非常驚人。
但更驚人的是:為了維護他的「鄉土中國說」,他竟仍然堅信世代定居是常態,遷移只是變態:
「鄉村裡的人口似乎是附著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會有變動。這是鄉土社會的特性之一。我們很可以相信,以農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態,遷移是變態。大旱大水、連年兵亂,可以使一部分農民拋井離鄉,但是像抗戰這樣大事件所引起基層人口的流動,我相信還是微乎其微的。」(《鄉土中國.鄉土本色》)
這就是用信仰在對抗經驗事實了。
且不說永嘉南渡、五胡亂華、靖康之難等等,曾引起基層人口流動的重大事件,在歷史上絕非微乎其微,而是屢見不鮮。
歷代朝廷對人口遷徙也都有政策在推動著,例如移民實邊、徙民至京,規模動輒數十百萬。
而那所謂「可以使一部分農民拋井離鄉」的天災與人禍,既是每年都有,甚或一年會發生好幾次,其規模亦達到「恐怖」的程度,則那還能說只是變態嗎?
農村裡,有句俗話說:「人挪活,樹挪死。」人不是樹,因此,費氏所相信的那種世代定居「常態」,其實才是變態特例。
因為一整個宗族村莊,大多數人都必然會流往外地,只有少數人才會留在原址。
這就是為什麼所有中國人在其姓氏族望之發源地都非常寥落,反倒花繁葉茂於異鄉的緣故。太原王、博陵崔、清河盧、隴西李。試問今日太原王氏、隴西李氏尚有若干?能比得上散居於各地的王李崔盧嗎?
費氏只看到每年淮河流域的難民逃到太湖來,卻未想到秦漢關東關中之民奔走益州交州;中州衣冠,南渡長江;嶺南又繼而開發;然後,農民更駕著船,棄其田疇耕耨,赴南洋北美淘金伐木去了。
世代定居?附著土地?哈哈哈!這是什麼神話?天底下怎麼可能有這樣的社會?中國尤其不是這種社會。
三,看歷史
由歷史看,依李泰初《漢朝以來中國災荒年表》(《新建設》十四期,1931年4月)、
吳毓昌《中國災荒之史的分析》(《中國實業雜誌》一卷十期,1935年10月)、
鄧雲特《中國救荒史》、
史觀《對災荒宣戰》(《大公報》,滬,1950年3月20日)、
竺藕舫《中國歷史上之旱災》(《史地學報》三卷六期、1925年6月)、
寧可《漢代農業生產漫談》(《光明日報》1979年4月10日)等文和專書的研究,從公元前18世紀的商朝時期開始,至漢朝末年,中國凡發生自然災害477次。其中商朝13次,兩週89次,秦漢375次。
吳毓昌《中國災荒之史的分析》(《中國實業雜誌》一卷十期,1935年10月)、
鄧雲特《中國救荒史》、
史觀《對災荒宣戰》(《大公報》,滬,1950年3月20日)、
竺藕舫《中國歷史上之旱災》(《史地學報》三卷六期、1925年6月)、
寧可《漢代農業生產漫談》(《光明日報》1979年4月10日)等文和專書的研究,從公元前18世紀的商朝時期開始,至漢朝末年,中國凡發生自然災害477次。其中商朝13次,兩週89次,秦漢375次。
另外,寧可在《漢代農業生產漫談》指出,先秦大約12年中有兩個災年,占16.6%。
從秦始皇元年至漢呂后元年的60年間,則有重災9次,占統計年度的15%,其中大水、大旱8次。
從呂后二年至新莽末年的210年中,有52個年度有重災,占統計年度的24.8%,其中大水、大旱即有42次,比先秦自然災害率要高。
東漢自然災害更嚴重,從光武建武元年至靈帝光和七年的160年間,有46年有重災,占統計年數的28.8%,其中大水、大旱凡39次。可見地力越來越遭破壞,災旱越來越多。
所以到了費孝通的時代,才會出現那種連年災荒、難民奔波流離於道途的情況。人口遷徙,正發生於此一自然條件中。
人口遷徙的因素當然不止是因為災荒。
以先秦兩漢來說,
殷淑慧《我國民族之轉移及混化》(《朝華》二卷二期,1930年11月)、
李斐然《中華民族古代之遷徙考》(《新亞細亞》十二卷五期,1936年11月)、
蒙文通《中國古代民族遷徙考》(《禹貢》七卷六、七期,1937年6月)、
馬宗霍《中華民族之遷徙與拓張及異族勢力之消長》(《國師季刊》十期,1941年5月)、
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史語所集刊》二卷一期,1930年5月)、
梁園東《商人自契至湯八遷重考與商民族興於東土駁議》(《東方雜誌》三十卷十九期,1933年10月)、
衛聚賢《殷人自江浙徙於河南》(《江蘇研究》三卷五、六期,1937年6月)、
李竣之《周代西方民族之東殖》(《清華周刊》三十七卷九、十期,1932年)、
譚戒甫《先周族與周族的遷徙及其社會發展》(《文史》六輯,1979年)、
林劍鳴《周公東征和贏姓西遷》(《文史知識》1982年十期)、
胡厚宣《楚民族源於東方考》(《史學論叢》1934年7月)、
劉德岑《秦晉開拓與陸渾東遷》(《禹貢》四卷八期,1935年12月)、
龔自知《第一批來雲南的移民 — — 莊蹻開滇》(《雲南日報》1957年3月14日)、
馬開梁《楚族南遷的時代及遷徙路線》(《思想戰線》1982年二期)、
王雲渠《西漢徙民於諸陵考》(《師大史學叢刊》一卷一期,1931年6月)、
梁園東《漢代中國民族之南遷》(《大夏年刊》1933年6月)、
陶元珍《兩漢之際北部漢族南遷考》(《禹貢》四卷十一期,1936年2月)、
呂克由《秦漢移民論》(《齊魯學報》二期,1941年7月)、
宋廢嵩《漢人北徙與匈奴南遷》(《集美校友論著》1948年5月)、
劉振華《從考古上看漢代中原移民與吉林開發》(《吉林日報》1979年4月18日)、
呂名中《試論漢魏西晉時期北方各族內遷》(《歷史研究》1965年6期)、
葛劍雄《西漢時期西北地的人口遷移》(《中華文史論叢》1984年二輯)……等文章,更可以看出中國各民族各地域人民東遷西移南徙北走的事實。
殷淑慧《我國民族之轉移及混化》(《朝華》二卷二期,1930年11月)、
李斐然《中華民族古代之遷徙考》(《新亞細亞》十二卷五期,1936年11月)、
蒙文通《中國古代民族遷徙考》(《禹貢》七卷六、七期,1937年6月)、
馬宗霍《中華民族之遷徙與拓張及異族勢力之消長》(《國師季刊》十期,1941年5月)、
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史語所集刊》二卷一期,1930年5月)、
梁園東《商人自契至湯八遷重考與商民族興於東土駁議》(《東方雜誌》三十卷十九期,1933年10月)、
衛聚賢《殷人自江浙徙於河南》(《江蘇研究》三卷五、六期,1937年6月)、
李竣之《周代西方民族之東殖》(《清華周刊》三十七卷九、十期,1932年)、
譚戒甫《先周族與周族的遷徙及其社會發展》(《文史》六輯,1979年)、
林劍鳴《周公東征和贏姓西遷》(《文史知識》1982年十期)、
胡厚宣《楚民族源於東方考》(《史學論叢》1934年7月)、
劉德岑《秦晉開拓與陸渾東遷》(《禹貢》四卷八期,1935年12月)、
龔自知《第一批來雲南的移民 — — 莊蹻開滇》(《雲南日報》1957年3月14日)、
馬開梁《楚族南遷的時代及遷徙路線》(《思想戰線》1982年二期)、
王雲渠《西漢徙民於諸陵考》(《師大史學叢刊》一卷一期,1931年6月)、
梁園東《漢代中國民族之南遷》(《大夏年刊》1933年6月)、
陶元珍《兩漢之際北部漢族南遷考》(《禹貢》四卷十一期,1936年2月)、
呂克由《秦漢移民論》(《齊魯學報》二期,1941年7月)、
宋廢嵩《漢人北徙與匈奴南遷》(《集美校友論著》1948年5月)、
劉振華《從考古上看漢代中原移民與吉林開發》(《吉林日報》1979年4月18日)、
呂名中《試論漢魏西晉時期北方各族內遷》(《歷史研究》1965年6期)、
葛劍雄《西漢時期西北地的人口遷移》(《中華文史論叢》1984年二輯)……等文章,更可以看出中國各民族各地域人民東遷西移南徙北走的事實。
據統計,東漢時期,關中地區的京兆、右扶風、左馮翊、涼州地區之戶與口數,只剩下兩漢時期的19.1%及22.7%,可見80%左右的人口都移走了,剩下的僅是少數。
先秦兩漢交通不便時尚且如此,後世之移動當然只有更加迅速了。
世代定居不移,顯然只是某些社會學家把社會凝型化,以便進行文化形態學式之對比時,以臆想構造出來的假象罷了。哲學家以其空疏,遂相採擷以為談證,則殊屬不智。
四,看社會
從世代定居的角度看,中國農村的基本單位是家族。
可是,若從人民遷移、不恒居處的角度看,則中國農村的基本單位就根本不是家族宗族,而是「社」或「社邑」、「社會」。
古代的社,從土從示,土即祖且之形,為陽具崇拜的祖先宗廟祭祀之地,它與宗族之關係當然極為緊密。
封建宗邦以「社稷」連稱,也表明了它是一種結合封建王權、宗族血緣和農耕經濟的單位。
但秦漢廢封建行郡縣以後,社便逐漸被「里」所混或取代,成為里社合一的制度。
漢末三國兩晉南北朝,戰亂頻仍,人口流散。這時的里社雖然仍是地域性同里居民的結合,但又已從三個方面與漢代的里社有別。
一是社與里分離,單獨組織單獨活動。主持社事者不再是里正、父老,而是有專門稱謂的社老、社正、社掾、社史。
二是並非里中全體居民參加,而僅為部分居民的結合,參加者已有「社民」這樣的專門稱呼。
三是除傳統的社祭外,又發展出了其他職能。它們與私社已沒有多大區別。
所謂私社,有適應門閥世族制度和戰亂中舉族遷徙與聚保需要,以宗族地望關係為紐帶而結成的「宗社」;也有按階級和職業結成的社;但最盛行的則是東晉至南北朝時因佛教流行而由信徒組成的「邑義」和「法社」。
邑義主要流行於黃河流域,一般按村邑或宗族組成,在僧人參加或指導下,結集人眾,聚合財物,從事造像、修寺、建塔、營齋、編經等活動。
主事者稱為邑主、邑長、邑維那、邑師等。參加者稱邑子、邑人。規模一般為十餘人到數十人,有的達數百人甚至千人以上。
「法社」興於南方,側重講經、說法、修行。參加者往往是貴族、官僚、士大夫。
社會愈發展,私社愈是流行。許多私社隨自己的主要活動和社人成份而有專名,如親情社、官品社、女人社、坊巷社、法香社、香火社、燃燈社等等。
它們大體可分兩類,一類主要從事宗教活動,如營窟、造像、修寺、齋會、寫經等,與寺院和僧人有密切關係,多數就是寺院和僧團的外圍組織,僧人參加或領導的也不在少數。
另一類主要從事經濟和生活的互助,其中最主要的是營喪葬,也有的還兼營社人婚嫁、立莊造舍的操辦襄助,以及困難的周濟、疾病的慰問、宴集娛樂、遠行之餞送、回歸的慰勞等。有些社則兼具兩類社的職能。
而傳統的社祭,則被此類私社消化吸收了,也成為這些私社會集的重要活動內容。
此外,還有農民集資買牛的牛社,士兵集資買馬的馬社,及管理灌溉工程的渠社等。
至於兩晉南北朝出現的「宗社」,則由於門閥制度衰落,已逐漸湮沒不彰。
另外,更有隋唐以後,普遍興盛的各種行會。隋代即有「行」,但只是同類工商業店肆集中的地方,沒有形成行會。
唐代前期,「行」遍布於各城市與州縣治所,行有行首,負責一行事務,有共同的行業神祭祀活動和組織動員的「行社」。
可見「行」已不單純是工商業者集中進行貿易的地方,而是同業人員的聯合組織,行會已初步產生。
唐代,行進一步發展,行會的職能明顯化。
各行不僅有共同的宗教活動,還產生了一些共同議定的行規。如無一定技術不得入行、非本地人不能入行、本行技術不得外傳等。同行者有共同語言,即後人所謂「行話」。
行會的組織結構有行首、師傅、徒工之分。行首對內組織宗教祭祀,督促每人執行政府命令,對外代表一切,負責與官府聯絡、交涉,維護本行人利益。
上述社集雖也有些是按地域組成的,但只是部分居民自願與自由結合。更多的則是打破了地域界限,按性別、階級、職業結合。
社的首領通常稱為社長、社官、尋事、社首、社頭,總稱三官,由社人推薦。社人之間的關係是「貴賤一般」、「如兄如弟」。社的活動開支,除臨事由社眾繳納外,還有若干公共積累,可以動支。
社的宗旨、職能及社人的權利義務已非純依習慣和傳統,而是採用社條、社約的形式加以規定。
換言之,中國社會的主體,是流動的人之組合,而非定居的農村宗族。
五,看契約
秦漢以後,我國農村的基本國家行政單位即是村里,社會生活組織則是社或會,只有部分宗族聚居村落中仍保留一些上古宗社遺風,或維持宗廟血緣祭祀體制。
但家族絕不會是行使社會生活功能的基本單位,因此把中國農村「鄉土社會中的基本社群」僅僅認定是宗族或大家庭,無論如何都是荒謬的。
惟有把中國社會設想為一種以家族為基本社群的結構,才能推論說中國人是在其中進行長老統治,形成禮俗秩序。
但事實上族長未必為村長里正,更不見得是社頭,族人里人又未必全屬同社社員。社員之間,則係以契約、以法理來結合來規範的「機械的團結」(Gesellschaft)形態。
因此每個社都有契約、社條、條約、規約規程來界定彼此的權利義務關係。
宋代以後,連傳統的宗族也逐漸社團化了,蘇洵、歐陽修的族譜,范仲淹的義莊,都表現了這種意義。
蘇洵建族譜亭,以族譜與族人立「約」,及范仲淹義莊,都把血緣性宗族轉換成了一種經濟和生活互助的團體,而且立了族規條約來規範族內人士之權利義務關係,導致宋代以後的宗族迥異於唐宋以前。
縱使族內長老要進行統治,所依據的也不再是禮俗與習慣,而是家法和族規。
宗族祠堂除了承擔血緣祭祀功能之外,也成為社團性群聚集議的場所。
如宋德安陳氏《規程》有云:
「我家累世餘慶,子孫眾多,上下和睦。然恐雲礽漸夥,愚智不同,苟無肅睦之方,恐負乖和之理。今欲維之以局務,定之以規程,推功任能,勸善懲惡,使公私財用之費、冠婚喪祭之籌、衣食輿馬之給,子孫可以世守。」
他所說管轄族人、庫司經濟、管理莊田、任責教育等「局務」,與范仲淹所訂《范氏義莊規則》甚為類似,這便證明了此時的宗族在血緣上固然是一大家族,但在內部組織及功能上,卻已社團化了。
有人昧於這種轉變,仍嚮往著古宗族狀況,或以為宋以後之鼓勵修族譜收合族,即是上復三代封建宗法之舊,周鍾岳《騰沖青齊李氏宗譜.序》便一語點破謂:「世之論宗祠與宗譜者,往往欲此以復宗法,其說遂膠固而不可通。」因為宗族事實上已不只是血緣群體了。
費孝通對中國鄉村的理解,正與周氏所批評的一樣,不知中國鄉村之基本社群並不是家族而是社;又不知社並非「禮俗社會」式的「有機的團結」,而是「法理社會」式的契約形態;更未認識到宗法家族已日益社團化,已變成一種仍維持家族血親人群組合的實質社團。
猶如散布在各地的某某同鄉會,雖仍敘齒爵、講鄉誼,卻非以地緣組合為其社團運作原理。
內部的權利義務乃至倫理關係,都需經由社約規程之界定。與職業行會社團、宗教人士法社、興趣遊藝社團如詩社、蹴球社等等,沒什麼不同。
在這樣的社會中,因社團組織發達,人民的權利義務關係均由各自的社團處理了,政府一般遂都不處理這類民事問題。
所有法律體系,如《唐律》、《宋刑統》以至《清律》都甚少民法的部分,民間的租賃借貸契約關係,悉由民間自理。
政府主要只負擔刑法的部分。惟有民間無法處理的重大民事糾紛,才會鬧上衙門,由政府機關進行行政仲裁。
但一旦由官府來處理,即不免於刑罰,故一般民事既無須赴官,告官又往往涉及刑案,百姓自以不打官司為常態。
費孝通把這個現象完全弄錯了,竟以為我國鄉土社會中進行的是一種「無法」的「禮治」方式。不以法治而以禮治,討厭興訟。
殊不知人民犯了族規,自有族家法處理,開祠堂、斷是非。犯了社規,自有社團依其章程規約來辦理,罰錢、服勞役,為何需要對簿公堂?此亦法治,但與西洋之法不同耳。
以此區分中西為禮治社會與法治社會,實屬無稽之談。
當然,這也不是說中國社會即是費孝通所說那種西方式的法理社會,而是說費氏這一套「鄉土中國論」根本不能解釋中國社會。
要明瞭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即必須從方法及視野上超越鄉土中國論。
建立在費氏一切論述之上,由「鄉土中國」、「安土重遷社會」所發展出來的各種論說,也須放棄,否則都是妄談,講得越多,錯得越厲害。
六,看文化形態
費孝通《鄉土中國》曾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社會學研究方法:社區分析。
他說道:
「以全盤社會結構的格式作為研究對象,這對象並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須是具體的社區。因為聯繫著各個社會制度的是人們的生活,人們的生活有時空的坐落,這就是社區。每一個社區有它一套社會結構,各制度配合的方式。因之,現代社會學的一個趨勢就是社區研究,也稱作社區分析。」
社區分析的初步工作是在一定時空坐落中去描畫出一地方人民所賴以生活的社會結構。
社區分析的第二步是比較研究,在比較不同社區的社會結構時,常發現了每個社會結構有它配合的原則。原則不同,表現出來結構的形式也不一樣。於是產生了「格式」的概念。
費先生說:
「依我這種對社會趨勢的認識來說,《生育制度》可以代表以社會學方法研究某一制度的嘗試,而這《鄉土中國》卻是屬於社區分析第二步的比較研究的範圍。在比較研究中,先得立若干可以比較的類型,那就是依不同結構的原則分別確定它所形成的格式。
去年春天我曾根據Mead女士的《The American Character》一書寫成一本《美國人的性格》,並在這書的後記裡討論過所謂文化格式的意思。在這裡我不再複述了。這兩本書可以合著看,因為我在這書裡是以中國的事實來說明鄉土社會的特性,和Mead女士根據美國的事實說明移民社會的特性在方法上是相通的。」
他的意思是說:
社會學不能泛說社會如何如何,應研究具體時空區域中之社區;並由對具體生活及制度之分析,來獲知社區之結構。然後,通過對不同的社區結構原則之對比,我們又可進行文化格式的比較。
所謂文化格式,即文化形態。
不同的社會有不同之文化形態,不同的文化形態則表現在它們不同的社會結構配合原則上。
所以他以「移民社會」來說明美國文化這種形態,而以「鄉土定居社會」來描述中國之文化形態。
他這種研究方法,影響深遠。或者說,他反映了他所說的那種趨勢,因此在社會人類學學界,此類方法之運用,可謂屢見不鮮。
從許烺光到楊國樞、李亦園,都嘗試藉著文化形態上的對比關係,勾勒中國人的國民性或美國人的性格。
但這套方法的第一步與第二步往往矛盾。怎麼說呢?
社區分析之第一步是研究「一定時空坐落中一地方人民所賴以生活的社會結構」,亦即特定之時空中的現象,例如費孝通所調查的田祿農村或花藍猺社會組織之類。
但由此得知的該社區之社會結構原則,在第二步工作中卻立刻推到「中國人」、「美國人」這麼廣大的範圍中去,上下包涉可達幾百年幾千年,地域涵蓋可至幾萬里,不再是「一定時空坐落中一地方人民所賴以生活的社會結構」了。而且社會研究轉而成了文化研究。
社會研究在許多時候確實需走向文化研究,因為社會制度的建立,以及制度間相互配合的原則,涉及價值觀的問題。
對於社會生活,為何這樣處理而不那樣處理,是文化的差異。要說明這些,當然須展開文化研究。
但是,這樣的文化研究,是要與社會研究相結合的,其範疇必須相當。
不能只研究某一時段某一地域之社會,便以此推斷中國文化如何如何、美國文化又如何如何。
其次,「每個社區有它一套社會結構、各制度配合的方式」,這是可以由社區之具體分析中得知的,有客觀可徵驗之材料可以說明。
但「每個社會結構有它配合的原則,原則不同,表現出來結構的形式也不一樣」,卻是需要透過解釋才能得見的。
用涂爾幹(Durkheim)的話來說,前者是社會事實的部分,後者討論社會結構之所以如此存在的原理、原因和功能,則屬於如何解釋社會事實的問題。
解釋若不相同,則對於整個文化「格式」的認定,當然就不會一樣。
那麼,費孝通是怎麼解釋呢?涂爾幹曾建議採用社會形態學,制定社會類型以解釋之(見《社會學研究方法論》第五章《關於解釋社會事實的法則》)。
費孝通也是以分別類型的方法,區分「中國格式」與「西洋格式」,然後說明其社會結構之配合原則。
但如此一來,究竟是「依不同結構的原則,分別確立它所形成的格式」,還是自己「先確立若干可以比較的類型」,才據此類型說某社會的結構原則是如何如何?依我看,恐怕還是後者的成分多些。
也就是說,他所解釋出來的所謂社會結構原則,所描述的那些因「結構原則不同,表現出來結構的形式也不一樣,於是產生了不同的文化格式」現象,根本起自他原先即已預設的社會類型分類上。
例如,先確立了社會可分成「移民社會/定居社會」、「法理社會/禮俗社會」等可資比較的類型,然後說中國之社會結構原則就顯現了這樣那樣的狀態,所以可稱為定居禮俗社會,形成了一種可與西方相比較的文化格式。
前提即是答案,自我論證,循環論證,所以越說好像越有道理。但若一旦不採用他的分類,則對社會結構原則的理解和解釋便會全然異趣。
此外我們則應注意費孝通這樣分類對比中西文化,有其時代因素。
五四運動以後,有一段時期,論中西文化者,流行採用此類文化格式對照比較之方法,如梁漱溟說西方是向前看的文化,中國人中庸,印度人向後看;錢穆說中國是尚德重義的文化,西方是尚力重利的文化;唐君毅說中國是黃土文化,西方是海洋文化之類。
藉著高度概括的兩相對立之類型,來凸顯中西文化的異質性,說明中國文化的特徵,以維護其價值或顯示它應予改造,乃20至50年代反傳統與尊重傳統之人士都常使用的方法。
運用這樣的方法,有其特殊之時代感與論述情境,值得同情。
但把歷史文化或民族性等問題,如此高度概括到一兩個詞語中,且予以極端化,形成「A」與「非A」兩種對比類型,卻是我們所難以同意的。
所以,我們不但要徹底拋開錯誤連篇的「鄉土中國論」,明白中國是個遊民社會,而非定居社會;明白社、族、群、會之行為理則在於契約和信義,而非長老權威。
還要逐漸避免使用高度概括的對立類型,來凸顯中西文化的異質性。五四以來那些老方法、老觀念、老範式、老論調,都最好別再講了。
…
#費孝通 #鄉土中國 #差序格局 #文化比較研究
推薦閱讀:
許多人說西方文化重分析,中國文化重融合。說得對!但能有個哲學的解釋嗎?下面是我的分析。medium.coma
一般人並不知道,也不關心學者怎麼想,可是學者的想法,常已把他的腦子給搞亂了。同樣,世界的爭端多起於觀念的衝突,而許多正是學者引起的。因此,了解一些學術上的路數,其實是生活上的必需。 底下,我要介紹一下比較文化研究的思路與進展medium.coma
近代講人類文明史與中國文化史,都有個基本框架,謂人類由蒙翳至文明,經歷了巫術時代、神權宗教時代,最後才進化到理性申張的人文世界。medium.coma
為什麼會看到廣告
66會員
268內容數
留言0
查看全部
龔鵬程大講堂的沙龍 的其他內容
你可能也想看
法願:中国是香港的香港寄放在奥巴马大王的哪篇文章回来了,大家想说什么就大声说吧。
中国是香港的香港
法治是社会的社会
自由是人心的人心
民主是呼吁的呼吁
香港在英国統治期間,有他大事因缘成就了香港和香港人,这些感情珍贵值得人们珍惜,所以大家都愛香港。中国回收香港说出了中国是香港的香港,是中国人希望香港不要發挥其作用做个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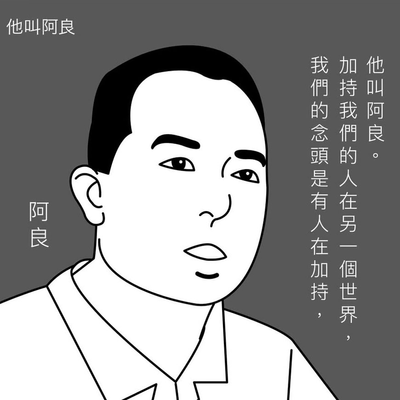
2021-08-03
劉仲敬訪談 105 @ 20200909 論中國的大陸體系其最大邊界歷史的大趨勢是能夠預判的,具體的點則是很可能有出入的。如果沒有史達林的話,即使蘇聯不在托洛茨基的領導之下在二十年代就跟英國和日本發生戰爭而自爆,至少捷克和德國無法落到蘇聯統治範圍之內是大概率現象。捷克本身並不一定會落入東歐集團的,捷克芬蘭化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這中間都是取決於一點點偶然事故。

2020-09-29

2018-04-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