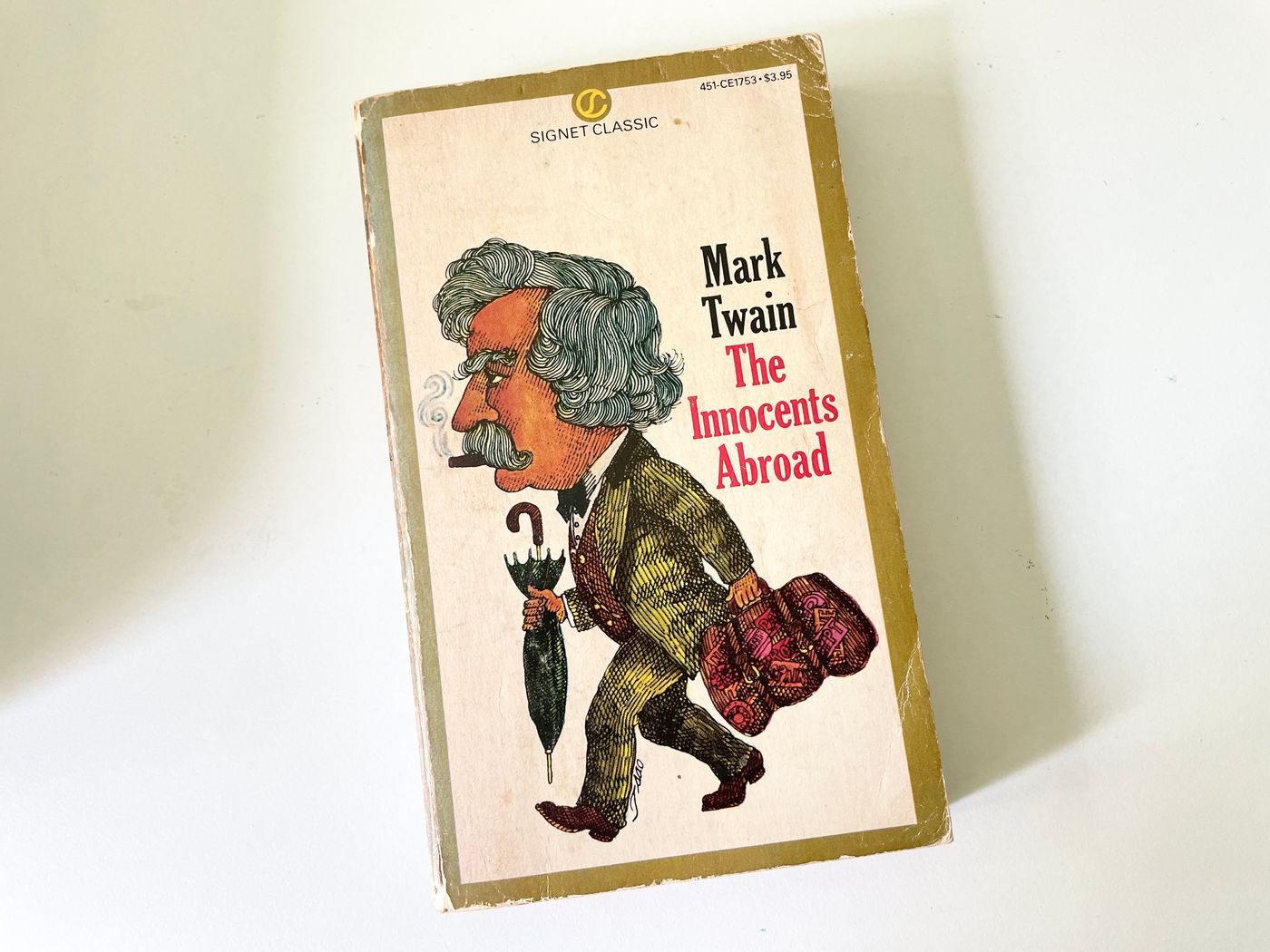Dear Jing,
兩周前讀完妳信的那天晚上,我就夢到自己身在花蓮,住在老舊狹小的旅社裡。因為一心想看海,出了旅館,便沿著街道直直往海的方向去,走著走著卻來到了山的面前。轉身返回,途中遇見了曾經熟識但後來沒再聯絡的學姊T,她一下子說了許多像是跟最親密的朋友才能訴說的事,一下子又表現得生疏淡漠。
早晨醒來,我還想著夢中清晰的騎樓、街巷、近海邊的快速道路。那是花蓮嗎?其實我很久沒去花蓮了,那也許是我記憶夾雜著想像的花蓮,或是宜蘭、新竹、和雲林的綜合體。但總之,一定是我所熟悉的台灣——路上汽機車交雜、街角有便利商店、我和學姊還去吃了可以免費續加豆漿的早餐。我們如何指認一座城、一個地方?

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我也是在大學時初次接觸;那是大一的國文必修,我選的課以旅行文學為主題,但現在還記得的也只有這本了(以及艾倫・狄波頓《旅行的藝術》xD)。印象很深的反而是老師提到,台灣有段時間開始盛行旅遊文學,一大原因是航空公司徵文、並開出高額獎金,大家紛紛寫起旅行——原來某類文學、藝術、文化的興起,有時不過出於這麼簡單實際的緣由。
當時,還沒有太多國外旅行經驗的我,讀著《看不見的城市》裡一個個以記憶或慾望、沙土或星象編織的,鏡像映照、自我循環、或除了名字什麼都在改變的,活人與死人之城,主要覺得新奇而充滿想像力;忽必烈和馬可波羅關於帝國、關於語言與虛實的對話,則似懂非懂。而這些年來,遊玩過也換住過不同的城市,如今因妳提起才又重拾,一口氣讀完,有了截然不同於當年的共鳴和驚嘆,那裡頭真是經歷各種形式的行旅才可能浮現的深刻哲思,卻表現得美麗輕盈如詩。

此刻的我,特別喜歡關於城市如活體、旅行如人生,那之中漫漫累積、或一瞬而成的變動,關於過去/現在/未來的無窮假設和可能性,以及不可能性。但同時也有點矛盾地沉溺於城市的相似與相連:有些地方第一次到達、卻似乎已熟悉,對話彷彿都聽過講過了,也已經度過同樣的日子。去到世界的哪裡不是如此?
不過,最吸引我的,仍是城市與其名字不完全相符、也並非毫無關聯的關係:
愛琳是遠方一個城的名字,你一走近它,它就變了。
路過而沒有進去的人所見的是一個城,困在裡面而永遠離不開的人所見的是另一個城。你第一次抵達時所見的是一個城,你一去不回時所見的是另一個城。每個城都該有不同的名字;也許我已經用別些名字講過愛琳;也許我以前所講的一直都是愛琳。
有趣的是,剛開始讀的時候,我彷彿在每座城裡都看見了土耳其。大概因為書中明確提及忽必烈的帝國和地中海東部,以及我最近剛好看了些在土耳其各地旅行和街頭小吃的影片,才意識到土耳其有多大,是原本認識淺薄才只知伊斯坦堡與安卡拉。但讀著讀著,到了書的一半左右,當可汗要求馬可波羅講講威尼斯,而他回答:難道你以為我一直在講別的城?
「我每次描述一個城市,其實都是講威尼斯的事。」
從那之後我讀到的每座城都成了威尼斯。甚至,回過頭往前翻閱,原本的那些城也都搖身一變似地成了威尼斯。
語言,或命名,對認知的影響力竟是如此巨大。

而馬可波羅甚至沒那麼需要語言。他可以用手勢、動作、叫聲、和旅行袋掏出來的物品來講述這些城市故事;那些物品像徽章,能被賦予不同的象徵意義,又不易混淆。甚至,他連旅行帶回來的東西都不需要,只要一盤棋和棋子:馬能代表騎兵、軍隊或騎士紀念碑,女王可以是露台上的女子、噴泉、或尖頂教堂。
忽必烈如今不必派馬可波羅出使了:他讓他不停下棋。馬的跨角移動、像在出擊時的斜線移動,皇帝和小卒步步為營的移動、每一局棋的優勢和劣勢,都隱藏著帝國的消息。
大汗努力專心下棋:然而如今他想不通的卻是下棋的目的。棋局的結果或勝或負:可是勝的贏得什麼、負的又輸掉什麼呢?真正的賭注是什麼呢?局終擒王的時候,勝方拿掉皇帝,餘下的是一個黑色或白色的方塊。忽必烈把自己的勝利逐一肢解,直至它們還原成為最基本的狀態,然後他進行了一次大手術:以帝國諸色奇珍異寶為虛幻外表的、最後的征服。歸結下來,它只是一方刨平的木頭:一無所有。
但馬可看著這一無所有的木頭,說起那來自什麼樹種,纖維的紋理、毛孔的密度代表曾經過怎樣的季節變化、生過哪一類蟲;忽必烈大為驚奇,而馬可波羅已經又開始講起烏木樹林,講載運木材順流而下的木筏,講碼頭,講窗邊的婦人……

待在小小的地方——或許無論在哪,每個人真正能認識的都只是小小的地方——經常忘了世界。如妳所說,狹長的花蓮約是台北到苗栗的長度,各鄉鎮已經難以一概而論,何況那些我們彷彿認得、但其實多麼陌異的名字和國度。我剛認識到土耳其的遼闊,一查之下發現它的面積不過排名世界第36。烏克蘭稍微小一點,排名世界第45,但已經是歐洲面積第二大的國家了;這麼廣大的國家遭受永久性的破壞摧毀,究竟會成什麼模樣?而目前世界排名面積第一大的國家是俄羅斯,約莫是台灣的470倍——我們如何能想像和理解那麼大的地方?
我其實不知道這些數字有沒有意義。只是希望自己永遠記得世界有多大。
寫著寫著,因為戰爭時事而有些沉重了起來。明明最初開始寫這封信的時候,我心想著的是要跟妳分享最近讀得愛不釋手的、另一本關於旅行與身體的書,波蘭作家奧爾嘉.朵卡萩(Olga Tokarczuk)的《雲遊者》。她也是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也許妳已經讀過這本、或作者的其他本書?

我非常非常喜愛《雲遊者》的敘事風格,文體在散文、極短篇小說、書信、人物傳記之間自由穿梭或融合,半真實半虛構,極富文學性。她以旅行貫穿全書,有對旅行的哲思、途中遇到的人和趣聞,也穿插許多對身體和器官的思考與故事,解剖學的部分尤其令人驚艷,我好久沒有像這樣讀到入迷了。最心愛的書和電影往往最難以用文字形容介紹,總之,也是很有自身魔法的一本書,覺得妳一定也會喜歡,而我看完之後立刻想找來她其它作品,甚至燃起了自己放在心底但擱置已久的、想寫些文學創作的欲望。
新加坡的三月多雨潮濕,讓我有種與台北同步的欣喜感覺,儘管身在台北時總是抱怨那令人難受的溼氣。大概台北就是我的愛琳,無論到了倫敦或新加坡、香港或奧斯陸;即使叨叨絮絮說著另一個城市的種種,到頭來仍是愛琳,既遠且近。
待過花蓮、又再次回到台北的妳,有沒有什麼新的感受呢?近來還在進行什麼樣的寫作嗎?想念妳了,希望妳一切都好、享受春暖花開——
Ally 郁書
2022.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