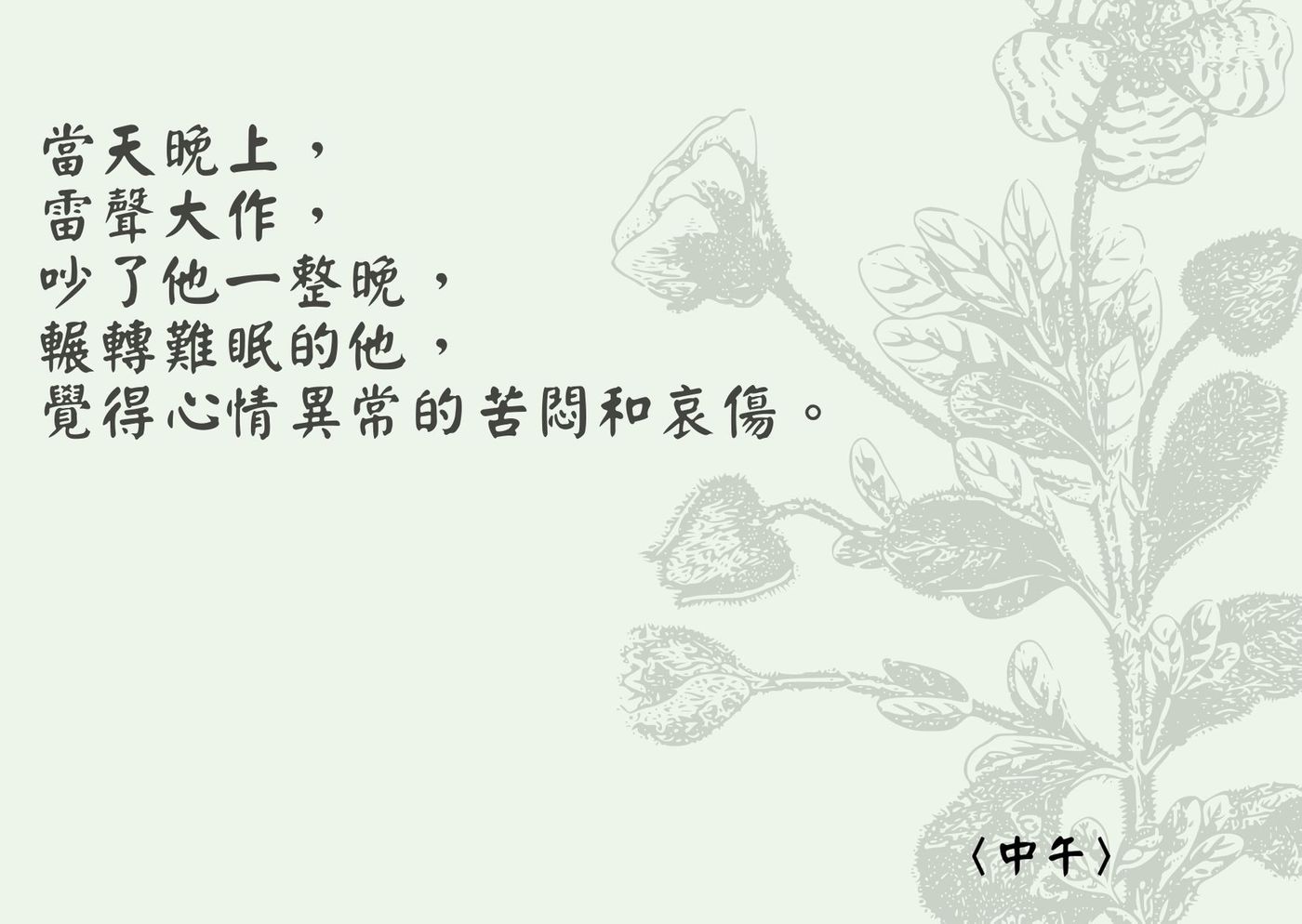阿公離開了。太沈重的一句話,也就沒說幾次。過了七月中,天氣還持續加溫,連悲傷都會蒸發的時候。
回家,阿公已經移放在冰櫃裡,沒辦法像那年阿罵離開還去牽她的手。離開的前一個週末最後見他,九十七歲高齡已經是身體與器官都疲憊的年紀,那天他在床上躺了大半天,如常的坐在床沿握握他手、捏捏水腫的腳掌。後來坐起,只想喝些冰涼的東西。坐了一段時間便又躺回床上。隔天還得上班,一樣握了他的手跟他說再見。
「週末我要回家啊,回家給阿公看看,免得他忘了我。」總這樣跟朋友說著,四處流浪那麼多年,他最記得我在員農的時候,也有長輩是員農畢業,阿公年輕時也會到員林賣橘子,坐他旁邊時就常忽然冒出一句「員農佔了員林一大半呢!」順著他的話,我就跟他說說學校裡的松鼠、農場裡的牛……。後來我離開,他可能一直記不清我在哪,因為週日跟他說要回嘉義的時候,他應允時總有些疑惑,不是在員農嗎?我也跟他說過換到嘉義的學校,有服飾科、美髮科、食品科,卻沒有松鼠也沒有牛,或許對動物與自然的情感較強烈,嘉家的介紹只讓他點點頭,無法讓他回憶起耕牛的壯碩與反芻。已經搭了棚架、設了壇開始誦經,進大廳看阿公躺在冰櫃裡面睡著般安祥,與每個週日道別時一樣,只是握不到他的手了。也進阿公房間看看,還沒有什麼改變。走出廳外,站在所有家人們後面開始聽經,蟬聲嘹亮,阿公都聽著。阿公在哪裡?在冰櫃?在牌位?在遺照裡?雙眼模糊著找也找不到了……
大家也好久沒有這樣聚在一起了,以往逢年過節我越來越不喜歡回去,逼仄的空間擠不下多少人,躲這也不是,躲那也不是,即使在同一空間也是滑了手機在另一個世界裡。大廳外搭了棚子,打了幾張大桌,哪張是接待、哪張是自己人、哪張泡茶逐漸有默契了,也稍有顧忌,不會一直滑手機看影片,即使坐著無言,家人們應該也該彼此陪著度過這段時間。泡了茶、沖了咖啡,甚至消暑用的可樂飲料都放了杯在阿公面前,而我們一言一語間聊著彼此最近的狀況,姪孫輩也在廳前玩耍。我看阿公照片笑得很開心。當然回家陪阿公,卻漸漸覺得回家陪這片土地上的家人。
來看阿公的親族們、朋友們很多,阿公年紀慢慢大了以後就不太出門,婚喪喜慶就由父輩再搭配一兩位年輕輩的作為代表,北部親戚傳了幾張阿公北上參加婚宴的合照,我竟然也在其中,算算日期是我在輔大時候,我那時的心態應該就是週末蹭頓飯,也難得看阿公北上走走。眾多的親朋好友來說著阿公的這些那些,我們回應著這些那些,棚下交織的言語如絲,交織成那些我們不知道的過往。只是那些人我都不太認得,還是有賴長輩們的說明,是傳頌也是慰藉。但我總不好湊過去說阿公明明說不喜歡貓,但還是會顧著貓飼料讓她們吃完。也不好去說阿公會將空的小餅乾袋甚至糖果包裝仔細打結才丟掉……
對我而言是成真的恐懼。阿罵與幾位媽媽那邊的長輩過世後有越來越真切的感覺,人是會死亡的。電影或生活中出現這種情境總讓我憂心,即使知道是一定會發生的事。這幾年講述〈蘭亭集序〉中快樂的消失與生命的消亡,舉了新聞中的例子之後我也會說我很害怕阿公離開,甚至是身邊每一個人離開,但怎麼會有例外呢?有些學生可能驚訝怎麼拿自己阿公舉例,或許說出他經歷過的悲傷,或許心有所感,也或許我自作多情,同學眼裡應看到的是我的擔憂與恐懼。會是什麼景況呢?這些人要是真的離開了?
只好珍惜,珍惜這片土地與身邊這些人們。國中時候鄰近的田地闢成外環道,奔跑嬉戲的土地開發大半,對面沙沙的竹林也消失,放紙船的灌溉水渠成了柏油路,阿罵帶著我們穿越田間小路去遙遠的夜市買蜜餞,週末回家到處撒野還能有滿桌蔬菜糖果餅乾,一直還長不大的小孩每週末還是回去,看這些花草樹木阿貓阿狗、老鼠蝸牛。週末回去蹭杯茶聊聊天,聽長輩說誰誰誰的事情,即使我還是不太認得。看堂妹們成家也帶了小孩回來,都是這片土地上的人與事,變著變著,有留下什麼?能留下什麼?













阿公離開前幾週總算裝了冷氣,一則因為阿公常說要吃涼的,再則天氣真的越來越熱,通風不是很好的紅磚矮房跟三溫暖一樣,曬一整天晚上還有34度。真正打動阿公要裝的理由是曾孫們回來只能躲在車上睡覺,屋裡太熱,大人小孩都不太能休息。有了冷氣,總能回去泡茶聊天一起喝綠豆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