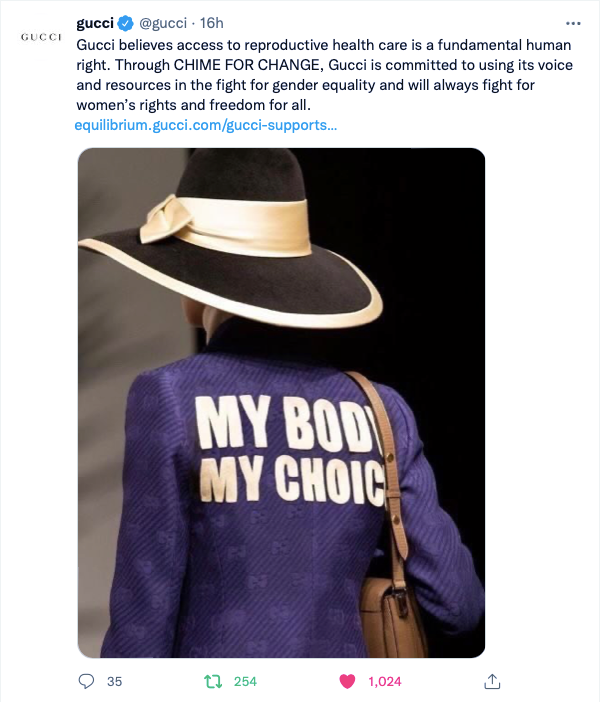美國墮胎權爭議釋憲後,最切時的女性生育自主權寓言
宛如《瘋狂麥斯:憤怒道》加上《使女的故事》
在這個世界生為女性,只有兩種人生選項——
成為母親,或是成為罪人。
除非妳蒙起面、拿起槍, 攀向絕壁上最後的自由之土……
對於為什麼有些女人能生孩子、有些生不出來,圖書館裡沒有一本書提出解釋和說明,就連凡事都能給予解答的《聖子訓綱》亦隻字未提。柏頓說「這些婦女的身體排斥受祝福的嬰孩」,卻同時表示「耶穌關愛大流感倖存者的所有子孫後代」。如果耶穌愛我們,為什麼會讓我們的身體排斥祂的祝福?我知道史賓賽女士會說這跟女巫挑戰耶穌基督造人的設計、跟她們的邪惡勾當有關,但祂不是已經降下流感,清除這個世界的邪惡了嗎?為何獨獨留下女巫?我並非不信聖子耶穌,我跟其他人一樣虔誠禱告。每當我感覺害怕或感激或痛苦的時候,我總是禱告;媽媽生病那年,我甚至天天祈禱。但我只是覺得聖子耶穌的教誨不足以解釋這個世界罷了。
不過我倒是在圖書館找到一本書,這本書的作者(艾德華.樂福醫生)宣稱他能解釋不孕及其他毛病起源。我聽過他的名字,因為鎮上的幾位女士手邊有他寫的一本小冊子,內容跟運動、心理衛生有關。圖書館這本叫《淺談疾病與遺傳》。起初我讀得津津有味,但後來,樂福醫生斷言不孕、腳掌內翻和其他許多疾病都會經由血液,從祖母傳給母親再傳給小孩。「若某女子不孕,」樂福醫生寫道,「通常她的阿姨或近親也會有人不孕。有點像是某種家族傳染病。」這使我開始擔心我的三個妹妹,暗自希望費爾查德的人還沒讀過、或根本沒有這本書。讀到後面幾個章節,我發現樂福醫生陳述的都不是事實:譬如他表示黑白混血的孩子會因為「血統不相容」而身體虛弱、容易生病。醫生還放上幾張畸形綿羊和山羊的圖片佐證,表示這種疾病乃是非互補血統雜交所致。
我曾兩次在寇拉頓協助媽媽為黑人母親與白人父親的嬰兒接生,孩子都很強壯健康。不僅如此,我還知道即使雙親都是白人,依舊無法保證嬰兒能免受虛弱或畸形所苦,因為費爾查德有許多白人家庭的小孩不到一歲就死了。我越往下讀,就越常想起鎮上某些女士的迷信:她們宣稱,光是和黑人同吃一頓飯就可能害白人得到流感。我把《淺談疾病與遺傳》塞進後面的書架,旁邊是一本講燕麥粉好處的書。
「我們可不可以再多訂一些科學書籍?」我問圖書館管理員湯瑪斯修女。
修女年約四十。在不同光線角度下,她的臉能從醜陋瞬間變得十分美麗。蘿絲修女不清楚她為何進聖子姊妹會,不過,她聽說她是帶著手銬被警長送過來的。
「這圖書館是我自己建的。」湯瑪斯修女答道。「芝加哥醫學院學生會用到的書都在這裡了,說不定還更多。你還想看什麼?」
「我想知道疾病是怎麼來的。」我說。
「那你可以去看洛里的《流感傳染手冊》,應該在窗戶那邊,在死亡紀錄底下。那本書也有提到風濕熱。」
「不是那種病。」我說。「我想知道不孕是怎麼造成的。」
湯瑪斯修女把手肘抵在書桌上。
「書販應該能幫我們弄到那本新出的、講生殖系統問題的小冊子。」她說。「但是不便宜喔。」
離家時,媽媽給了我二十個金鷹幣,後來全被馬車伕拿走了。他說是車資。
「我身上沒半毛錢。」我老實告訴湯瑪斯修女。
「沒關係,」她說,「你可以替我工作。」
從那天起,我把所有空閒時間都投入儲藏室的抄寫工作,將書籍內容謄在一張張粗草紙上。這些紙薄得一不小心就可能被筆尖劃破。我寫了整整三天,這才赫然看清我謄寫的內容。
這本書的開頭並不特別,首章講的是腹絞痛和經期紊亂。起初我讀得有點生氣,因為女人最大的問題竟源自每個月持續幾天的小痛楚;不過,抄寫熟悉的藥草名尚能稍微撫慰我的情緒。第二章談到紓緩熱潮紅和停經憂鬱的一些藥方。來到第三章「月經遲來藥方」,不讀內容我也知道這章在講什麼。
我十二歲那年,蘇珊.米爾斯來找我媽。驚惶忐忑的女孩我見過不少(譬如私處痠痛、懷孕出血、眼周或手臂出現瘀青等等),但蘇珊─她一直都是個陽光女孩,有說不完的話,那年她剛好來到適合婚配的年紀─她嚇壞我了。那天,她像鬼魂一樣走進我家,步伐輕到沒有聲音,眼神渙散。
「我晚了一個月。」她說。「可以請您幫忙嗎?」
我不曉得她需要什麼,但媽媽知道。她說。「你確定嗎,蘇珊?如果你需要錢─」
「我不需要錢。」蘇珊說。
「如果是因為對方已婚,你知道這沒關係的。他的妻子或許會很生氣,可是現在你懷孕了,大家都會支持你。如果你希望他帶你回家,他就必須這麼做。現在是你說了算。」
這時,蘇珊看了媽媽一眼,那個眼神令我終生難忘─徹底、全然的鄙視。
「瑪努森太太,」她說,「如果你幫不了我,直說無妨。」
我以為媽媽會生氣,她非常討厭講話不禮貌的人;然而她只是點點頭。「請你把我說的背下來。因為我不會寫給你。」
於是,她描述要怎麼前往牛津鎮理髮鋪,請蘇珊表明要找一位名叫「薩羅妮亞」的女人,另外還要帶上五十個金鷹幣─那是五倍於媽媽為人接生的費用。
後來,我問媽媽蘇珊要去做什麼。她告訴我:雖然學校沒教我們怎麼做,但確實有法子能終止懷孕。不過方法非常危險,因為不論是接受或執行的人都有可能去坐牢,甚至落入比坐牢更糟的命運。所以,如果有人選擇這麼做,肯定是她遇到了非常、非常嚴重的情況。
「所以蘇珊到底怎麼了?」我問。
媽媽說她不知道。不過接下來那三天,我看見她多次和她鎮上的朋友卡特太太、懷特太太和巴洛太太咬耳朵,竊竊私語。蘇珊從牛津回來後,媽媽把一位礦工介紹給她;礦工娶了她,帶她離開費爾查德、前往銀礦區。直到我離開鎮上以前,蘇珊沒再回來過。每當鎮民酸言酸語,表示米爾斯太太很可憐,竟然再也見不到她唯一的女兒時,媽媽的眼神總會變得十分冰冷。
「我知道那本書在寫什麼了。」我跟湯瑪斯修女說。她正在重新排列架上的聖人傳記。克蕾門汀修女每次都把書弄得亂糟糟的。
「所以呢?」
我不知道我該不該怕湯瑪斯修女。她讓我做這些事,其實有可能會連累我,害我被院長修女盯上。我在聖子姊妹會的名份還不確定。我還沒宣誓,也知道院長隨時都能把我踢出去,這樣的話我就沒地方去了;所以我給她一個我自認最安全的答案。
「院長知道嗎?」我問。
湯瑪斯修女微微一笑。她的笑容並不冷酷,但我也看不明白。
「如果你知道院長知道哪些事,你一定會大吃一驚。」她說。
這個答案並沒有讓我放下心中的大石頭。
「我可不想被送走。」我說。
她示意我坐下來。晚禱的時間快到了,窗外天色已暗;圖書館空空蕩蕩、只剩我們倆。幾縷髮絲從湯瑪斯修女的頭巾底下鑽出來,散發麥金色光芒。
「你知道我為什麼會來這裡嗎?」她問我。
我搖頭。
「我跟著我母親學習,就像你一樣。」她說。「但是我母親跟你媽媽做的事完全相反─不論是女人、女孩,她們有了麻煩就來找我媽:我媽會替她們墮胎。」
我點點頭。表面上我似乎一點也不驚訝,其實正好相反。我一直以為,修道院的每一位女性都跟我一樣生不出孩子;至於當年的那位「薩羅妮亞」(就是蘇珊去牛津求助的女人),我把她想成老巫婆似的模樣:指甲長、牙齒尖,就像我每年十月都會拿來嚇珍妮和茉莉的那本圖畫書裡的人物一樣。但事實上,這位幫人墮胎的女子極有可能跟我媽媽背景差不多,也可能有自己的孩子。
「警長逼我親眼看他們吊死我母親。」湯瑪斯修女說。「鎮上的每一個女孩都必須到場觀刑:這就是背離聖子耶穌和聖母瑪利亞的下場。我媽就是最好的例子。」
她的語氣冰冷苦澀。冷得令我血液發涼,苦得彷彿嚐得到味道。
「至於我,警長給了我兩個選擇。」她說。「要不坐牢,要不進修道院。我選哪個對他來說都一樣。反正肯定不會有人娶我,我也不可能有小孩。我終此一生都不准跟一般百姓往來。」
說到這裡,湯瑪斯修女笑了。「這不也算坐牢嗎?」她說。「所以你別擔心,你已經在牢裡了。」
我其實可以拒絕幫她。我大可請她找別人抄寫,把我的閒暇時間拿來跟著蘿絲修女研讀《無婚女子每日祈禱書》;但我也十分好奇。我想搞清楚這位來自牛津鎮的女子到底知道什麼:她知道的事竟如此危險,並且鮮為人知到連媽媽都不肯告訴我。於是,我在上帝之家開啟我的犯罪事業:但我手裡握的不是槍,而是會漏墨的筆;我的獎賞是書,不是銀幣。
我在湯瑪斯修女的藏書中讀到:快捷市有一名女子受人追求,但她不想嫁給對方,結果對方強取她的身體並使她懷孕。這名女子喝下翼莖草熬煮的湯汁,十三週後流產。
後來她跟另一名男子結婚,生養了兩個健康男孩。另外我還讀到,一名有血糖問題的孕婦聽產婆說生孩子會要了她的命,於是她只好服下艾菊油和脫水奶油調製而成的飲品;孩子流掉了,但她也因此保住性命。我甚至讀到有個女人遭她父親玷汙並懷孕,這時我才明白蘇珊.米爾斯當時為何用那種眼神看著媽媽,以及她何以遠走他鄉、不再回來。
另外,我也讀到有人喝鹼液墮胎,最後一屍兩命;喝松節油的同樣逃不過死神召喚。我還讀到有人一連跋涉三座城鎮,沿途找了七名產婆、一位草藥師、甚至還請求牙醫幫忙,但沒人願意幫她,於是她只好自己來─她用編織棒針終止懷孕,最後出血而亡。我一直以為我再也不可能覺得自己很幸運,但此時此刻,我安安全全坐在儲藏室裡看書,讀到有人流血流了一整天、從白天流到黑夜,我只覺得自己真幸運。
整本抄完之後,湯瑪斯修女把謄本賣給書販(這位先生駕著馬車,在丹佛與芝加哥兩地之間來回做生意),換了《病因論》和《婦科疾病診治大全》回來。兩本書的作者都是波尼.馬維神父,他既是神職人員也是醫生。
不過馬維神父的書很快便令我失望了。他說,要治療子宮肌瘤,可將一份培根油兌一份水飲用,可我知道這配方根本不管用。他說,孕婦如果在滿月之夜外出即可能引發早產,但就連費爾查德的老太太們都曉得這純粹只是可笑的迷信。至於不孕,神父列出的可能原因包括:性冷感或母性不佳,少女時期偏好男裝打扮,喜歡吃辣或太苦的食物,懶散,過度專注於不屬於女性的消遣或工作(譬如簿記、算帳)。
「我覺得馬維神父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我跟湯瑪斯修女說。
「可是書販告訴我他很厲害呢。」湯瑪斯修女說。「還說芝加哥醫學院一口氣買了五本。」
「那我只能說,這位書販和馬維神父的運氣都很好。」我答。
湯瑪斯修女皮笑肉不笑。
「我想我需要的是大師級人物所寫的助產書。」我說。「真正有經驗、實際接生過孩子的。」
「我來想辦法吧。」湯瑪斯修女說。「不過,如果要請書販幫我們找書,費用更高喔。」
結果我花了整整三週才賺到(或抄完)換得愛麗絲.沙佛《婦科疾病手冊》所需要的謄本數量,而且還得另外再抄六本以支付他從丹佛帶書回來的費用。然後,夏天來了。我們會在禮拜天坐在屋外草地上讀經禱告,看萬物繁衍、欣欣向榮,這時院長修女會領著我們採集天竺葵和黑眼金光菊,放進餐室各處的小瓶小杯作裝飾。小小的喜悅使我們開心地咯咯笑,輕鬆的心情甚至延續至晚茶時分,即使是幾句無厘頭的笑話都能引我們發笑:譬如瑪莎修女的教理學奇差無比,她竟然以為耶穌會創始人「聖依納爵」是黃鼠狼的守護聖人;換作是我以前那群朋友,她們說不定根本笑不出來。但我心裡始終五味雜陳。在修道院裡,我的心情越來越平靜,每天早上醒來時不再會下意識地期盼看見妹妹沉沉睡在另一張床上,也不會在擠牛奶的時候偷哭了。我開始盼望九月宣誓,希望能趕快換掉身上的灰衫、改穿黑袍。但另一方面,我也察覺我的心和腦子似乎有某種空缺。我知道克蕾門汀修女和其他幾位虔誠修女會讓聖子耶穌填滿她們的身心靈,但那些故事無法滿足我,尤其是我根本不屬於那故事的一部分:我不僅懷不上孩子,被關在修道院裡的我甚至沒辦法去做媽媽訓練我做的事,沒辦法幫忙把孩子帶到這世上來。因此,我只好認真思索我能從沙佛女士的書裡學到什麼。
當然,我依舊認為沙佛女士或許有辦法治癒不孕。我想像自己在聖子姊妹會附近的林子裡採集多種草藥、樹皮植莖,仿效媽媽將這些材料泡成藥酒,以備不時之需(草藥師傅有時候拿不出這些藥材)。但我要怎麼知道這些療法有沒有效?我大可再找一個男人,一連數月在正確時間與他交媾;假如我的肚子還是一丁點消息也沒有,我不可能會知道問題是出在藥方、他、或者我身上。就算我被治好了─假使我當真受孕、生了孩子,我會想再回到原本的生活嗎?我會抱著孩子,以勝利之姿重返費爾查德嗎?我甚至可以想見媽媽的表情:如果我帶著她的外孫回家,她臉上必定會先閃過震驚與困惑的神情,然後才允許自己展露笑顏。光是想到這一幕我就心痛。然後,驚喜消逝,眾人請求我原諒,就連我丈夫也哀求我重新接納他(但我可能會拒絕他。有時候,在夜深人靜時,我還是不太確定自己的想法)。我想,如果有機會重拾為人妻、為人母的安逸生活,我認為我應該不會就此滿足。
因為我想搞清楚不孕到底是怎麼回事。我想了解胎兒如何在婦女體內發育,以及究竟有哪些子宮內或子宮外的因素可能阻撓受孕。唯有如此,我才能感受到只有在「了解我必須明白的道理」之後才會擁有的平靜,並且把我習得的知識傳給別人。因為媽媽說過:「你不能直接推翻別人的信仰,你得給她們一些能替代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