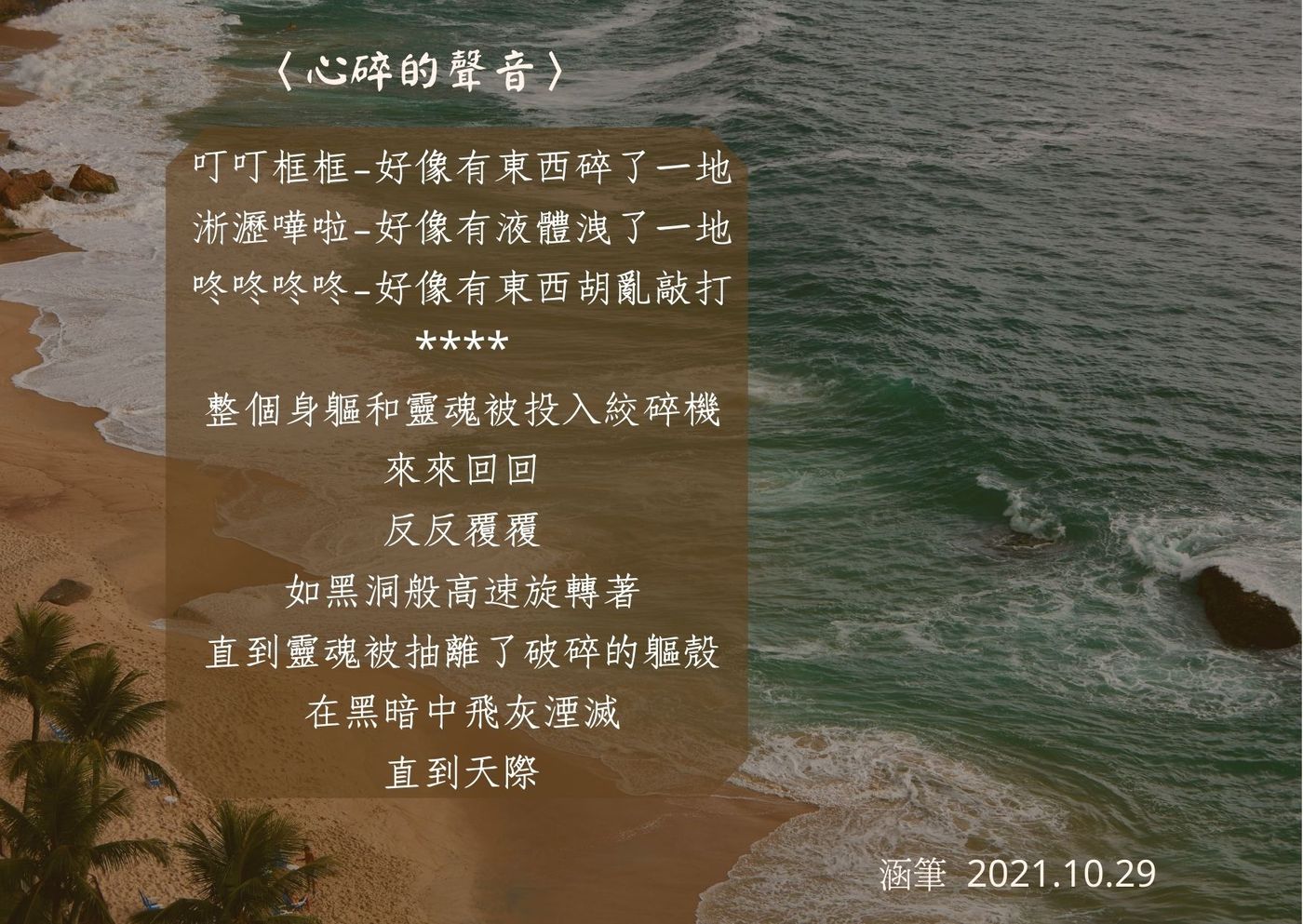在談話中,他偶然會冒出一句:「我沒跟妳說過嗎?」接著不待回答,就繼續述說自己這幾天的生活和工作。這虛偽的一問馬上讓我心情低落。這代表他已經和另一個女人分享過這件事。她就在他身邊,永遠能第一個得知他遇到的事,微不足道的、重要的、所有的一切。而我呢,頂多排在第二順位。我已經喪失即時和他分享一切的權利,讓情侶之所以為情侶的分享--腦子裏的想法、所有的遭遇。「我沒跟妳說過嗎?」這句話將我劃歸到偶然相見的親友圈。第一個和他分享每日生活點滴、地位無可取代的那個人,不再是我。「我沒跟妳說過嗎?」這句話將我貶為可有可無的聽眾。「我沒跟妳說過嗎?」這句話的意思是:我沒有必要告訴妳。
書寫中的我也在暴露自己的執迷和痛苦,但那與親身到拉普大道走一趟所面臨的暴露迥然不同。書寫,就是不被看見。將我的臉孔、身體、聲音--也就是構成我這個人的一切特徵,暴露在某個人眼前,讓他目睹我的頹喪消靡、自暴自棄,我怎麼樣也無法想像,甚至感到殘酷。相對而言,正在書寫這些文字的我,對於暴露、探索自己的瘋狂執迷,並沒有感到半點不自在,頂多是不在乎。老實說,我根本沒有感覺。我只是竭盡所能的去描述嫉妒啃噬下的所思所為,將私密、個人的內在情緒,那些無以名狀的種種,轉變為清楚、具體的東西。我的文字裡所表現的不再是我的慾望、我的嫉妒,而是嫉妒和慾望本身。寫作中的我像是隱形了。
談論日常生活的時候,他總是小心翼翼,只使用「我」,聽在我耳裡卻變成「他和她」。將他們兩人相繫的不再是性行為(那已成為慣常的行為,不斷在沙灘、辦公室一角和賓館房間上演的激情),而是她中午替她買的長棍麵包,堆在洗衣籃的內衣,兩人邊吃義大利肉醬麵、邊收看的夜間新聞。在我視線所不及的地方,他慢慢被馴化、收編。兩人共享的早餐、放在同一個杯子的牙刷,就像互相在對方體內受胎,在我看來,懷著兩人愛情結晶的是略微發福的他。共同生活有時會讓男人變胖。
我和他交往時所恐懼的便是不知不覺養成的日常習慣,然而,這些日積月累的習慣,顯得如此根深蒂固、不可動搖。所以有些女人非得讓喜歡的男人搬來家裡不可,哪怕將來會吵架、不滿對方,甚至過著悲慘的日子,也在所不惜。
Annie Ernaux,《L’Occupation》,張穎綺譯,大塊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