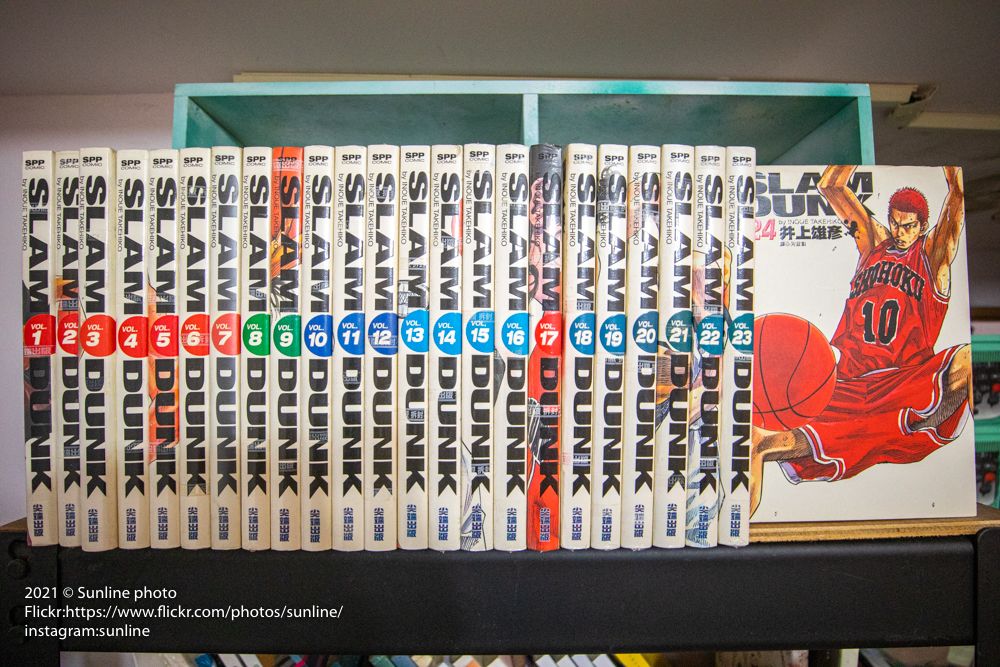在我還很小的時候,大約大學時期,叛逆、孤僻,不通人情,只喜歡躲在圖書館,一心一意的沈溺在書堆中,直到翻到鄉土文學,仔仔細細的研究歷史脈絡,終究被電影《多桑》男女主角的鄉土味吸引後,才在《悲情城市》裡頭注意到作家吳念真。
當時,可以為了重複看《多桑》,蹺掉主修的課。
讀他的書通常有一種神奇的感受,且在三十歲以後,這種莫名的被認同感就會冒出來,在每當遇到瓶頸的時候,令我不自覺的忍不住到書桌去摳它的書脊,接著側躺在床上,慵懶的翻閱。即使已經翻閱無數次。
讀吳導的書跟普世呈現的不一樣,有人情世故、有關點,有處事哲學,還有學不完的做人。
做人做到某個極度厭煩的級數時,讀他的書就是一種享受。
吳念真導演在書中是這樣解釋的,在人生中會遇到許多生命的曲折,也許是怨懟、怨恨、屈辱,不滿「但最後幾乎只剩下笑與淚、感動和溫暖」,剩下的都會煙消雲散。
「當你有一天什麼都不記得的時候,至少還有人會幫你記得這些人,這些事。」
記得那些人、記得那些事,不知不覺中這一切成了生命的刻痕,甚至是生命的一部分。觀察著百態,體會炎涼,而這也是我在田野調查中感到最快樂、最豐沛的回饋,在與人對談的過程中,我彷彿向是在對每一次拋在湛藍的空中停留於記憶片刻發自內心的讚嘆,那代表帶著期待被發揮、渾圓飽滿的故事致敬,回應無論虛或實、強與弱,瞬間感受到的情緒都是確切的,以至於在接受到喜怒哀樂的剎那,都竭盡所能的用最誠摯的態度去面對。
因此,捧著滿身尿騷味窩在輪椅上阿桑的手;與流浪漢老伯說笑著遞上禮物;對滿身汗臭味缺牙的大哥遞上冰水、對法庭上失去愛子痛哭的母親擁抱,替跌在家門口前爬不起來的老伯攙扶,沒有要求回饋的幫忙,義不容辭的大老遠只為了幫人圓夢...這種旁人看來吃力不討好的事,像是一場又一場荒謬卻無比真實的故事,回過頭望,自己竟都參與其中。
猶記得二十出頭歲,有一年開著車在往返中港路上的深夜,電台微微弱弱的播送著詹雅雯的《北極星》。
訊號隨著76快速道路斷續著,但臺語演歌技巧的轉音,悠然坦蕩在幽靜的車廂。
當時阿嬤剛倒下,什麼都要資源,我說一不二的性格,為此還跟老母大吵一架,那是離家出走的概念,獨自搬到外地後第一次想嘗試當編劇、當作家,離經叛道的我將她氣得火冒三丈,要我死出去,不要再回家。
但我後來還是有回家,臨走前,還塞了三萬塊給她。
那年的我骨子裡是有傲氣的,卻被一首歌喚醒了脆弱,死死的握著方向盤,對著擋風玻璃哭得唏哩嘩啦。
清晨才到家的我,在早上五點的租屋處前路口被警察攔查,他要我搖下車窗,交出身份證,核對照片與本人的模樣。當紅著眼眶濃妝豔抹的女駕駛一開口,嗓音沙啞,年紀相仿的警察竟愣了一下,才匆匆放人,叮囑趕快回家。
我也成了他人生旅途中的這些人,那些事。
弄文化聚落,是想聽到更多人傾吐自己沒有邏輯、無邊無際的人生歷程。
其實,也許內心本質更想看到的,是那顆總能呈現人間無數,拍攝出些許哀愁的長鏡頭下,瀰漫燦笑的你我他吧。
※素材取自於侯孝賢1989年《悲情城市》劇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