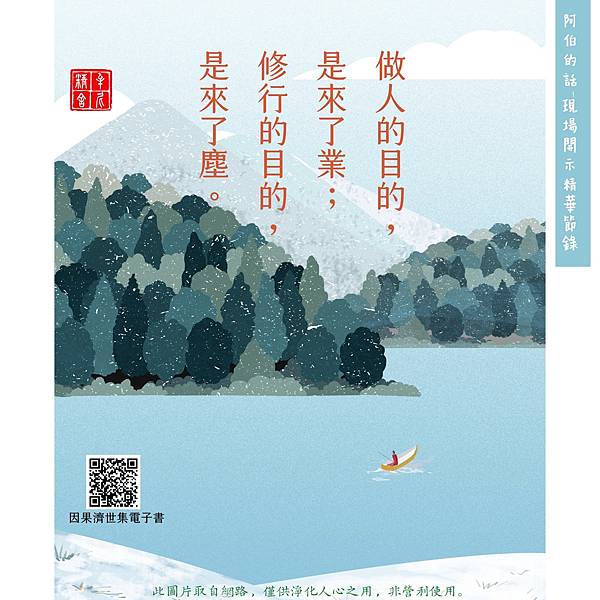我在芳苑鄉路上國小學感受到最深、最深的體悟,是那裡的孩子比起二林市區裡的學童,顯化的情緒明顯穩定許多,老師通常也不太會罵人,當你板起臉孔,用很嚴肅的表情看著他們,告訴他們真理,所有看似大事的紛擾,最終都會在太極的黑白之間演變成玄,然後化為虛無。
他們會安靜的聽,偶爾反駁幾句,但最終塵埃落定。
很喜歡這種感覺。尤其是其中一位小女孩熟門熟路的在校園找果實的任務中,遞給我無患子的種子時,那副撞見我一無所知,顯得比長輩還博學的驕傲:「老師,這個果實像不像漂亮的手串珠子?」
「妳很厲害,找得到這麼漂亮的珠子。」我只看到一串串裹著綠色外皮的無患子,直到捧著她遞給我的果實,暗紅色摻著黑,漆亮、漆亮的模樣,驚呼著:「我也覺得它很漂亮,我也想帶它回家,只可惜我們的時間還要拿來上課。」
「老師,妳放假可以常來,我也希望妳一直在我們學校。」
我摸摸她的頭,不停的陪他們在校園找尋果實。在文化部的兒童文化館,陪他們看了『100顆種子』的故事,一邊測試他們的語文閱讀能力,他們對於松果種子完全消失,到最後仍得以生存成長為森林的不可思議充滿了未知的想像。比起中、高年級,低年級的穩定度反而更高,似乎不是因為我對他們的管理關係。
而是,在溝通與陪伴的教育之下,芳苑鄉路上國小的師長們都有共識,於是不需要太用力的情緒去表達,施教者與受教者的橋樑一直都在。
在陪伴孩子的過程中,他們天馬行空,也會黏在我的身旁,才來教書五天,他們已經有人錯喊我『媽媽』。
「媽媽,我想說... ...」那孩子突然語塞,「說錯了。」
當我緩緩的回他怎麼了嗎?他訝異的看著我,我便回他:「有很多小朋友也都會叫我媽媽,我也是一個媽媽,所以沒關係。」
情緒跟情緒是會碰撞的,碰撞的刺激無法彌消,它只會不斷的被養大,像是一團被遺落在角落的毛髮,你只能試圖去撿起它,但不會想去梳理其中的糾結。
知道他們的描述能力不夠強之後,所有的教案課程我都延宕了一天,用雙倍的時間慢慢的去陪他們書寫『感覺』,感官上的一切不應該用情緒來表達與交流,我認為他們是可以寫出好文章的。至少,在這樣的環境裡長大的孩子,應該更能理解萬物皆有靈的真理。
低年級的孩子們很喜歡畫圖,我也不想限制他們的作法;愛唱臺語歌曲的小男孩,雖然不愛書寫,但一拿起筆,字體是學童中數一數二的漂亮;喜歡調皮搗蛋的,也不愛書寫,但一鼓勵他把想說的話寫出來,洋洋灑灑成了一頁雙面還寫不完的心得感想,小女生中規中矩的寫出了文章,但她其實最想做的事情反而是研究我手上的松果到底長什麼樣......大家都用自己的方式在進行所謂的「課程教學交作業」,而我在其中觀察著,像是一個紀錄者,又像一個冒險的實踐家。
這群孩子最後會長成什麼樣呢?
彼日要上課前,我被校門口的風景給吸引住了。
能看見山巒那樣清新的日子,我們能不能做到一直快樂呢?
走到走廊時,一隻肥大的蛞蝓趴在廊道上,孩子圍在牠身旁,問我:「老師,這個蛞蝓,妳想牠會怎麼了?」
「我不知道,但我們可以選擇不要傷害牠。」腦子裡瞬間想起兒子在中正國小時提起下課時的慘況;同學將樹幹上的獨角仙撥到地板上,然後奮力的踩死牠,當下那畫面震撼了我的兒子。他告訴我,
「媽媽,妳不是告訴我說不能傷害動物嗎?我都有做到。可是我告訴那個同學,我媽媽說不行這樣,他卻推我、還打我!」
但眼前的這群孩子只是默默的圍著牠,看牠緩慢的爬行,扭動身軀、擺動觸鬚,卻不知所措的樣子。
此時,校長先生突然走到我身邊,和藹且親切:「老師,妳覺得該怎麼做?」當我還訝然他怎麼會請教我這個問題時,當下反應卻隨口脫出:「將牠放回草叢是最好,那裡是牠生存的地方。」
在我還在思考一切來的突然的同時,校長先生笑咪咪的從一旁的牆邊取起掃帚,輕輕的把蛞蝓掃進了畚箕,用著理所當然的步伐與動作解釋了對生命的尊重。
「讓牠回該去的地方。」校長始終揚起嘴角的對我笑。「謝謝校長!感謝你!」我忍不住這麼說著,心裡波瀾四溢,激動的想泛淚,當我領著一群孩子走進教室時,從家裡的爭執開始造成我內心創傷與紛擾彷彿瞬間消失了。孩子尊重生命的能力這麼強大,他們閱讀的強度這麼強大,那種對無常的淡然與生活的好壞都這麼的實在,沒有一絲對生命教育的苟且,他們正在做著。
在小小的校園裡,他們沒有官腔、沒有包袱,沒有功利主義,我們在嘻笑中學習,一切緩慢的順理成章。
他們不用一直選擇競爭,不用一直被挑戰,學著打開感官,把感受描述出來,然後輕鬆自若的述說自己想說的話。
教育不該只有一種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