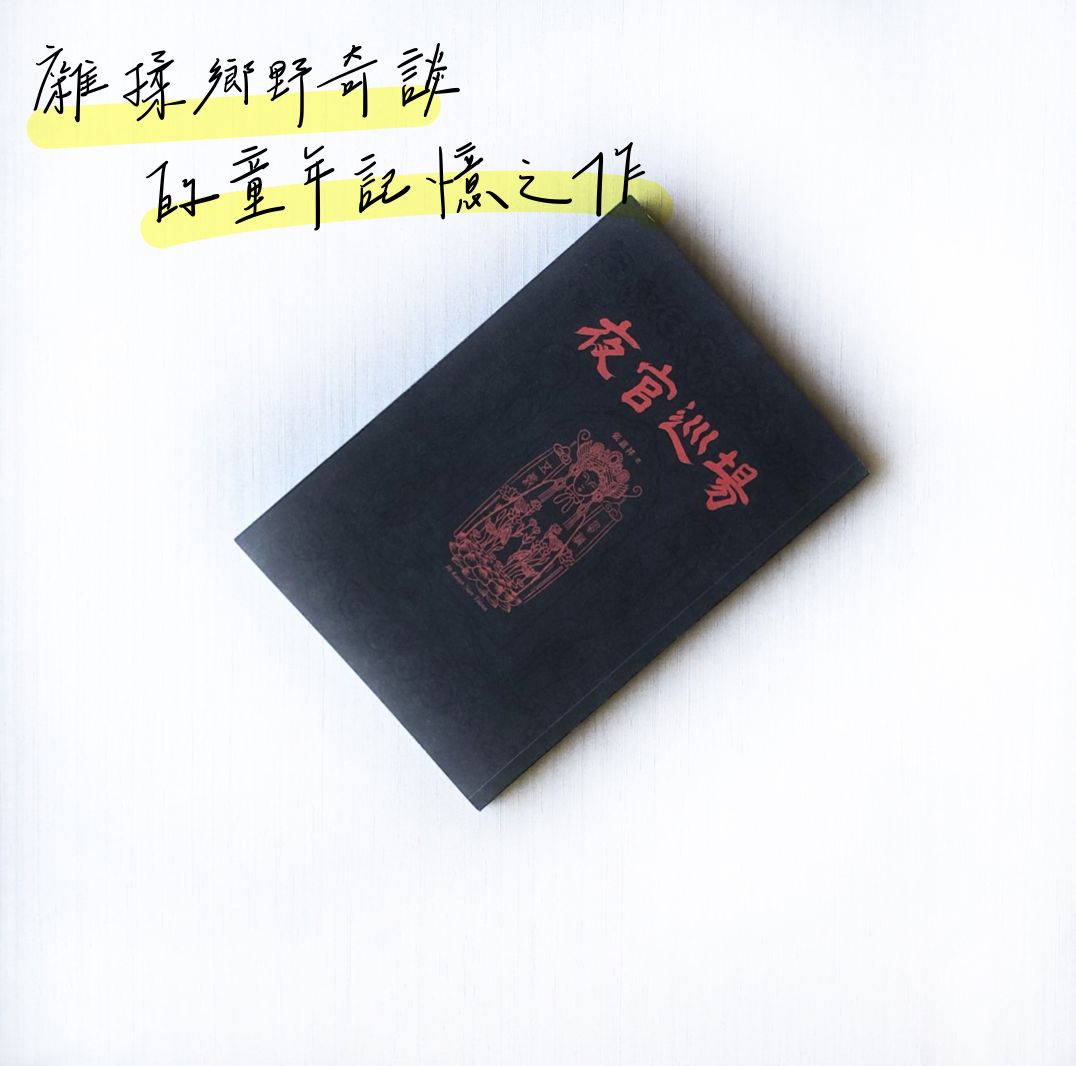童年的技憶
更新於 2023/06/11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小時候上天入地,上能爬樹摘果子搗鳥窩下能池塘抓泥鰍采蓮蓬,放牛是基本功,但在鄉村能幫父母下地插秧割草,上灶燒火做飯才是能幹的女娃子。插秧就是玩,騎著秧馬在水田裡劃水,燒火做飯也是僅限於父母在地裡忙活不過來,屋裡沒人做飯餓得只能搭個椅子在灶臺上炒個現飯(剩飯),做飯是女孩子要學的男孩子不用學。
我倒是學到一些男孩子的技藝比如抓蜈蚣和釣黃鱔。立春驚蟄過後,天暖燥熱那幾天夜裡蜈蚣們要出來開會了,老輩人說是蜈蚣們的相親大會。要知道蜈蚣是一味中藥,到了抓蜈蚣的季節,街上路邊都是收蜈蚣的攤販,蜈蚣的市價每年都有波動,產量多時幾毛錢一隻,供不應求時一到兩三塊錢一隻都有。春耕時父親白天播種晚上就頭戴探照燈,一把火鉗,一個葫蘆就上山去了。那時一到掏蜈蚣的時節,晚上日頭落下月亮爬上山崗,男女蜈蚣們就從石縫裡爬出來相親了,村頭村尾,山坡上田埂上,都是手電筒的燈光穿梭著,就像電視上月黑風高夜國軍在月臺抓間諜的場景,只是這些燈是用來抓蜈蚣的,我們叫“照蜈蚣”。第二天天一亮,村頭便聚起一群男女老少比賽昨夜照蜈蚣的收穫,誰的蜈蚣又大又肥,誰掏到的蜈蚣數量最多,盛況可以稱得上是我們那獨有的“蜈蚣節”了。蜈蚣喜歡在石頭縫裡安家,每次蜈蚣節已過,山上凡是亂石裸露,像是野豬刨過的地方,必是掏蜈蚣的人留下的狼藉。畢竟野豬多年前就已經絕跡了。
記得有一次父親在屋後豬欄旁邊抓到兩隻正在談情說愛的蜈蚣,我們可高興了,竟然在家門口能抓到蜈蚣而且是一箭雙雕。掏蜈蚣有經驗的,不僅戰績可觀而且從不會被蜇,要知道蜈蚣是五毒之首,被它的齶牙咬過後毒液滲入皮膚,疼的紮心。有一次我們一群小嘍囉跟著“山大王”—然然—一個比我們大四五歲的孩子王,一時興起去帶我們去山上學抓蜈蚣,然然是抓蜈蚣老手,我那憨厚老實的堂哥潤生就被惱羞成怒的蜈蚣給蜇了,頓時就嚎啕大哭,然然立馬幫他把手指頭的“毒血”吸出來,叫潤生不要告訴他媽是被蜈蚣咬的,要不然潤生母親是要跟然然母親杠口的(吵架),當時看著潤生烏青的手指頭和一臉痛苦的樣子,我們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娃子才知道才見識了蜈蚣的威力再也不敢輕易玩蜈蚣了。
抓蜈蚣是要講究技巧的,我見過父親抓蜈蚣,找到蜈蚣以後先用火鉗鉗制住蜈蚣的身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食指拇指捏住蜈蚣的頭,只要速度夠快就能先發制蜈蚣,即便它怎麼扭著身子纏著人的手也轉不過頭來咬到你,因為它的頭已被牢牢控制住了。抓起來丟進裝了酒的葫蘆裡塞住蓋子就完事了。有的人不捨得酒就用摻了洗衣粉的堿水,丟進去不多時蜈蚣便一命嗚呼了。白天就把蜈蚣拿出來用竹簽支起來曬乾。有幾年蜈蚣行情很好,漲價的厲害,村裡的蜈蚣都要被抓絕跡了。只能去鄰村掏去。後來興起挖蘭草,據說是城裡人愛起野生蘭草,供不應求,蘭草行情比蜈蚣還賺錢,好品相的蘭草能賣到一株四五塊到十幾塊不等。蜈蚣們才免遭滅族的厄運。蘭草是喜幽靜的,須得到深山林壑裡才能找到,所以那段“蘭草熱”時期,山裡被挖的傷痕累累,夏天大雨一來水土流失嚴重。直到後來上面下達政策不准挖野生蘭草了。
在我的鄉村,春天除了春耕插秧便是靠蜈蚣和蘭草糊口,到了夏天,除了照料水田裡的稻子就是去田溝裡釣黃鱔了。一到暑假,基本上全村的男孩子都去釣黃鱔了,那是夏天裡極大的樂趣了。城裡人的餐桌上盛行吃野味,除了名貴的野生團魚,甲魚就是野生黃鱔了,而我家鄉的水田溝渠裡到處都是黃鱔,行情好時一二十塊一斤了。黃鱔在城裡有個更好聽的名字叫“鱔魚”,雖然長得像蛇的遠房兄弟,卻性情溫和,沒有攻擊性,屬於魚類,眼睛很小(我們那裡形容人眼睛小就說那人長者一雙“黃鱔眼”),土黃色的身子跟泥鰍一樣光滑,也很擅長鑽洞,到了冬天田野乾涸它便在地底的洞裡冬眠,平時在水裡吃藻類植物,對最愛吃的蚯蚓沒有抵抗力,很容易被釣到。我從父親和堂哥那裡學會了釣黃鱔的本領後,每天下午三四點就拿個鋤頭或鏟子去屋後,菜園子的牆根空地裡挖蚯蚓,要揀那種黑大而肥就跟上了黑釉一般得蚯蚓,陽光下身子能反射五彩斑斕的光澤的黑蚯蚓,我們叫這種蚯蚓為“臭蟲鱔”,是絕佳的釣餌,它的近親“香蟲鱔”是魚愛吃的釣餌,膚色是暗紅色的。挖到的臭蟲鱔帶回家在火灰(灶堂裡的柴灰)裡面滾一滾,就跟驢打滾一樣,蟲鱔就動彈不得了,它的皮膚受不了強鹼灰的灼燒,用稻草秸稈在竹簽或小木棍上把蟲鱔五花大綁,我喜歡用青草葉子將蟲鱔一圈一圈綁起來最後系上個完美的蝴蝶結,以示對蟲鱔以身獻祭於黃鱔的禮節,黃鱔見了說不定會眼前一亮爭著入籠呢。將綁好的釣餌放進竹篾籠子裡,竹條編織的籠子有的很精緻的,只是貴一些。有鄰人發明了簡易自製的籠子,把空的農藥塑膠瓶子紮幾個眼,剪掉瓶底套上漏斗形的竹網,那竹網是捕籠的關鍵,黃鱔被裡面的肥餌吸引遊進籠就很難出去了,只能享用最後的晚餐等待命運的審判了。
到了黃昏太陽快落山天氣不怎麼悶熱了,便開始扛著十幾個竹籠去田溝裡撒網了,每塊稻田之間都是相通的,水溝起著蓄水疏水的作用。夏日的黃昏,落日的晚霞盛開在天邊,夏蟲在田野裡歡唱,稻子在結著它的穗,野草長得人高,三兩隻白鷺在稻田間悠閒地踱步,見人走近便展翅飛往山麓的梯田裡去。淡淡的暮色裡家家房前屋後炊煙嫋嫋,雲霧般飄散在山間田野。遠處山林裡鷓鴣聲斷斷續續隱隱約約。稻田裡蛙聲已經開始做夜晚大合唱的排練了,找一個隱秘安靜的田溝角落,撥開浮萍綠藻,往水深處投下竹籠,有時水邊生著一種香氣襲人的小野花便順手采了,待將所有籠子投入各處的田溝裡後就回家吃晚飯了。
第二天天一亮就要去收黃鱔籠子了,夏天天亮的早五點鐘東方已經魚肚白了,田埂上露水尚重,須穿上雨靴,如果光著腿在草叢的露水裡過,回去便要出疹子癢的難受。憑著記憶把各處投的魚籠子收起來,記性好的孩子投四五十個籠子第二天能一個不漏的收回去。從水裡撈起來的籠子如果沉甸甸的那就是有收穫了,若是輕的沒重量就是無收穫了。早晨照樣是大家提了籠子回去,比賽起誰家釣到的黃鱔最多,能賣到多少價錢,一般釣到的都是小黃鱔,不中秤。如果釣到又大又肥的黃鱔更是嘖嘖稱歎,當然有時候也有餓壞了的水蛇誤進了魚籠子。
野生的黃鱔是膽小的魚,一有風吹草動便鑽進水草叢裡,我一個很要好的玩伴,她父親會黃鱔的語言,據說是她爺爺祖傳下來的本領,有一次她帶我去她家一個秘密的池塘看他父親養的寶貝,那是一個廢棄的茅坑改成的小池塘。她得意的向我表演她父親教給她的絕技,她吹出一種很好聽的口哨,只見寂靜飄著綠藻的水面立即浮出好多鱔魚頭,似乎在回應主人的召喚,等哨聲一停,它們便冒著泡泡往水底遊去,池塘又恢復了一潭死水。我對她的這項獨門技藝很是印象深刻。
後來長大了去異鄉求學謀生,偶爾回去家鄉,家鄉的田地已经荒廢了很多,年輕人都出去打工掙錢,不再像以前老一輩要靠天靠地吃飯,或許是對家鄉生態的一種好處,至少那些野生動物可以安心的繁衍,不會面臨絕跡的危險了。我兒時的一些技藝早已退化,只剩下那些技藝帶給我童年的樂趣一直留存在記憶裡。
1會員
6內容數
留言0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