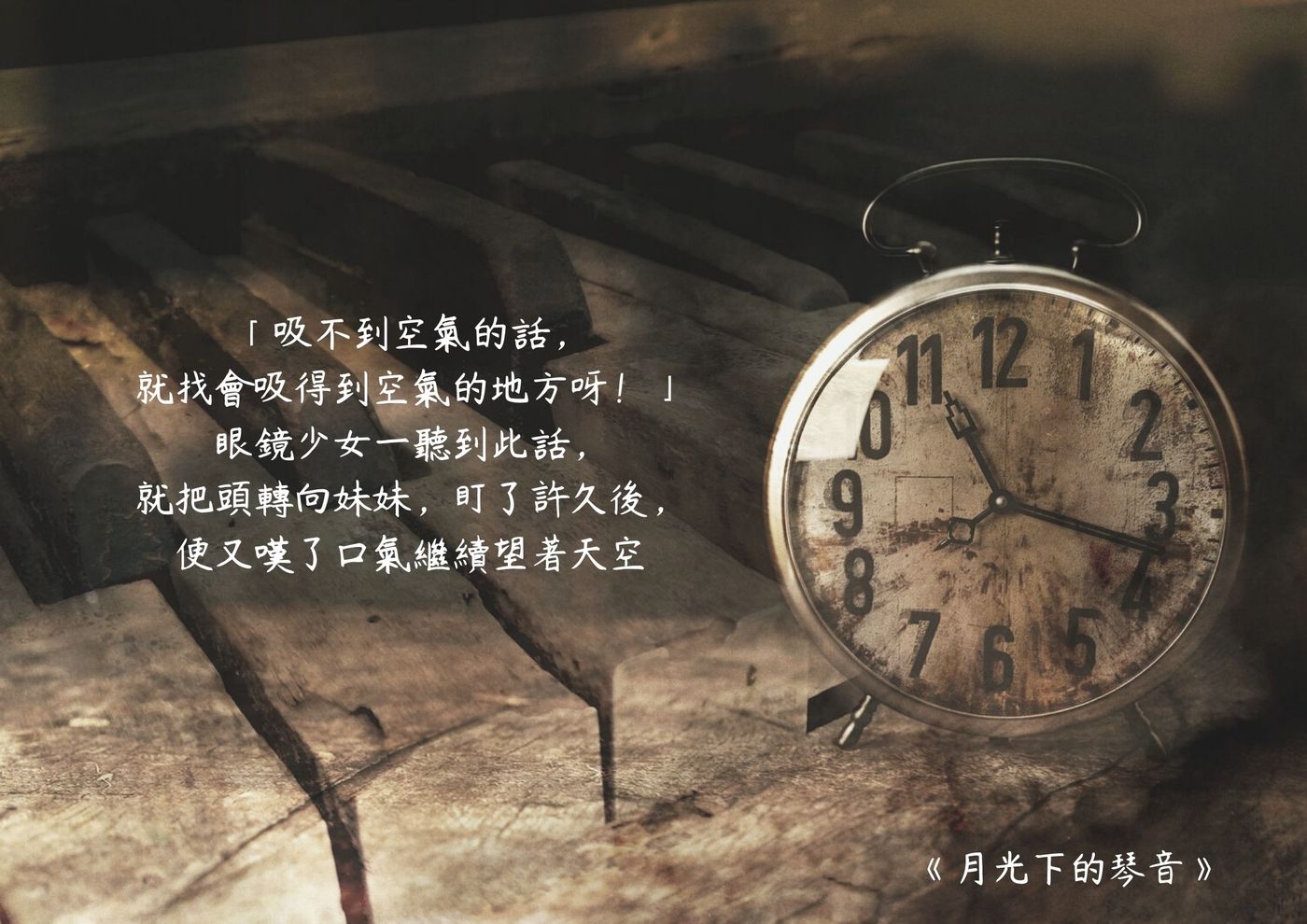1.5/ 夏熱
陳俊霖的那個眼神她還沒摸透,班導就喚她進門,並用「這孩子真讓人不放心」的眼神無聲指責她的不守秩序;鐘聲畢竟不是她廖潔琳專屬的鈴聲,如果可以,她也曾天真爛漫的想過擁有控制時間的能力,這樣學校生活會過得更順遂吧?
但她又會想倘若真有這個機會,更希望自己擁有穿越蟲洞的能力,能使空間扭曲摺疊,她可以不再擔心上學遲到看人臉色的生活,可以不再為了跑處室寫悔過書而懊惱──「如果可以」真是青春絕佳的代名詞。
在他們這些學子都還未察覺,還企盼的時候,必定從未想過有一日不再希冀這個「如果可以」,不再使用這毫無意義的句式來安撫自己無法接受現實衝擊的創傷……
坐窗邊的潔琳習慣性望向窗外,雲朵是越來越可口了,但看著又像能採收羊毛的黑羊;思緒早已飄得很遠,落到了羊腳附近,那處飄著閃爍的絲線,但人又感受不到風颳刷過的快意──被家裡嬌慣的私校同學們刻意調降十七度的冷氣正不要錢的放送,早些時候處室廣播節電都像玩笑。
──都已十六七歲的年紀,還在玩什麼對抗大人的遊戲。
潔琳自己也想笑,她也曾在十六歲的年紀以燙剪的方式對抗學校的「大人」、收獲一張要家長複查的簽名單時她是真心想嘲笑這可悲的髮禁;還過著受父母恩澤的日子,哪位孩子染燙的錢不是家人出的?
為了給董事會一個乾淨可愛又虛偽的清純形象,這些處室的大人們也是無所不用其極的規範他們。可青春不就貴在每個人未經打磨的多樣性嘛。對潔琳來說,沒有變化的人們太可怕了;所謂的進入社會是變成一個沒有感情的生命體嗎?變成一個不可表露喜好,任何情緒都會被貼上標籤:「這是一個情緒化的人」、「這人會把情緒帶進工作」、「這人的情緒反應我很不喜歡,不打算和他繼續當朋友了」……
當精神分析學派還在提倡情緒的可貴、面對情緒並不可恥的時候,這些人有再多的苦都往肚裡吞,並逼迫身邊的同伴如他們一樣:理性──如若理性是指她將擔憂陳俊霖的想法轉化成、給他安上許多似好萊塢劇本的複雜緣由,那她還是很理性的。
於椅子上坐定的潔琳本就比同齡人矮小許多,即便挺直背脊也不可能看見被走廊圍牆遮擋的校門、那有著稚嫩白皙臉蛋,聲音帶著幾分小學生童趣的男孩──陳俊霖;她想,自己一定無法猜對學弟是已踏進校園,得了處遮陽避雨的地方安歇?還是辦完事情又離開……
但對這個非正常時間到校的人,她仍下了許多假設──是身體不適?還是被霸凌……對。很有可能;她想起學弟曾被國三畢業的學弟們拉進廁所的畫面……當時她正好與國中畢業外考的同學敘舊,讓這些男同學去廁所救他;雖然潔琳自己也很想衝進去,但她早已過了可以恣意闖入男廁的年紀,不然定是抬腳踢得這群人無法自理。
那時,陳俊霖被救出來後瑟瑟的模樣使她心疼,但聽聞只是被剪了頭髮又覺得好些了。現在想來,可能他有被做什麼更嚴重的事,只是害怕被用異樣眼光看待而不敢說……
她總能幫這位學弟找無數的藉口。當然,這不純是因為他看來軟綿綿,笑起來很可愛的模樣激起她的保護欲。更多的是,他是少數能令她放鬆相處的朋友。阿布她們班的學弟妹都令她有這種感覺,唯一苦惱的是他們都太客氣了,每個喊她都帶一聲學姊。
她不喜歡以稱謂稱呼彼此的友情關係,這總令她感到生分。她與學長姊的關係則像平輩,每個人都能輕易的喊彼此的暱稱,也是這樣的稱呼令他們無形間於友情的路上邁過好幾年的相處。所以當阿布她們如此喊她的時候,她已經有了預感,有了危機意識,很可能和這群人畢業後就無法再聯繫了。無法再這麼好了……
「哈啾!」不知道班上的誰發出聲音,教數學的女班導拿其取樂,大家笑得開心,更重要的是,牆上的時鐘逼近了下午四點。
轟轟──轟轟──眼前的朋友被窗外閃光嚇得哆嗦,回過頭和潔琳她們聊起天:「雷聲也太大了吧!剛那個閃電根本打在操場……」她們商量回家事宜,鐘聲來的很是時候──噹噹噹噹──噹噹噹噹──一片混亂間,不知道誰說了:「下雨了!齁我沒帶傘。」、「誒,明天約,等下一定下很大不能去了。」、「幹。我原本還想打球的。」、「先走了。」、「哈啊?」、「趁雨還沒下大趕快回去啦、白痴。」
太多聲音混成一團,出了教室,潔琳才發現不只她們班這樣,走廊上別班的學生也吵吵鬧鬧頻繁奔走。她像是裡頭的異類,只是緩緩靠上圍牆,這時,雨勢漸大,幾絲水滴像壞掉的花灑打上她的臉龐、自雙頰滑落,可她依舊不捨、將目光滯留於校門口,企圖看得清楚些……
若能看得更清楚就好了,但在雨線交錯下,視線可及處已灰濛一片。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