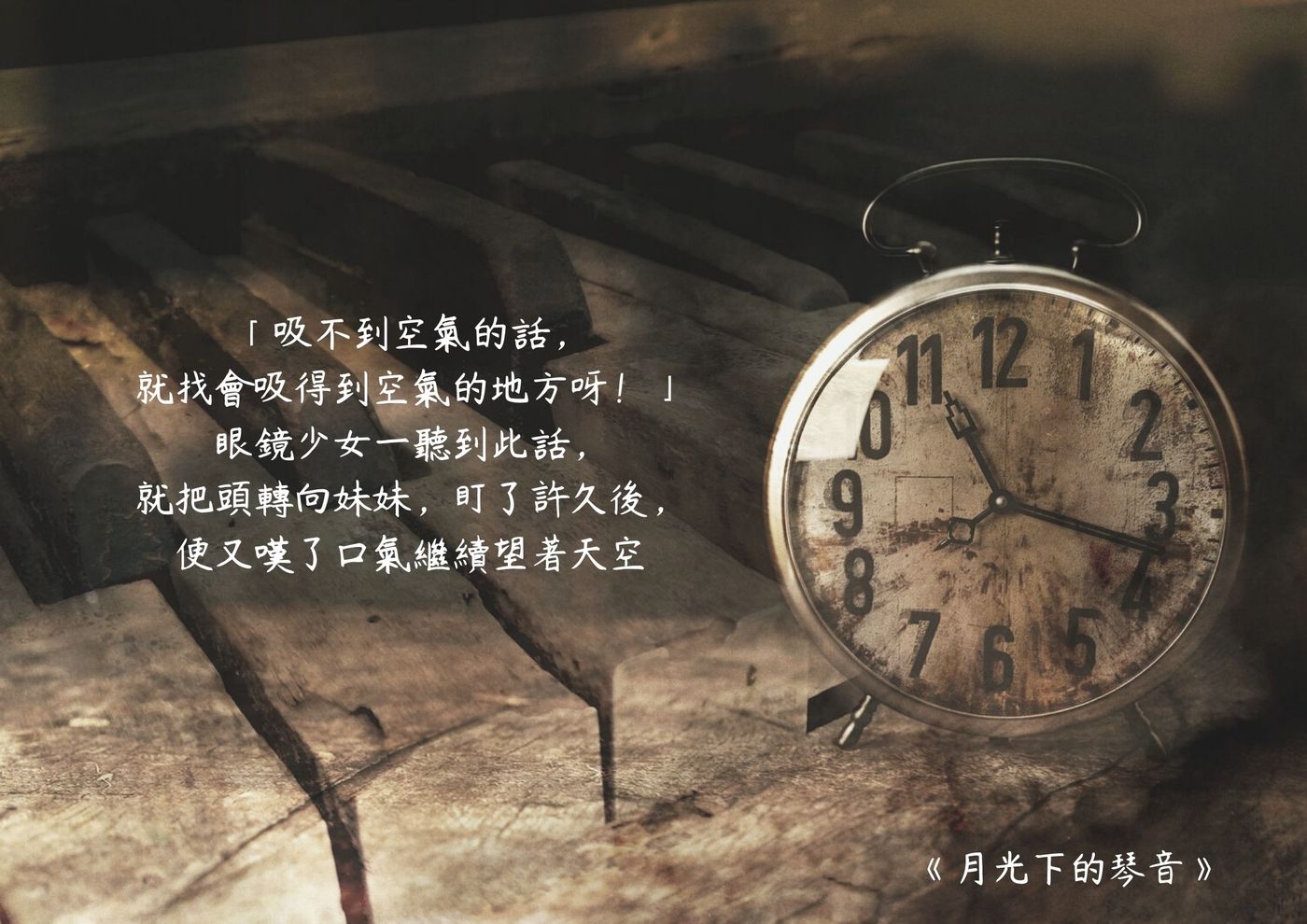3.2/ 蟬鳴
曾有過許多象徵青春的事物被埋進土裡,其中一味便是這年夏天陳俊霖的化身──校園內粉紅艷麗的杜鵑花被暴雨殘忍侵犯,它們狠狠墜下變得軟爛不堪,黏糊糊地與一地黑漆、褐色的土壤混成一塊,生長旺盛的杜鵑生殖器有些更死在了柏油上……
──陳俊霖屬於哪個部分呢?有幸成為養分的勝利組?或那以結果來說,無法延續生命、毫無意義的花屍……僅僅是注視著,她不知道,抑無法歸納,但又希冀他是落進土裡的幸運。
她感覺自己的呼求變得孱弱,甚至帶有死氣。對未來,頃刻就徬徨失措;她是知道的,夏蟬注定會滅亡,這是可控的結果,但牠們也會以多年的生長掙生命剎那的烈陽,鳴唱愛之歌;她是注定被這些紅花所哺育,未來,她也能變態──
可現在,她尚未知曉其中道理而專注於自己的憂傷,舔舐、自療,更將蟬視作短命鬼,即便成蟲可能活過兩個月,在她眼裡也同蝴蝶;這年紀的青春男女為向世界爭辯自己的與眾不同,總會信些偽科學,那也是青春特有的遺毒,廖潔琳無可倖免……
升帶考試終於結束了,她分神思考的同時已將黃帶與洗好的道服仔細收好,就在這時,她的腦海出現一個奇異的句子──夏天,是可劃去的一連串的待辦事項所組成的──
清單。
其後她發覺,事件是不斷出現與消亡的,無論是一個又一個傾心於誰的感情事,那也是能劃去的項目……意識逐漸迷茫,迷迷糊糊的,潔琳鑽進羽毛般柔軟的被窩,在冷氣與羽絨被的完美協調下,再擔憂的事件、未能達成的遺憾都不再重要……
一大清早,潔琳坐在學校的教室打呵欠,在老師來前解決了早餐。窗外震耳欲聾的蟬鳴提醒昨日的她是多麼天真,蟬鳴就是蟬鳴,才沒那麼多詩意夢幻的意涵,除了吵,還有更吵,僅此而已。
「齁!真的很吵耶。牠們的聲音都蓋過我了。」吵得連老師都受不了;刺耳蟬鳴正與催眠的授課內容相互作用,潔琳始終未得機會閉目養神,昨夜很早睡,但在室內冷氣的作用下,批著運動外套的潔琳又開始點頭了,她想起家裡的冷氣似乎也是這個溫度……
明明該像其他同學一樣開心放暑假的,但怠惰的廖潔琳失足加入了補考戰隊,他們這群沒考過的同學繳了額外的學費,還得穿校服回學校上半天的課,而那早些時候她認為來得太快的夏天,這年不只來得快,來得更是緩慢,像要將整顆臺灣都烤熟似。
──蕃薯啊,突然有點想吃……「廖潔琳,別再神遊了啊。這次考試再不過我也救不了妳。」女老師的聲音伴隨同班愛鬧的朋友那句:「被茱蒂罵了還換邊睡,妳卡比獸喔。」
潔琳聽了盡力挺胸坐好,抬起手、彈向朋友伸來鬧她的手,一邊還能朝老師傻笑點頭。當自己不再是大家的焦點,她才低下頭、瞪著講義上的題目體會什麼叫「ADD學生的學習狀態令人堪憂」。
身為ADD、注意力缺失症的多年受災戶,廖潔琳也很討厭在一個四五十人的班級裡、不坐前排就容易分心的學習狀態。甚至,就算坐前面還有機會分心!當全世界都在說她智商低的時候,她很想說,光是ADD就讓她連智商測驗都無法專心考了──智力測驗根本就不該在四五十人的班級內考啊。
潔琳又神遊了。
好險課下得很快,正午的鐘聲一響,夏蟬紛紛受了陽光感召倏地放大一倍,戶外熱呼呼的,操場被曬出金黃色的反光,她走得再快都沒能帶起一絲涼意,風早已變得溫熱,過分慈藹的太陽令她找不到被呵護的感受。
慶幸的是她不曾因北部的太陽而曬傷,有時她會羨慕容易曬傷的白皮膚們……和王宇軒吃了挫冰,草莓煉乳喚不回她的戀愛情感,明日就週末了:「到時約後操打球吧!」
就這樣,魚與熊掌終究不可兼得,這年暑假注定要失去許多東西,但也收穫了許多,以往未曾有過的、假日能一起運動的球友,潛進朋友家蹭飯的經歷,第一次去正式道館的過程,升帶考試……許許多多加在一起──
她竟還是不滿足!
3.5/ 蟬鳴
捱過夏日最炎熱的時期,廖潔琳和王宇軒等幾個一起參加補救教學的朋友也考完補考了,一同約在學務處的布告欄前看名單,待潔琳看見自己的名字列在數學與英文「通過」的欄位上才鬆口氣,轉身,笑著和她們報喜。
──通過補考考試,她們的暑假才算正式到來。
然而,暑假過去快一半,潔琳在家還沒享受幾天清閒的日子,接著又要去學校上暑輔!
──暑輔!萬惡的暑輔!
為了讓家長不用管暑假這段時間小孩的安危而發明出來的利器,成功傷害無數臺灣學子一年最長的假期;回家在電腦桌前擺晃著腿,坐在長板凳上回阿布訊息時,咬著冰棒的潔琳這樣想。
【阿布】明天放學要不要來我家,我阿嬤明天下午出門,不會在家,要來看看嗎?
好啊。
【阿布】那放學一樣約藍藍路,還是要約妳教室門口?
嗯……我想一下。
約妳教室好了,比較近。
【阿布】好。
潔琳有個怪癖,她喜歡稱「到過朋友家」為「攻佔朋友家」,更精準的說法是,親自走進朋友家,這個使一個陌生的地方變得熟悉、增加安全感的行為,其實只是蒐藏癖變相的表現。
至於約阿布教室,是因為一年級教室在一樓,她們班所在的樓也離校門口很近,再者……她不信,不信陳俊霖就這樣消失了──廖潔琳真的有病。
她的病從一個人的消失開始出現病徵,她開始緬懷這個消失的人,以複製對方的行為模式來緬懷。第一次發現的時候她已經十二歲了,或許是和國小一票熟人分開才染上這個病,但回神時已難戒除,她唯有重複刻畫對方的行為到滿足、厭膩才停手。
人一定有他們熟悉的行為模式,如何懷念一個人而寂寞,如何承受一個人的拒絕而不厭世,如何離開一個人而看起來常態──
成熟。
她想,自己什麼時候才能擺脫這念舊的模式?但這些天反覆約在阿布班級前會面,用梭巡的眼找那淪為已知的,不存在的人,她就知道了。自己簡直無可救藥。
在接近開學前三週,她突然發現阿布落單了:「怎麼今天只有妳?」阿布的臉色很不對勁,隱忍著什麼準備發飆的模樣,她在很多牡羊座身上見過,例如她的父親……「妳和小妤她們怎麼了嗎?」
「咳,別說了。我們鬧掰了。她們覺得我很討厭,突然不跟我說話了。」阿布和她在學校巷子旁的肯基基訴苦,潔琳盡心開導她,心裡卻恨透自己的推理直覺,幾乎先知的直覺早預測到今日的局面……
阿布有其領袖性格,但這種性格說難聽點是渾然天成的強勢。身為大團體的中心人物,阿布的控制欲自然使人畏懼,也讓愛好自由的朋友厭惡。當人際關係變成一方屈就於另一方作為,那就不是一個良性的互動關係了。
暑輔結束前的最後一週,阿布和小妤她們持續冷戰且未有和好跡象,阿布更因其為所欲為的作風,被學務主任列為頭痛人物,三不五時就因違規去處室報到,這也是潔琳始料未及的。早些時候,阿布還說過自己和小妤她們都跟主任關係很好。
暑輔結束前一天,阿布已經很習慣來她班上找她聊天了,潔琳依舊是之前那副模樣,只是她們的身邊再沒有小妤了;雙手懶洋洋地掛在圍牆上,接近吃飯時間,朝校門、操場的方向放空的潔琳被校門口的一群人給晃傻了。
白皙瘦高的男孩在校門口和阿布班上的學弟聊天,有說有笑的模樣令她心神不寧,恍惚間,她似乎見到了對方朝她直直投射過來的視線,那個視線炙熱地能灼傷人,更令她不敢細看。
一旁的阿布沒有察覺似地和她聊著不甚重要的瑣事。她卻無法控制,細細地用眼神描繪那人的形貌:濃黑的髮絲、長開的五官、抽高的身形……
她甚至連問阿布都做不到。
阿布之於他尚且有同班同學的身分,自己呢?廖潔琳之於陳俊霖有什麼身分?學姊算什麼身分?隔得那麼遠,校園裡隔了穿堂,隔了餐廳,隔了兩三棟樓!
要承認自己在意一個人,甚至是一個比自己年紀還小的人,她可做不到。潔琳輸給了自尊,將記憶封藏在一本塗鴉日記裡,而日記?多年後交予友人保管早已不知所蹤。
似乎她的記憶也能隨蟬鳴被敲響,隨夏天的結束再次丟失。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