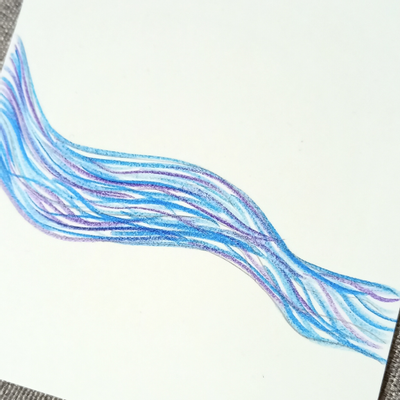我總在晨霧未散時踏入遊樂場。空蕩蕩的鋼架攀爬網像具剔去血肉的鯨骨,未通電的旋轉木馬靜如停擺的日晷。這座城市尚未醒來的時刻,才能聽見橡膠地墊縫隙裡藏著的往事——某年某月某個穿吊帶褲的小男孩遺落的玻璃彈珠,正與昨夜雨水折射出萬花筒的光。
滑梯頂端的鐵皮溫度總比現實慢半拍。當晌午的太陽將金屬烤成烙鐵,此處卻仍沁著朝露的涼意。我常疑心這道波浪形曲線是時光蛀蝕的齒痕,幼童攀爬時總要發出銀鈴笑聲,像往深井投擲的硬幣,須臾便墜入記憶深潭。有回見著個西裝革履的父親,趁幼子滑下時偷渡半秒童年,西褲後袋的鋼筆在離心力中畫出藍色拋物線。
鞦韆架前立著兩尊銅像。左側掛牌寫「限重30公斤」,右側卻無字。我見證過無數母親在此進行隱秘的儀式——她們先將孩子推送至雲端,待笑聲與彩霞齊飛時,忽地越過禁區跨上右側空座。剎那間鋼索發出琴弦崩斷的顫音,三十公斤的靈魂與九十斤的肉身在空中交錯,織就一張掙不脫的網。黃昏是魔術師抖開的綢布。蹺蹺板兩端升起戴老花鏡的祖父與穿背帶裙的孫女,夕陽在鍍鋅鐵桿上熔成金汁。他們用體重較量著光陰,一頭壓著《牡丹亭》遊園驚夢,一頭翹起《權力的遊戲》。沙池裡混著三代人的腳印:穿繡花鞋的裹足阿婆曾在此堆砌女兒牆,如今穿洞洞鞋的孩童正修建星際堡壘。
最愛觀察自動販賣機的黃昏時刻。投幣口吞吐的不只是鋁罐汽水,更是疲憊主婦的十分鐘逃逸計劃。我看過穿香奈兒套裝的女士在此兌換橘子味童年,罐身凝結的水珠沿著絲襪靜脈流成護城河。當霓虹初上,整座遊樂場便成了倒置的星座圖——蹺蹺板是搖晃的天秤,旋轉飛椅是失控的仙女座,而我們都是被重力釘在原地的觀星者。
某夜暴雨後,我見清潔工正在沖刷彩虹地墊。水流捲走棒棒糖紙與生日派對邀請函,露出底層用粉筆畫的跳房子格。這讓我想起敦煌藏經洞的覆壁畫——時光原是層層疊疊的羊皮紙,每代人都以為自己書寫的是首章。滑梯底積水倒映著月亮,忽然明白老子所言「大曰逝,逝曰遠」的真意。
最後的摩天輪車廂即將拆遷那日,我看見穿中學校服的少女在吊籃裡燒筆記本。灰燼如黑蝶撞擊玻璃窗,將二次函數與告白信熔成新星座。她們在最高點尖叫時,對街寫字樓正墜落某個中年男子的領帶夾。這座垂直城市裡,每個墜物都在尋找自己的地心引力。
離場時總要經過那台投幣望遠鏡。有人窺見木星斑紋,有人搜索童年住過的唐樓。我最後投下硬幣,鏡頭裡浮現的卻是萬花筒圖案——原來我們畢生追逐的璀璨,不過是幾片染色的碎玻璃,在光的魔法中暫時團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