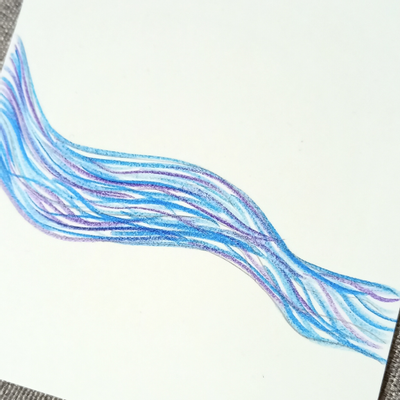霧鎮總是籠罩在白色的薄霧裡。
日升日落之間,霧從未消散,人們說,那是因為這裡的青年,一旦踏上離鄉之路,就會在霧裡失去自己的影子。
每年夏至,霧鎮的廣場會響起十三下鐘聲;那是畢業的日子,也是領取「初始面具」的儀式。 孩子們排成長隊,靜靜地等待。有人眼裡閃著渴望的光,有人卻低著頭,像在哀悼什麼。 面具陳列在石桌的台面上,每一副都閃著象牙白的光,沒有表情,沒有紋路,只有一片空白。
人們相信,那是新生的象徵,也是世界對一個成年者的認可。
當朔弌走到石台前,長者將一副面具遞到他手裡。 「記住,戴上它,你才會被世界承認。沒有面具的人,將無法被任何人看見。」 長者的聲音混著鐘聲,像是命令,也像叮嚀。
他凝視著手中的面具,心中生出疑問: 若是每個人都戴著面具,那麼——誰還能記得誰最初真實的臉? 他想起鎮上的傳說:有人曾拒絕戴上初始面具,結果不久後,他的名字被遺忘,聲音被霧吞沒,甚至連家人都不再看見他。 那個人最後孤零零地消失了。
一陣霧風掠過廣場,吹動了他的衣襟。 他終究還是將面具戴上。那一刻,世界震動了一下,視野模糊又清晰。 他抬頭望去,看見遠方霧後有一道光,像是某種召喚。
霧鎮的青年們一個接一個消失在霧裡,背著旅行箱,踏上未知的旅途。 而他,戴著屬於自己的第一副面具,也走出了鎮拱門。 霧鎮之外,霧氣仍濃得像絨布,街道兩旁的房屋像是半透明的幻影。
朔弌戴著初始面具,緩慢地走著,旅行箱在手,沉重卻又令人安心。 忽然,一陣低沉的鐘聲從轉角的巷子裡傳來。 他循聲而去,看見一位左眼淡金像晨光的老人玄岑,正蹲在街角,用木槌敲打著金屬片。 每敲一下,金屬片就像水面碎光,反射出街道另一端的倒影。
玄岑抬頭,瞥見了朔弌。 「你,帶著旅行箱來的孩子。」他的聲音沙啞,卻出奇地清晰,「我知道你尋找什麼。」 朔弌愣了愣,心裡閃過一絲不安,又似乎有種被看透的安心。 「你想換面具,或者——學會戴面具的規則。」
玄岑指了指遠方一座木質招牌,上面刻著「寒籟齋」三個字。「去那裡,你會找到你的第一份角色,也許能支撐你走得更遠。」 朔弌不解,但直覺告訴他:這是個起點。 他跟隨玄岑指引,穿過霧氣,踏入中醫館的木門。 裡面擺滿藥櫃,氣味混合著乾草、木屑和微微的香料。
玄岑揮手示意: 「這裡,每一副藥方、每一個治療過程,都像面具一樣。你要學會替人調和,也要學會掩藏自己。」 朔弌低頭看了看手中的旅行箱,熱氣在面具上打了旋。 他微微點頭,知道——自己的旅程才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