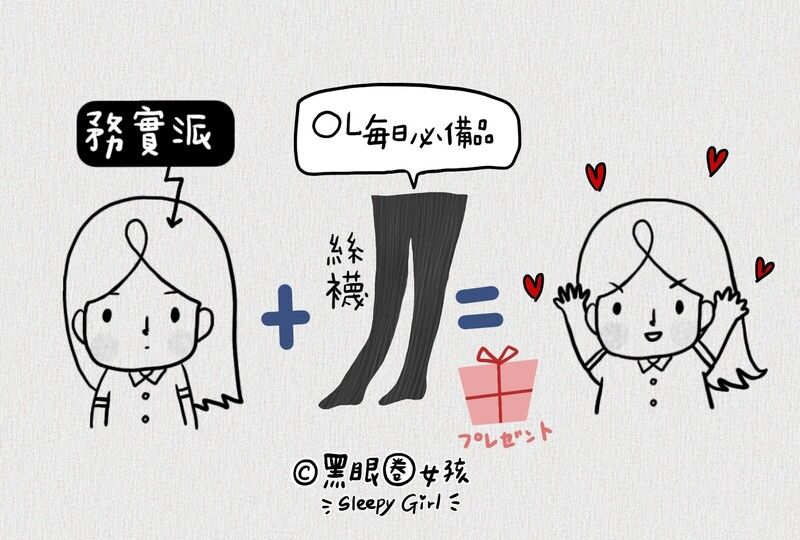雖然每一次口譯總讓我殺死大量腦細胞,但從沒想過翻譯翻到後來還要幫忙跟死神拔河的......
某天一大早,隔壁部門的日本顧問(以下稱川爺)走到我桌前,一臉苦惱地說著負責幫他口譯的F女上午臨時請假,問我是否可以協助隨行口譯。面對這種毫無預警的突襲式支援申請,當下我自然是千百個不願意,但他是跟我感情還不錯的川爺呀,所以還是應允了,隨即趕緊臨時抱佛腳,迅速查找即將拜訪的公司的相關資訊。
我、採購與川爺於十點左右開車出發,採購在車上表示,川爺早上起床後便覺得不太舒服,所以這趟行程結束後要帶他先去診所看醫生再回公司。川爺說可能是著涼了,沒什麼大礙,一路上仍跟我有說有笑。走進協力廠的廠房不久後,我明顯感受到川爺的步伐不如以往,且反常地默不作聲。我嘴上忙著口譯廠商說的話,眼角仍留意著他的臉色,約莫走了十來分鐘,川爺終於開了口,卻是表示人不舒服要待在原地休息,叫我與採購先隨廠商洽談。我內心有些不安,畢竟依我對川爺的了解,他是絕對絕對不會以身體不適為由影響工作分毫的人,我提議不如取消後續行程,先看醫生要緊,川爺卻揮著手笑說他只要休息一下便好,堅持該處理的事情先處理好。
我和採購互看了一眼,很有默契地加緊腳步辦完正事,隨後急匆匆帶著川爺到診所去。
醫生詢問了各種症狀,再確認了「有無抽菸?喝酒?」、「有無家族病史?」、「是否有心臟疾病?」等等,我便在一旁翻譯,除了有抽菸外,其他一概沒有。
「醫生說沒有發燒也沒有感冒症狀,看起來也不像是流感,以胸悶、肩膀背部痠痛這些症狀來看,不排除是心臟疾病。」我照實翻譯。
「我心臟好得很呢。」川爺一副受到侮辱似地駁斥。
「也是啦,你還比我健康呢。」我心裡也暗想著,心臟疾病應該無法從早撐到中午,早就倒地了吧,「醫生說他先開藥,如果晚點還是不舒服,最好到大醫院檢查比較保險。」
「這醫生也太小題大作了,就是昨天沒睡好,等等回去休息一下就好了。」
見他還能說說笑笑,我也就放下心來,回到辦公室後便忙自己的工作去了。
到了傍晚,我隱約聽到川爺跟大家說再見的聲音,抬起頭只看到他離去的背影,一問之下才知道他決定回家休息。這實在太不尋常了!雖說這根本不關我的事,但左思右想,我還是起身去找下午才來上班的F女,「希望是我自己嚇自己,但川爺肯定是非常難受才會提前下班,他自己一個人住,最好晚點以送晚餐為由繞去確認一下比較安心。」
下班回到家後,我收到F女的訊息,說她去探視了川爺,一切無事。但我總覺得心神不寧,又雞婆提醒了一句:「建議晚點再傳個訊息問問。」F女笑說我實在很搞操煩(台語,很愛瞎操心之意),當然我也不否認,但我之所以這麼憂慮,是因為川爺(以及我所知道的很大一部分的日本人)對於請病假這件事情一向嗤之以鼻,若非萬不得已,他是絕對不會提早離開公司的。
晚間七點剛過,便印證了我的不安。看到來電顯示採購二字時,我的心臟便開始加速,一接起電話,採購語氣急切而簡短地說川爺極度不適,必須送急診,F女無法陪同,另一位會日文的主管又住得比較遠(我家離醫院約十分鐘的路程),問我能不能到醫院去和他會合。
我二話不說奔出了家門。
川爺其實是七十幾歲的老人家了,但他老是喊著要再工作十年,而且永遠比我這年輕小姑娘更活力充沛,騎腳踏車還能從我旁邊超車然後取笑我太弱,所以常常讓大家忘了他年事已高。我實在太大意了!趕往醫院的途中,內心七上八下,連十分鐘的路途都覺得無比遙遠,恨不得有扇任意門。
當我衝進急診室看見川爺時,他病懨懨癱坐在輪椅上,整個人萎縮成一團,臉色慘白而痛苦,額頭上冒著冷汗。他手摀著胸口,勉強回答(其實絕大部分都是我代為回答)醫生簡單的問診。抽血等檢查程序結束後,我忐忑地站在川爺身旁,一瞬也不瞬的直盯著他看,心裡百般懊悔,想著「中午就不該打哈哈,應該堅持送到醫院檢查的」。
眼看著他臉色由青轉暗,似是喘不過氣來,我緊張兮兮跑到櫃台跟護士說病人狀況不太對,是否可以幫忙確認一下,護士冷冷回了我一句:「每個來急診的病人都很急,輪到時自然會叫妳。」
急診會依病人狀況分級,這點我再清楚不過了,臉皮極薄的我也不想當個不講理的人,更無意為難忙碌的醫護人員,於是我又走回川爺身邊,焦急地等待,一分一秒過去,只見他已經無法支撐自己的頭而往旁邊歪斜,意識似乎漸漸飄遠,跟他搭話已經連搖頭點頭都無法回應。我開始搜尋採購的身影,只見他站在遙遠的門外與其他主管通話,我像熱鍋上的螞蟻般在川爺身邊踱步,心裡的不安不斷擴大:「怎麼辦,如果他出了什麼事怎麼辦?」
我又走向櫃台:「拜託妳,可以幫我找醫生來看一下嗎?」
「等一下就會來看了。」
「妳看看他,我覺得......」
「請妳尊重醫護的判斷。」那名護士依舊冷漠地打斷我的話,臉拉得老長地加重音:「輕重緩急不是妳說了算。」
我回頭看了一眼川爺,如果是在漫畫裡,死神大概已經站在他旁邊了,當下眼淚真的快奪眶而出,內心的自責和害怕他下一秒就撒手人寰的恐懼將我吞噬,再也無法呆立在一旁看著生命流逝,理智在那一刻離我而去,再也不管什麼講理不講理,我在櫃檯前提高了音量:「算我求妳了,我真的覺得他快不行了!他是外國人,我不能讓他在這裡出事!他!快!掛!了!」
這時一名穿著白袍的醫生快步從我身後跑過,聽到我帶著哭腔的高分貝聲音而煞住腳步,轉頭看向我,一臉警覺地問了一句:「什麼狀況?」
我像抓到救命稻草般,跩著他往川爺的方向走,急忙解釋:「他是日本人,從早上就不舒服了,似乎是心臟的問題,我看他......」
醫生沒等我說完便彎下腰去檢查,幾秒鐘後,他臉色大變地衝往另一個方向,消失在我的視線內,只傳來他的大吼聲:「XXXX的檢查報告出來了沒有?給我!快!」
大約一分鐘後,那位醫生又衝了出來,後方跟著幾位醫護人員,推著病床火速往我方向衝來,我被這陣仗給嚇傻,茫然看著川爺被四個人俐落地抬上了病床,護士用力拉扯四周的簾子,在我還來不及反應時,川爺的身影便已消失在簾後。
醫生拿著一份似乎是檢查報告的資料夾,在我耳旁劈哩啪啦說著我其實無法理解也因語速過快而聽不清楚的一串話,大概捕捉到心肌梗塞、手術、繞道、支架、危急之類的關鍵字,最後他丟了一句:盡速聯繫家屬。
心肌梗塞?從早上到現在?我覺得自己全身上下每個細胞都在顫抖。
採購不知何時回到我身旁,我強忍著眼淚請他確認誰可以代替簽字,並要到了川爺家人的電話,抖著手撥打國際電話,川爺的妻子電話未接,好不容易聯繫上兒子,我試圖以平穩的聲音簡略地解釋,請他們盡快搭機來台。
掛完電話,身邊又無一人,看來採購又到外頭去打電話了。所以誰能簽手術同意書呢?還沒來得及多想,眼前的簾子突然被粗魯地拉了開來,躺在病床上的川爺身上已經換成單薄的手術服,身上多了一堆管子,接著四位醫護人員推動著病床開始飛快地移動,護士回頭對我喊了一句:「妳跟過來。」
我使盡全力跟在病床後方奔跑,這輩子連賽跑接力都不曾跑得這麼賣力,但是那飆車般的病床速度實在太快,把我遠遠拋在後頭,只能以視線緊緊追著那些狂奔而變小的身影。醫護人員如臨大敵的態度跟陣仗,加上那張病床的狂飆速度,都讓我內心的恐懼加劇,心裡反覆對自己說:來得及,不會有事的。
當我好不容易趕到手術房外,在上氣不接下氣的狀態下,又急忙應醫生的要求在川爺耳朵旁邊翻譯,告訴他現在要進手術房進行心臟手術,會麻醉、放置支架,以及聯繫好家人了等等。
話音方落,我便被一雙手往門後推,手術室的自動門啪搭一聲在我眼前關上。
我這時才有了好好喘氣的時間,狂跳的心臟猛烈撞擊胸膛到想吐,沒有心臟病都覺得自己要心臟病發了,我脫力地彎下了腰,雙手撐著膝蓋,大口大口喘氣,看著從額頭上滑下的汗水滴滴答答落在地板上,前胸後背全被汗水浸濕了,醫院的冷氣讓我冷得直哆嗦……
我維持這個姿勢在手術房門外大概站了近十分鐘,終於找回了冷靜,直起腰來才發現,自己置身於陌生的空間,環視四周沒半個人影,好像落入什麼迷幻空間似地,靜得嚇人。
抹了抹汗水,準備沿著原路走回急診室,驚覺當時只顧著追病床跑,根本不記得來時路,我便在那迷宮般的大樓中迷了路,後來循著地板上的顏色標示線走,賭錯了顏色走錯了道,幸好再胡亂找路的途中終於碰上了一名醫生,告訴我沿著藍色(?)線走,前後花了快二十分鐘才終於回到原本的急診室。幾位高階主管都來了,解釋完後,已經近十點,會日文的主管表示後續他會處理,謝謝我趕來。
回到家後我全身虛脫地躺在床上,等待,回想著一整天的細節,懊惱,眼睛緊盯著手機,發酸,等到近乎絕望時,才終於等來了「手術順利結束,川爺安好」的訊息。放下心中大石的剎那,緊繃情緒一鬆,眼淚就嘩啦啦不受控地滾下來,不知情的人看了都要以為是壞消息呢......。
真是謝天又謝地,幸好,命從死神手上搶回來了,否則我恐怕後半輩子都會被各種「如果」與「早知道」的悔恨念頭啃噬……。

隔天下午,我到醫院去探病,才一踏入病房就感受到好幾道視線,接著便聽到川爺虛弱卻愉悅的聲音說:「來了,我的救命恩人來了!」
原來,川爺還存有一絲意識時,有聽到我跟他講話的聲音,也知道我反覆去找護士求救,當然,後來氣急敗壞的叫喊聲他也沒錯過。(天知道這樣在公眾場合大小聲對一個臉皮薄的人來說多麼不易……)
「如果不是妳,再拖下去我這條老命恐怕真的就沒了。」
川爺的太太也握著我的手表達感激,寡言的兒子則站在一旁對我四十五度角鞠躬。
那一刻我突然覺得有點好笑,都說人生如戲戲如人生,這種場景跟對話都好像在演什麼八點檔,我希望自己的職涯生活能很精彩,但絕對不是這種充滿戲劇化的精彩,再大顆的心臟都承受不起,更何況我這麼膽小。
在那之後好長一段時間,跟著川爺時我總是戰戰兢兢,深怕這個愛逞強的老傢伙(喂)突然心臟病發,而川爺則老是把「妳是我的救命恩人」這句話掛在嘴上,甚至有次在某個社交場合遇到他的同鄉(看起來不比川爺年輕),聊天中得知他們倆相約好似地在差不多時期到鬼門關前走了一遭,他還對同鄉說:「來,跟你介紹一下,這是我的救命恩人。」還真是永遠不忘提醒我那個曾經幫他跟死神拔過河的夜晚,都不曉得我那時嚇得可不輕!
這大概是我口譯生涯中最難忘(驚魂)的一役,也是回想起來最「歷歷在目」的一件往事。
在我離職半年多後,接到了醫院來電追蹤川爺的狀況,要我提醒他定期回院檢查。那是我最後一次和川爺聯繫,去年聽說他回日本了,盼他一切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