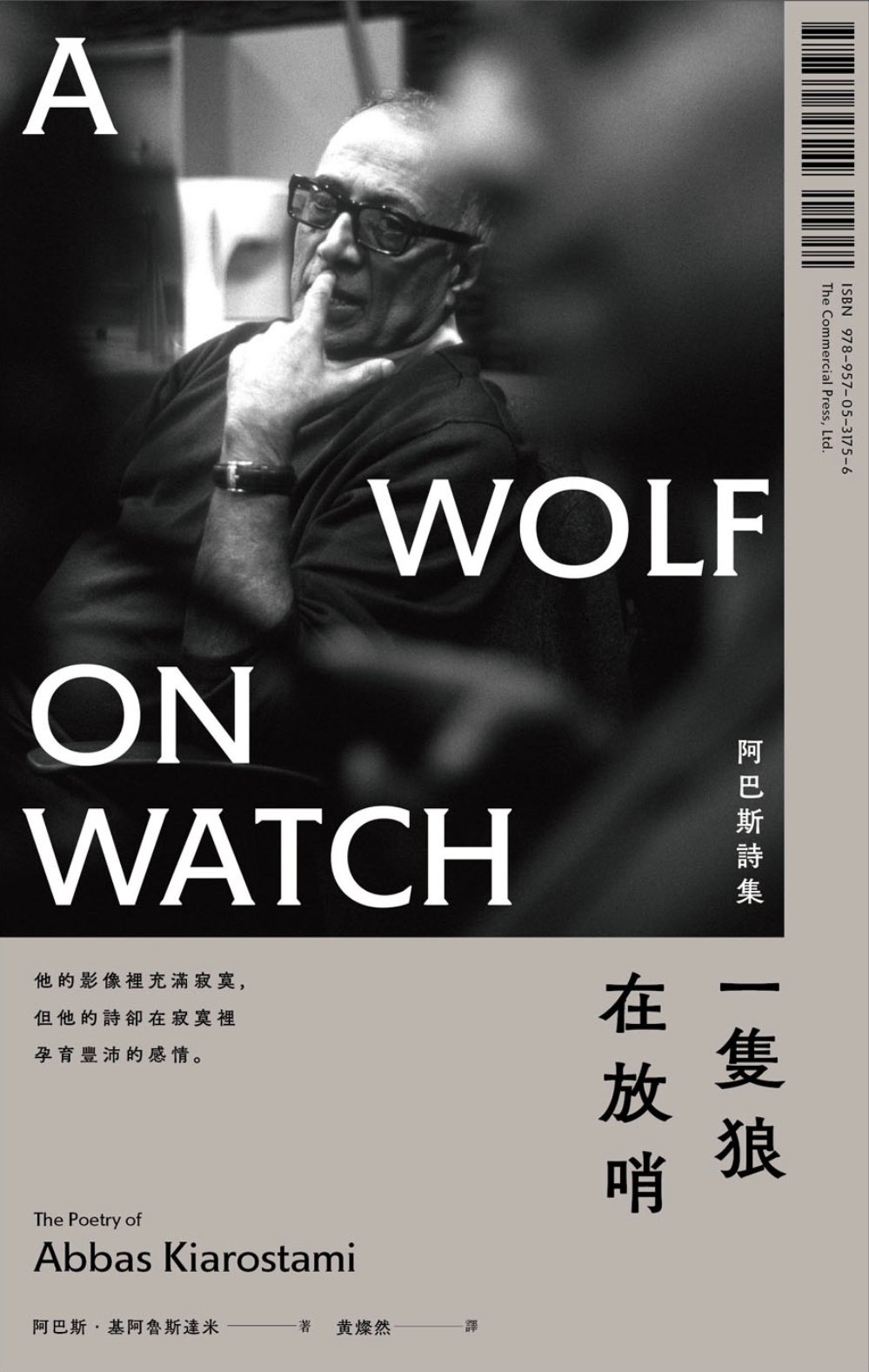Two Men and a Wardrobe (1958)
每一次欣逢夏日,都讓我感覺曾經的夏日更美。這個美,非關行經風景的亮麗與朧暗,而是一種自由來去的暢意。何以愈活愈困縮,是我該反省的事,而藉寫字紓困,不失為權宜之計。過去我瞧不起濫情囈語,自我感覺過剩者之間的惺惺相惜,我一點興趣也沒有,但這麼說可是輕看了人性。生活必有壞得冗贅、醜得不堪之時,落筆另織一方水土避禍安神、訴苦自娛,有何不可?
五月 ── 適合觀海、午睡、採花給大病初癒的人。熱浪的前奏溫馴撫過日常的邊陲,蝕落一地鵝卵狀的夢境。立夏之際,諸事纏身的我挑選了兩部天馬行空的短片〈Two Men and a Wardrobe〉與〈At Land〉,重溫喜趣順便介紹,盼望能產生跳脫現實的特效:沼澤變作沙漠,水底如雲頂。我信,人若想身心健全,閒情逸致、神遊機遇不可或缺,急如熱鍋蟻,更要一片冰心在玉壺啊。
Two Men and a Wardrobe (1958)
〈Two Men and a Wardrobe〉是羅曼.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1958 年在波蘭洛茲電影學院拍攝的學生作品,可以說是我愛上電影的契機之一,那種在散場回家路上會不禁起疑的:這理應是我拍的吧,怎麼有人先下手為強呢?── 荒謬的提問足見共鳴之強烈。四年前有幸一觀高雄電影節的優質策展「時代之心:波蘭洛茲電影學院短片專題」,除了這部〈Two Men and a Wardrobe〉,也一口氣看好看滿華依達(Andrzej Wajda)、奇士勞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等人在成為電影大師之前的習作簿,結下了我與波蘭藝術電影的不解之緣,至今仍銘謝這場意外的相逢。
這支短片的故事,是關於兩個瘦小的男人扛著一座巨大衣櫃,從海中離奇冒出、走向岸邊,隨後進入小鎮嘗試販售衣櫃給路人的過程。沿途他們想設法搭電車、上餐館,卻屢屢不受歡迎遭到驅趕,也碰上了暴力事件 ── 無端捲入街頭混混的玩鬧,被廢棄物處理場的管理員毆打。最有意思的是,鏡頭並不緊緊跟隨著兩名主角,反而經常猛地橫搖至旁邊某處的景象,講述著「與此同時」的平行時空,例如一個扒手正悄悄竊走某人的錢包,或者一個醉漢努力爬上階梯卻迷迷糊糊倒退回來。其中也有生靈喪命:先是被石頭砸死的貓咪,再來是河邊一個慘遭謀殺的陌生人。主角並沒有注意到這些事故,使得觀眾彷彿成為了目擊兇案的唯一旁觀者,卻束手無策。

Two Men and a Wardrobe (1958)
〈Two Men and a Wardrobe〉以鬧劇的外皮,捲伏悲觀的嘆息。純真如頑童的男人脫胎自汪洋,無以抵抗陸地群居種族的險惡和敵意,摸不清楚社會權力運作的原則,虧過痛過,只能回到原點,再次流離入海。如今的波蘭斯基儘管因權勢性侵而聲名狼藉,但我認為他描繪「世道殘酷,因其深植人心」的手法之準確,是他佳作輩出、且對每個世代的觀眾來說都具有欣賞意義的原因之一。在〈Two Men and a Wardrobe〉這部早期作品中,波蘭斯基擬仿默片時代的 slapstick comedy 風格,細密運針縫合多起暴力事故的切片,鋪敘出兩個扛著衣櫃的男人的遊走路徑,將超現實的無風破浪起手式,導入社會寫實的面向,呈現出個體的脆弱,以及集體的模糊與沉默。而最終,男人依舊扛著衣櫃回到海中,世界運轉一如既往 ── 有你、沒有你,都改變不了什麼。

Two Men and a Wardrobe (1958)
好作品可以絕望但不可無情,黝暗的命題之上,〈Two Men and a Wardrobe〉有它的瞬閃時分:男人初登沙灘,興奮地手舞足蹈翻筋斗,照鏡整理儀容上路冒險;男人回到海岸線,小心翼翼繞過小孩在沙地上堆起的密集沙堡,不願踩壞任何一座;還有,他們在觀海廣場上分食一條置放在鏡面上的魚,它與天上浮雲一同映在鏡中,彷彿成雙飛行,隱喻著男人攜手共闖的怪奇旅程。如此影像,詩意而柔軟,緩和了黑色幽默的銳利,也豐富了打鬧詼諧劇的層次。

Two Men and a Wardrobe (1958)
一座漆黑的衣櫃,被搬運過明亮的沙灘;兩個男人,睡在方形的陰影之中。我對他們笨拙行走的模樣尤為喜愛,啟發了我寫下一則短篇小說,以及之後的許多創作。他們的步伐和身影消失在海浪之間,追索下去,會是什麼呢?電影 ── 這種時候我非常確信,電影應該保持停留在岸上的遠目姿態。

Two Men and a Wardrobe (1958)
瑪雅.黛倫(Maya Deren)的〈At Land〉,對老讀者來說應不陌生。我在前幾期的《潺時》討論過關於這位實驗電影導演的紀錄片《瑪雅黛倫之鏡》,當中就有提到這部拍攝於 1944 年的短片。礙於文章結構,讓瑪雅的代表作〈Meshes of the Afternoon〉佔去較多篇幅,不免有憾,於是在此補充一些我對〈At Land〉的看法。

At Land (1944)
故事照樣從海灘開始。和〈Two Men and a Wardrobe〉不同之處,這次是一個女人被沖上了岸邊。她赤手空拳,宛如擱淺那般倒臥著,睜開眼睛的時候,她看見海浪倒退地捲回,令她感到異樣。但轉望天空,飛鳥又是順時地向前飛過。
短短的一段開場,瑪雅.黛倫已讓我羨慕和她活在同個時代的人。〈At Land〉之喻,在女人逐步登陸的過程中浮顯出來:這座陸塊,是夢境的淺眠處、潛意識汪洋的偶然島嶼 ── 是我們清醒後依然能記取的影像。她攀向漂流木,卻在匍匐前進之中移物換景,抵達一張衣冠筆挺會議長桌。而後,情境持續變遷,她追隨一顆掉落的西洋棋,爬下礁岩組成的懸崖,然後跟著一個男人邊說話邊來到一間小屋。她鑽入房間,看見一具罩著白色床單、只露出臉的活死人,對望良久,她輾轉走到戶外,回到海岸,兩個女人在浪花之畔下著西洋棋。她偷走了其中一顆,然後開始沿著沙丘奔逃。回眸時,她發現許多個自己,正站在各自敘事線的盡頭,不明所以地瞪視著疾馳的她。

At Land (1944)
串聯碎片,布局奇想;失重的空間,錯序的時間⋯⋯瑪雅.黛倫玩弄電影的剪接術與虛設造景,重現夢的景象和作夢的知覺,予我一種既恍惚又入神的奇妙感受。剖析每一層物件的象徵、指出主角隱約的執念,自然是有趣的,但我更好奇的是:為何是「在陸上」?她從海上來,由昏迷至甦醒,暗示著結界的存在;陸上的艷陽直射,相較起水底的扭曲光線,竟才是變幻莫測的蜃景野域。若從夢境心理的角度來看,我認為登陸代表著一種主體的顯形,由此延展行動,揭曉創傷和慾望。而若從生物演化觀點來看,生命起源自海洋,適應陸塊的過程之漫長是人類難以衡量;水與陸的交界處,遂成為物種演化史的主戲棚。

At Land (1944)
或許,瑪雅化身浪潮的沖積物,意欲表現的是一種曖昧隱密的過渡狀態,不僅是空間的轉變,也包含時間定律的改易。十五分鐘的〈At Land〉,是日復一日的脫胎換骨,是永無止境的水土相蝕,亦是一場短瞬的陷眠(hām-bîn)。潮濕的意識,在遊蕩的途中逐漸曬乾,而新的受器突出體格,使女人覺察到內在的真實 ── 某種懸墜情感、因回憶而產生的陣痛、重述故事的無盡紛歧⋯⋯在她眼前顯影,變得具體可見。「陸上」的最後一層涵義,猶如死亡前夕極端清晰的生之圖景:一種推搡擠壓而現身的「可見地帶」,一場漂流者渴盼的靠岸,猶如橫切過雙目的狹縫之光,在片刻的刺眼後歸闇。

At Land (1944)
〈At Land〉奔向大海的結局,是夢醒抑或還魂?電影仍是留在了海灘的這一頭,不再跟隨,也不再剪裁。我們可以看見女人遺下的足跡,也知道等會兒海浪就會將其抹去。塵歸土,雲化水,存在或許是一場枉然,但至少,電影為我們溯及既往:女人在陸上最後一次走遍所有風景,並確信自己曾經來訪。
數月不見海,便患缺水症。縱然挑選這兩部短片作為書寫對象有啃老本之嫌,但近期著實鬧片荒,非我所願。無能也無緣嘗鮮好電影,我心情極爛,所幸寫著寫著,還是有股重拾信仰的定氣。
也想起其他肇端於海岸線的故事。卓別林(Charlie Chaplin)的早期短劇經典〈The Adventurer〉(1917),一個越獄犯把自己埋在沙灘裡,穿梭於礁岩洞穴躲避警察,最後在槍聲的追逐下逃向大海,游到氣力盡失。亞倫.雷奈的浪漫科幻電影《我愛你,我愛你》(Je t'aime, je t'aime,1968),男人進入時光機重返過去,一口換氣,探出頭來,便是那水藍色的浮潛夏日 ── 愛人躺臥在岸邊,望他涉過數十個寒暑,擁夢洄游。我想著,如果現在出發到海邊,能捕獵他們遠行的殘影嗎?這些打從海上來的人。
五月五,夏之始。此時耳語緩言,猶如晴空之上的弦月,枯淡、蒼白、荒疏,卻是閉目養神的眼窩之形。再次睜開以後,我該將目光投向何方?群鳥與貝殼,藤蔓與狗。浪無止息,恆常餽贈遺物予荒渺之岸:積沙成石,攏石為陸,便是我們呼吸漫遊的島。

At Land (1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