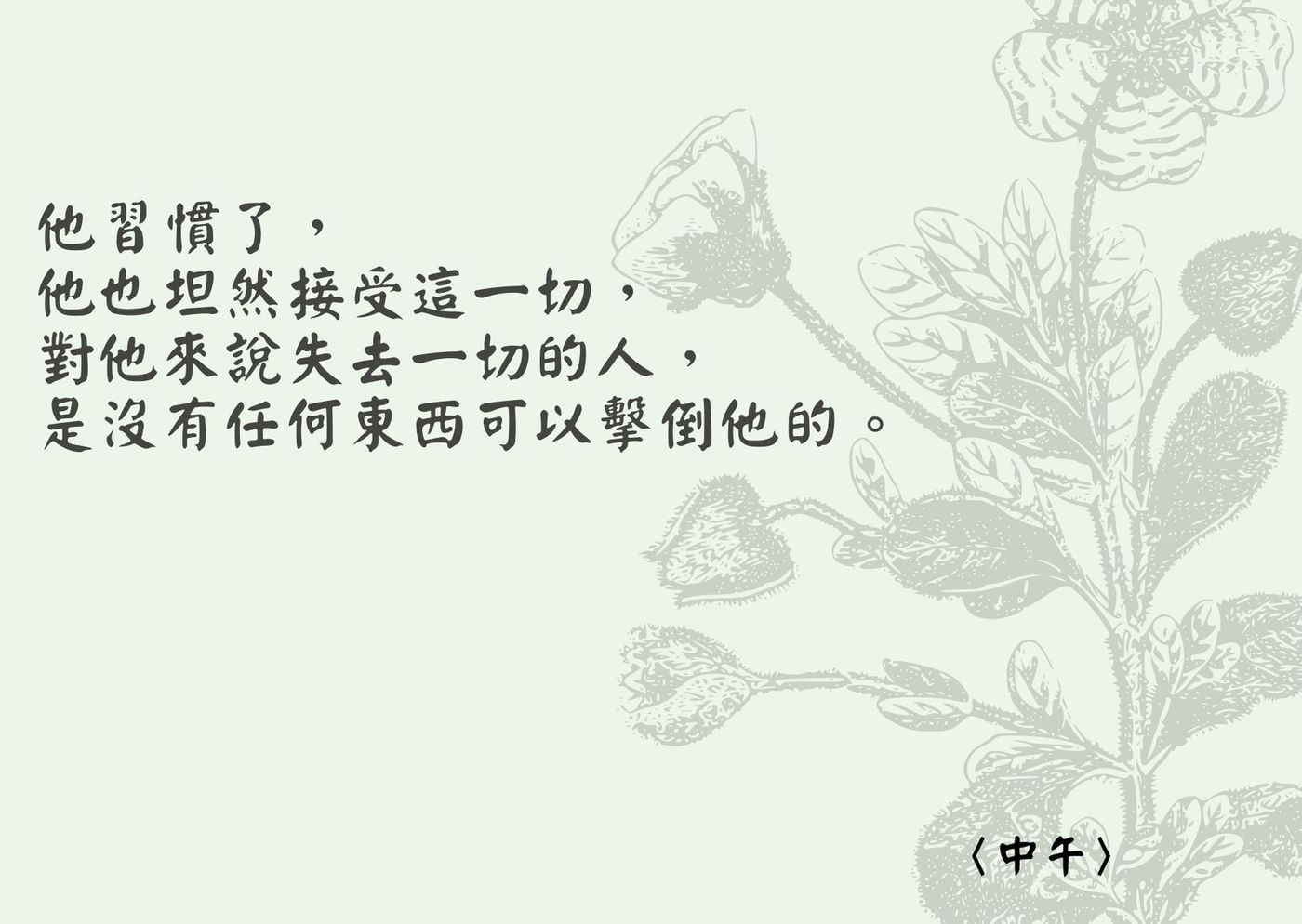這一日,他照例在穿堂那座壁鐘差五分指向八點的時刻走進鄉公所,卻沒向負責打掃的清潔工阿水嬸打聲招呼。
「阿水嬸,早啊。」或者:「辛苦妳了,阿水嬸。」謙和有禮的問候總讓一位卑微老婦眼中的公所真正亮了起來,有了光,有了溫度,好像一天從這一刻起才真正開始。但是今天,阿水嬸拄著掃帚狐疑地目送他登上階梯的背影,察覺出些微的異樣。
「鄉長伊有心事?」二樓鄉長辦公室的門沒多久便被打開,那一隻右腳卻遲遲不跨進去。他站在自己的辦公室門口,摸著後腦勺,懷疑剛剛有條人影在他眼前晃過,就在幾分鐘前,一個矮小的身子和一張臉,面對著他──啊,是阿水嬸──他猛然回神但為時已晚,於是搖搖頭,有點洩氣地終於把右腳踩進自己的地盤。
當然,他當然還有一隻左腳。事實上,四肢健全的他甚至得過油菜花季綑豬大賽的亞軍,原本要送給鄉民的獎牌目前就擱在他的檔案櫃上積滿灰塵,可供來賓驗證本鄉鄉長的健康狀況。然而此刻,獎牌的主人惶惶不安陷身一張皮椅,動彈不得有如當年在他手中掙扎的豬仔。
上班時間才過二十分鐘,人也才坐下不到半個小時,他已經接了三通電話。這三通電話來自不同地方不同的誰,可是他的應答以及對待話機的方式卻大同小異,都是不耐的「我還要再研究研究」然後砰地一聲掛斷。早晨的空氣裡不時傳來他粗重的鼻息與扭動身體製造的椅子嘎吱噪響。
他勉強振作起來,開始批閱公文。
桌案上兩個塑膠盆子分別貼著「一般」與「急件」兩種標籤,前者現盛有四五件黃色公文封,後者則顯得空蕩蕩,淺綠色盆底只躺著一份紅皮公文。他從不看那多餘的標籤。「紅皮先,紅皮批完批黃皮」,這宛如童唸的辦公口訣蓋由他自創,平日由他默守,這會兒卻也由他自行打破。他三兩下看完黃皮公文便擲筆起身,扔下那份孤零零的紅色急件逕自走向一扇窗把窗打開,接著從口袋掏出一包長壽與一只打火機,三兩下點著一根菸就倚窗吞雲吐霧起來。
「最近你菸怎麼抽得這麼凶?少抽點呀。」
太太在他出門前還再三叮囑,但他眼睛盯著辦公室牆上「禁止吸菸」的標語,仍不得不抽它一管。實在是,他實在是心情又煩又亂。
煩什麼?亂什麼?他煩一個理由理不出來,亂一個結果結不下去,主要的癥結,乃在那份被他壓了一個多禮拜、至今仍死賴在他桌上的「紅皮」──一件難批而未批的棘手案子。那案子半年前便開始白天進駐他的耳殼夜晚進駐他的睡夢,以至於現在的他能夠輕易穿透那紅色公文封直視裡頭的簽呈抬頭:「福魚潭觀光客倍增計畫」,他並清楚,所謂的計畫其實是怎麼一回事。
「幫福魚潭整容」──記得在半年前的那場聚會上那一位建商是這麼說的,在場幾位鄉民也一致認同。他們一致認同,「我們的福魚潭」是該好好整治整治了。
「我們的福魚潭夠美,但是不夠吸引人,我們應該讓她豐富一點。」一位攤商說:「建議擴大攤販區域。」
「我們的福魚潭硬體機能不足。」一位工程包商說:「應該增建遊樂場、大型賣場。」
「對,大型賣場。」一位賣場經理附和說道,然後把頭轉向一位鄉代。
白臉唱完,該黑臉唱了。他依稀記得那位鄉代是以一種柔中帶剛的腔調說了一些什麼,話的內容不是重點,重點是那說話的腔調,擺明要他識時務,否則「不知道下屆鄉長選舉會跑多少票」,假如他還敢企圖連任的話。
有人必須銀貨兩訖,他知曉。剛剛三通電話的其一,便是那位鄉代打來的,他聽得出,對方被催貨催得很急,什麼時候貨能拿到,就看他,看他鄉長的貴手了。結果,他們只要結果,並且是讓他們滿意,上頭大大批了個「可」字的結果。
「可是,他們要的理由怎麼辦?」他捻熄香煙,想起另一組他們。
他們是誰?他們是一群勇敢又天真的學生。他們,不知如何得知大人們的陰謀,竟然在關鍵時刻直闖進鄉公所,找上了他。
「請不要傷害大家的福魚潭。」帶頭的男學生這麼說,眼中燃著讓他熟悉的熱火。「必須給個理由,為什麼?為什麼你們想這麼做?」
「為什麼?」他問自己,好像昔日父親問他,為什麼要出來選鄉長一樣。當時他以男學生的眼神給了老父親篤定的理由,現在,老父親早已辭世,他卻還在這裡,得不到自己的回答。
於是,理由在頭,結果在手,他被兩方拉扯,就快身首異處了。此時又一通電話進來,他走回座位,不情不願拿起話筒。
「我黃課長,想請問,關於福魚潭的那份文……」
啊!──他低吼一聲摔上電話,走出辦公室,走出鄉公所,走出所有驚奇困惑的注視。他走了。
然後他不知不覺來到一所小學。漫無目的地走,竟然走進包辦了他整個童年的小學校園,連他自己也很訝異。但其實他是不肯承認,舊地重遊,無非是遭遇此生極艱難的關卡,心靈想尋一個寄託,一個讓他安適又不致丟失顏面的寄託。
所以他的雙腳往某一個方向走。那一個方向,將領他到一處僻靜的校園角落,而那角落裡,將有一棵老松。
他七歲時,父親與他一起種下的小松,如今應該已是一棵挺拔的老松,他加快腳步,向記憶中的它走去,穿越整個校園,尋了又尋──竟然沒找著。
老松不見了。父親與他的那棵老松不見了,幾年前父親往生他還懷著哀傷來看過它,現在它竟然消失了。
「松樹呢?原先種在這裡的松樹呢?」他抓住一個倒霉的學生,氣沖沖地問。
「松樹?這裡是遊戲區,你沒看到那邊的鞦韆,還有溜滑梯……」
他瞬間懂了。原來學校為了遊戲區,寧願一棵老松,他們寧願要一座溜滑梯,而把他的老松,他父親的老松,砍了。
他覺得眼眶濕熱,有一股悲哀從心底升起,望著天空,他慢慢領悟了些什麼。
現在,他回到鄉公所,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紅皮批完批黃皮」,他把那份「紅皮」打開。
「阿爸,你總說我自私。」他眼裡的火回來了:「你說對了。」
終於,不必給理由,也有了結果。福魚潭繼續保有她的美,一些人歡欣,另一些人憤怒,一位鄉長心甘情願放棄政治理想,因為一棵老松的緣故。
〈本文原載於中時浮世繪版,2004/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