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楔子
類型電影的廣泛性,將其多發的創作概念,以一種截然不同的操弄手法,與作品本身的意圖凝練在一塊。如電影不同於文學或劇場的表達形式而作為當代文化的共通語言—它的特殊之處,正是能夠在不同面向的整合概念中,將故事的實質意涵重新建立起影像空間的敘事觀點;尤其是在特定類型電影為主體的表徵中,更能夠觀察到此一現象的幽微之處。
好比我們在【懷特獨白私心自作計畫】這項計畫的執行上,便就是以類型電影的相似性,以將筆者觀察到的文化意涵與及其涵蓋在作品中的個人立場,再行透過超譯觀點的重新詮釋,另行開闢此一專欄分類法的實驗項目。顯而易見的是,對於在同一類型作品的表現上,其就以敘事主體的目的性以及方向進行比較,作為觀者便能夠更清楚的了解它們在論述架構的基本差異。不過,關於本文所及的分析方法,其不僅只為了凸現出作品之間的優劣之處,則是透過解構、重新歸納與整合的梳理過程,使我們能跳脫出影像表徵的誤區、從而將它們的本質凸顯出來——也就是說,在釐清劇情的同時,誘發我們與作品的感官連結,並且使故事背後的獨立精神存在能夠成為客觀的實際物,並向現實議題探討的範疇繼續發酵。
而在有了前述的引介之後,相較於類型電影的基本定義與其邏輯,想必觀眾便能有更明朗的概念進行比較了;僅此,那就讓我們再次回到懷特獨白的論述範疇,並從影像符碼的角度循線挖掘作品在鏡頭語言中遺落的訊息和信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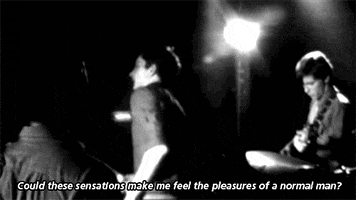
鏡頭・凝視→以死亡象徵的神聖性,還原文化符碼二層說的實際存在
基於作家對於生存意志提出的質疑與反抗,文學中的死亡象徵便成為了他們印證其物存在的現實途徑。
比方是杜斯妥也夫斯基在《罪與罰》這部作品中,用以主人翁的遭遇,向我們展示人性的所在:其故事主角拉斯柯爾尼科夫本是名再平凡不過的普通人,但是,因為受到高利貸放款的老婦人壓榨,卻讓他成為了罪人;然而,面對拉斯柯爾尼科夫內心的囚牢,法律之於社會的險惡,又何嘗能算得上他所背負的苦難?
且不僅止於此,在那急切渴望的真理、痛苦和內心盼求的解放中,卻更能看到杜斯妥也夫斯基字字話語對於現實的拷問與無奈——猶如拉斯柯爾尼科夫倍受侵蝕的心智,無論他最後是否選擇投案、又或是在殺害了放款老婦人之後,為窮人們帶來了解放的契機,拉斯柯爾尼科夫崇高的理想終究無法實現,同時,他也只好接受現實的原罪、在自我放逐的過程中,面對人性險惡帶來的懲罰。
此外,透過《罪與罰》的詮釋,那周旋於杜斯妥也夫斯基思緒裡的道德問題,便也同樣在此被映照了出來;只不過說《罪與罰》是其中一個例子,則若再以《地下室手札》的角度去做比較,這對於人性的剖析,卻都使我們這些讀者能夠更近一步地感受作者對於內心持續抗衡的現實責難,甚至,當讀者都已讀遍了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後,必定也就能理解他所經歷的人生、那些沈痛的代價還有用文學訴諸一次次的行動證明了。

從《誤會》談荒謬的本質性
不過,相較於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或許大眾對卡繆、卡夫卡的劇本架構都較主流市場青睞些,尤其是筆者在過去推薦此類經典讀物時,身邊大部分的反應還是比較認識卡繆多一點的。那接下來,就繼續從卡繆談存在吧,不對,正確來講,應該是從卡繆的文學觀點談荒謬,這才算得上他作為一名文學家的思想價值所在。
而說到卡繆,也許有部分聽眾的第一反應,會想到他的代表作品《異鄉人》,不過呢,相比異鄉人而較讀者比較少接觸的劇本作品《誤會》,這才是我們今天這一集內容所要談的範疇。
《誤會》,從作品的文意來看,就如他本身的含義並無異同,其誤會的明義直白來說,也就是誤會本身,貫穿著這一整部劇本的核心架構。
而後,若再更近一步來認識這本讀物,以從劇中角色與其時空間場景的關係作導讀:旅館、兒子、他的妹妹和母親,單憑藉這三者關係的衝突,幾乎就已將他們的關係交代完畢了,且再向下梳理劇情大致發展脈絡:故事的主人翁——也就是兒子這名角色,在經歷離家出走十多年之後的某日,回到了故鄉,期盼能在此找到他未曾擁有過的幸福所在,也就是人應擁有故鄉的常理性;但是,正當他回到了這早已遺忘『他』的陌生地、回到了他多年前和母親一同生活的旅社,並且還抱持著自己仍能夠在這處找到他所失去的『幸福』時,他的母親卻已然將他拋卻得好遠。且況,就更別指望妹妹對他的印象了。
不過,整部劇最為荒謬的命題:也正是主角對於『人與人之間不可能擁有的幸福』這件事所做出的一切原則;其故事的主角:兒子,在經歷『離家出走』的放逐過程到他『返回故鄉』這段思潮之間,面對兩種不同生命經驗的『衝突』以及其必然經歷『人格重建』的轉變過程,兒子作為一名理想的實際行動者,卻在現實與荒謬的迴盪下,讓自己和其中的癥結、攪和,更甚至決定了死亡的安排;而也正是因為他對於人的『信任』,以造就了荒謬悲劇的產生。
但同時,若他在回到故鄉之時,就以人們所能夠理解的方式『招認』,或許就如同他的妻子瑪麗亞所告誡的,能夠阻止悲劇繼續發生;不過,也同樣是因為他沒有選擇公開的緣故,造就了這場荒謬劇最為荒誕的部分。其在劇中,透過誤會的三幕劇,我們得以透過兒子與妹妹的對話,大致感受到他所想要給予妹妹所謂的『親切感』,只是妹妹相較於哥哥,也就是面前這名陌生人的態度,卻使她更為感到排斥,僅此,透過兩者的互動,便也道出了此劇幕基於『信任與人之間不可能幸福的可能』的主旨——其就算是兒子選擇揭露自己的身份,如此的幸福也並非會是他所想要的模樣,其就算他人得知自己的身份,其對於母親和妹妹而言,這已然拋棄而又再次歸來的念想,又何曾不是母親的奢求,再者,當兒子能夠讓母親自主地想起兒子的面容,哪怕這微乎其微的可能並不能抱有太多期待,但當兒子回到這處被他拋棄許久的旅店時,他所巴望的幸福,卻也早已在內心實現,只不過所謂的幸福,就瑪麗亞這名局外人,所不能理解的,正是兒子和母親在經歷自我放逐多年之後,這囚困內心的苦難,是如何約束著彼此,同時,又包含著解放的契機,將她那懇切難耐的心智,隨著兒子的放逐而抽離,予以成為母子兩人難以斷除的聯繫;即便母親在兒子出走多年以來嘗試告解,但種種的掙扎,卻只有在無盡的孤獨中盼望著幸福的到來,這持續消極的懸念才能夠有獨自抗衡的意志,使得他們能在生活中依然搏鬥著。
僅管故鄉並不在此處、母親也不代表幸福、但是,當母子二人終於能夠在死亡相會時,這場誤會造就的不幸,卻已然使他們實現了幸福,其幸福的真正意義,正是在兒子回到故鄉之時,將內心的罣礙一一屏除了、乃至於母親長年渴望的平靜,也同樣在死亡的過程,帶來了永遠的解脫。而這便也就是《誤會》所印證的事實,妹妹所嚮往的實現,在所謂的生命體驗中,都是短暫的,惟是在死亡象徵的幸福過程中——即在我們解脫之後,回到了真正的故鄉,使我們都能夠實現永遠的幸福。
再者,正當故事的另一名外來者登場,而從主角的妻子瑪麗亞觀點做觀察,卻又再一次凸顯了劇本裏裏外外的荒謬本質——尤其,是當瑪麗亞在和主角的對話過程中,所讓觀眾明白的立場:正當她向丈夫坦言自己進到這處被人遺忘的所在就已失去對人的信任時,瑪麗亞那作為外來者的職責,就以從這名幸福的女子身上感受到她和這處悲傷之地的不同了。只不過這哪怕是瑪麗亞這樣說,她的丈夫卻執意孤行,因為只有這樣,對於主角而言,這才是真正的故鄉,亦者或說是他理想中的故鄉地。
而隨著瑪麗亞黯然退去、旅館的隨從、妹妹以及母親等人的出場,整齣戲碼的荒謬卻因為主角本身對於『幸福』與『故鄉』的執著而使他們所有人的痛苦加劇了。其從這三幕劇當中,作為觀眾的視角,我們必然能夠感受到母親對於『解脫』的執著,哪怕是短暫的歇息也好,母親長年對於活著的疲憊,或更說是被剝奪的幸福這事,相對於女兒正值年華時期的狀態,母親卻已不再有自由的渴望了;但是,女兒之於母親的不同,除了是她並沒有母親那般承受失去兒子的痛苦經驗外,更多則是沒有受到時間與命運的擺佈,且還有更多幸福等著他嚮往與實現,不過,就算從母女倆的交談中,能夠感受到母親的無力,但女兒殷殷期盼的自由,卻已將她們和所謂的『幸福』拉得更遠。
於是,女兒最後做出了行動,讓主角就此沈沈睡去、向著永遠的孤獨、不再歸來,但同時,當母親得知了兒子的身份與一切事情的原委後,卻也相繼和她的哥哥一同死去,只留下妹妹和瑪利亞,讓她們繼續接受這場現實與荒謬的消磨。
其從劇本對於《誤會》本身的荒謬性,建構人們之間不可能會有的幸福,這一切基於現實與理想的衝突性,也正是誤會情節最為荒誕的一部分,況且,從主角和瑪麗亞生活境地來到這處沒有幸福的所在,又怎麼能指望幸福的實現呢?但是,除了人們不可能擁有的幸福,主角對於故鄉的嚮往,或是母親對於解脫與死亡的到來,早已做好準備的態度,這一切的原委,卻又以最荒謬的方式,將現實人們對於故鄉與幸福的指望,一一消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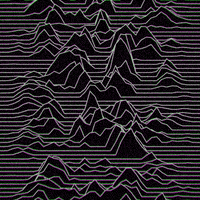
物自身的證明
同樣地,卡繆之於人們抱持『苟活』的解釋,其從《薛西佛西的神話》中的論述上,便就能感受到我們人之所以為平庸、與其沒有意義的所在:
無論是《誤會》中的母親基於終老與死亡的渴求,或是主角在成仁之前依然抱持著對故鄉的嚮往,他們作為『人』的條件,就已被時間和命運所圍困;乃至於從『薛西佛西對抗巨石的終極難題』再行深入探討,這無窮無垠逼迫薛西佛西的極限,只有當祂不再違抗命運時,才能夠以絕對超脫的精神性,應證自我的實現。而後當薛西佛西又再一次次和巨石搏鬥時,他卻早已超越了時間、擺脫了這束縛著他的一切,並再次獲得了命運的主宰,成為了物自身的存在。其後,從《誤會》中的人們對於幸福的嚮往與解脫,再轉向《薛西佛西》不再受命運擺佈的獨立意志,這凌駕於生命意義的實現,正是卡繆對於現實存在的質疑;同樣地,儘管人們終究無法越過這場生命體驗,但活著也並未代表毫無意義,只是在必然面對的死亡之前,我們應當賦予自身意義,並成為我們存在的證明。

被否定的自我→以死亡的平庸性指涉人性存在的惰性
而從側面來剖析文學詮釋中的不同面向,好比說卡夫卡在於《審判》與《在法的門前》遺留下的符碼,故事中的K為何成為了罪人?他究竟是因為什麼關係成為了被告,同時,在他罪行被定讞之前,K又該如何替自己辯護?然而,正當他因而陷入法律,在這往返書記、法院、工作與其親友關係的過程之中,故事更為核心的命題卻因此變得模糊——也就是K和他的原罪,這正是卡夫卡在劇中留下的疑問。但在另一方面,筆者認為《審判》並非不具有核心,其就如同法人所述:法律從來都不曾過給予過界線、只是不加以約束,而卡夫卡對於人們所謂的核心概念,也只不過是人們總想要試探的結論,卻總在無法揣摩到他的人格塑造、而將其視為晦澀難懂的文學而已定論之。
當然這其中也不乏能夠理解普遍讀者的疑問,尤其是如同《審判》在章節順序的編排上,或卡夫卡在論述本身的跳躍性,就為閱讀體驗設下了諸多門檻,以至於像是筆者在解讀其中的意涵、包括文意背後的象徵性,若只就將劇情強行拆開來分析、而不去處理卡夫卡與其他著作中的思想架構,便會使我在梳理文字的過程中,有過於強行解釋的意圖、甚者會脫離作品的本意。
但是,自從K被宣告有罪時,身為讀者的我們,卻也一同陷入了卡夫卡世界中的囹圄;回想K第一次為自己辯解、而後遇到了看守人、進入法院、或在一次次進入閣樓接受審訊的過程中,若K不加以揭露,是否就能延緩判決的下達?也就是說,當K執意要為自己的判決做出辯駁,因為人不可能無罪的天性,卻反而讓他更加向死亡靠攏,以至於在他生日在即的那段時間,便解釋了K為何莫名其妙的被帶上街、並就此結束了短暫的一生。
另一方面,再以權力身份關係做剖析,將K與另一名被告做比較,雖然我們並未能夠得知他最後是否被定讞,但是,再以兩人面對訴狀書的處事效率,《審判》中的唯一原則,不就再次證明了K作死的必要呢;再者,就算撇除執法人員、律師、牧師或他口中的預言故事,則以律師身旁那名普通女子再行判讀,讀者卻也能夠從女子和他的對白中,理解K人格中的諸多矛盾,無論是他逐漸失序的行為:包括受到法律影響的生活、抑或是女子質問他的內在本質,這一切事件堆疊下來,都更加暗示了K的罪行;並且透過他的處境,更引射著人們在社會關係中,若缺乏了人格的核心,便就喪失作為人的自主性,唯獨以失能的苟活著,無論是被判刑的K,亦者是與社會性場域依存的文化群體,這錯亂而無有秩序的人生,便就是對於我們生而為『平庸』應當以此為借鏡的。

意境的死→如詩人呢喃般
僅此,從文學中指涉的死亡象徵,繼續探入電影中的實際寓意,其『死亡』在影像語言中表達的意義,便也成為了我們再行思考個人在社會中依存的準則。而後,從文學轉向電影中詮釋的死亡概念,比方是從《審判》的語境,轉向鏡頭語言的象徵寓意,缺乏敘事主體的論述又該如何應證其中的連結性?此外,在死亡象徵的基調上,本文所欲探討的主旨:相較於『死亡』的符碼表層,或藝術家們所謂的情感解放,這以『超脫的精神性』帶出社會價值觀的衝突問題,惟是懷特獨白所面對的首要難題。
回到文本的實際範疇:死亡象徵的神聖性,這在前述所提及的作品概念中,就已出現過數回,比如《罪與罰》的拉斯柯爾尼科夫、《審判》裡面對判決的K以及在《誤會》這場悲劇中相會的母子,他們的境遇,皆是在死亡的解脫過程,證明了物自身的存在;而同時,對於其中隱性的詔示,文本中對於死亡的神學象徵,卻也經由這戲謔性的試探,被映照在敘事的情境裡。
同樣地,電影中對於死亡的指涉性,也具有相當明顯的諭示,好比電影作品《控制》所講述joy division團長在面對人生的抉擇,更多消磨他意志的正是在愛情與理想的建築過程中,不斷被剝奪的自主權;尤其,單就以作品的情境色調,也正能夠感受到故事瀰漫一種壓抑的氛圍。再者,若再去細數劇情和歌詞之間的對應,透過主唱字句間表達的情感,這無盡折磨他身心靈的精神狀態,也都再一次讓觀眾浸淫在主唱Ian同時面對三角戀情和音樂夢想時的各種衝突。而這一切,直到他逐漸失去控制、逐漸失去自己,直到傷心欲絕,也不得將他帶入永遠的黑暗之中;於是最後,因為這些痛苦的消耗,讓Ian選擇用自盡的方式結束他和樂團短暫的一生。但是,在那晦暗的個人特質以及艱澀難解的詞曲下,Joy Division的傳奇經歷,也早已成為後世轉載的輝煌歷史。
除此之外,不可忽略的是,電影透過這強而有力的黑白鏡頭,讓作為觀眾的我們,也終能夠再更涉入Joy Division深靄的音樂風格之中;而其關於Ian與他歌詞帶有詩人韻味的語境,也正如同他擷取人生經驗的反芻、不僅有Ian在人生不同境遇面對愛情與樂團人生時的總總縮影,更多的魅力正是透過那窒息的吸引力,將他日漸消沈的意志、隱隱作痛的身心責難以及背負詞曲創作時的自我突破,皆再一次用Ian自我厭惡的人生觀,與以將無意義的龐克精神從音樂中獨立出來。
然而,當音樂成為一種瀕死的行為藝術,Ian的個人實現,卻只有在夢想破滅時,能以用『結束生命』換來真正的解脫,何其令人感到心碎;即便Joy Division的音樂歷程在去美國之前便結束了,但至少也還有電影作品的存在,讓樂迷們還能夠一再地進入到Ian那極盡瀕臨死亡的音樂創作中,感受這一段生命譜寫的靈魂輓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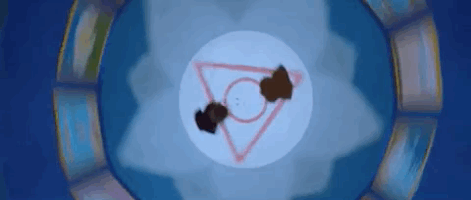
死亡與解脫→情感的昇華
就直觀來看,作品《控制》中對於死亡象徵詮釋,確實都太過清晰了;但同時,也正是受到Ian的影響,讓電影能夠以如此透徹的態度,將生命毫無意義的觀點抽離出來。不過除了控制之外,其他電影又是如何塑造死亡的?
想當然,對於死亡的概念,也絕非只有一種形式,比如說在前面幾集節目內容中就有提到的《我想結束這一切》,就是一個經典且易懂的例子,便也就讓觀眾能夠以一個意象的形式去理解恐怖電影的構成。雖然這部電影和控制在氛圍上,有著相當低沉的調性,不過比起《控制》而言,這在《我想結束這一切》裡的老人所抱持的生命態度,卻並不是從死亡中解脫,反而是在接受時間給予他一生的孤獨之後,接納自己將要死去的事實;並且,當老人戰勝了死亡恐懼的心魔時,他便也就不再孤獨了。

以光為引介,帶入死亡的神聖性
再者,關於死亡的神聖性,筆者這邊還想再一次提到《燈塔》這部作品。其概念與前述並無異同,惟是這些角色在經歷死亡的過程時,藉由『光』的引介,使得作品所欲表達的概念——也就是超脫的實際形式,被真正的實現在觀眾的眼前;就好比說『死亡的凝視』,當我們透過作品的詮釋、並且加上劇情前後的調配,而使感受到角色心境更加幽微的變化——死亡,也就在他們和鏡頭凝視的頃刻之間,發生了!就如同奇蹟般的,成為作品的共通語言,無論是《燈塔》中經歷死亡的兩名看守員,或是在更為經典的作品案例《發條橘子》、《鬼店》等諸多例子,便也都能夠觀察到作品是如何透過鏡頭去捕捉他們死前心境的。

空間的指向性→劇本已死的重新解釋
而撇除前者對於時空間性的屏除,並在更近一步從鏡頭語言的表徵進行二次論述,死亡又是否能夠以方向性而作為一種形式的展現?比方是故事透過角色的凝視,從而帶領觀眾在鏡頭交流間,達到彼此的共識?具體來說,就以發條橘子在分鏡上的表現做範例,其關鍵鏡頭對於主角的眼神方向,無論是第三人稱敘事觀點的構成,或更為主觀的鏡頭設計,這種側重的角色關係,就越加顯示了故事情節與人更為緊密的連結;尤其是當主角在接受『人格重建』的過程時,鏡頭下,我們可以從醫生的對位,再次以觀測者的視角窺探主角掙扎時的模樣——而其在關鍵事件中,就是經歷了人格的二次塑造而使他迫於行為的壓抑,逼得他最後選擇以墜樓的方式結束掉人生;不過關於電影與原作在結尾上的安排,仍較有差異,但是,在這接受人格改造實驗的境遇後,作品所欲探討的恐懼形式,也正是基於人格被抑制而扼殺了人格本身,並在人格的原型上,其所塑造的人格,或者稱為第二意識,是否還能稱他們兩種人格為同一種概念?亦者在人格被抑制之後,新的人格與之帶來的行為模式,又是否該被視為不同身份以論定之呢?
再者,回到鏡頭語言的方向性進行延伸——這部同樣以高度實驗性質的劇情作品《聖山》,又再一次地向我們展示了『形式的超越』:好比說是劇情從主人翁的敘事上,將其刻畫為一場『試煉的過程』,而其中,便不乏是宗教與其信仰價值觀的探討,同時,也包括歷史與其文明發展組成的基調,將這一切反常理、反敘事的劇情概念,與《聖山》的核心主旨劃上等號,但是,作品在另一方面,卻在結論上,向觀眾道出了完全平行的答案;也就是說,當觀眾和主角群演一同進入了聖山所謂的試煉之中,見證了大師的門徒、也見識了革命、割禮或其以眾多行為表徵暗示的神秘符碼,卻直到電影結局,被大師告知這一切都是精心設計好的賽局。於是,當鏡頭平行向遠方延伸,就連燈光、劇組人員都冒了出來,卻只留下我們這些觀眾一頭霧水。
而即便如此,在電影循序漸進的論述過程中,《聖山》作為反敘事的邪典代表,卻也證明他在當代經典中的地位,尤其是能夠讓人在端詳其作品的過程中,使我們感到故事更為深層『不得其門而入』的距離感;或甚者是在一切指涉為修行的心路歷程,卻在最後用鏡頭披露電影一場超現實大騙局,將其再行重塑『劇本已死』的荒謬之作,卻也使得筆者能夠藉由電影與其作品的諸多平庸性,再行解讀文本中的象徵寓意。
不過,既然本文的重點是死亡的文化象徵,那是否所有代表所有的死亡都有其意義可言?有鑑於此,若僅以『死亡』的純粹性作分析,便可以肯定作品在形式與其意圖的詮釋架構下,必然有其意義可言,不過,無論它們的形式或意圖,也僅僅只是作品的基本定義,且況再論敘事者的目的,就得另闢一篇內容出來,並不得只以此篇幅而論之。

歸納
回到文化象徵的主體:其無論是文學或電影,死亡的精神分析,透過本文的論述便以論證它們存在的關係,即如《誤會》以荒謬建立起劇情結構的基質,亦者或是《審判》中面對失序的體制與逐漸失去自主性的人格,透過作品中隱含的核心構成,
那近似於寫實的生活樣態,卻也都一在地被投射了出來。再者,就算是如卡夫卡的作品經常得透過『解碼』的過程,才能夠理解其象徵的實質意涵,但當讀者能夠觀察出作品之中的規律,便可依循其中的準則,並應證故事本身存有的真正意圖。
另一方面,電影相比於文學,也較能夠體現出影像的優勢,其從《控制》一著為舉例,作為觀眾的我們便能夠感受到Joy Division主唱那份帶有自我厭惡感的心路歷程,尤其當我們被Ian的歌詞吸引,便就能再一次感受他那背負著家庭與事業的壓迫感,尤其還包括他極力想抽離的選擇權,卻只能透過在歌詞裡抒發生活無法逃離的迴圈,於是在最後,沈沈的選擇以死亡帶來解脫。
同樣地,從死亡的文化象徵一路轉向鏡頭語言的具體表現,燈塔在死亡的行動中,便就更加具體的向觀眾展示了作品對於死亡的企圖,比方說,溫斯洛最後跌下燈塔、並被烏鴉啄死的鏡頭,故事透過那樣寂靜的氛圍,加深刻畫死亡的氛圍感,無論是以人物的凝視,或更直觀、更平行的鏡頭構圖,其就形式的表現意義,便也成為了它賦予故事實質寓意的具體證明。
於是,從死亡的精神性一路轉向鏡頭凝視時的氛圍感塑造,我們對於作品的內外構成也就能夠有更為深度的理解——尤其是那些不得好死的人,亦指涉劇中未必有所明確告知的安排,在過往的社會性解讀中,我們經常會以開放性觀點而示之,而在透過此一觀點的論述後,過往作品處理的拙劣之處,便也就能以物自身的存有觀點,釐清作品與文化符碼中的邏輯謬誤;縱使以文中所述的驗證方法有其過度解釋的成分,而這種解構文本的梳理過程,在應對必要情勢時,卻也成為分析時,具有非常關鍵作用的特殊之處。

補充說明
為建立本文以及內容識讀之真確性,其關於『死亡象徵』之核心概念,筆者則是透過形式與其精神分析,再行將『死亡的實際行動』轉向對情感意志的『超脫』,也就是從自我證明的過程中,重新探討解放與存在的可能。不過基於筆者對於『死亡』的論述仍有不足,尤其是內容著墨在『文學性的追求』,使讓本文較其論述產生過度的模糊。
以下,懷特獨白再行提供此一書單,為內容呈現上的不足進行參考,詳情請參見本集專欄之節目資訊:
- 從赫胥黎理解時間敘事觀《島 Island》ISBN:9789869705165
- 進入卡夫卡的思想世界《審判 Der Process》ISBN:9789868834248
- 從杜斯妥也的的道德觀,談人本的極限與社會性之死《罪與罰 Crime and Punishme》ISBN:9789577300539
- 比較:第二人格的解救《發條橘子 A Clockwork Orange》ISBN:9789861207575
- 虛無與人荒謬的本質:從抽離與自我重建《誤會: 卡繆的三幕劇 Le malentendu》ISBN:9789869677752
- 理解卡繆作為思想的第一人《薛西弗斯的神話 Le Mythe de Sisyphe》ISBN:9789862138144
- 我與杜斯妥也思想之連結《地下室手記 Notes from Underground》ISBN:9789869231893
- 淺談物自身觀點《一切能作為學問而出現的未來形上學之序論》ISBN:9789570860443
- 關於現象學觀察與存而不論之研究《存在與虛無》ISBN9789866723704

敬謝與結尾
本集節目在此告一個段落,感謝您的聆聽。懷特獨白是嚼嚼廣場旗下的電影評論媒體;我們用文本分析方法,挖掘作品埋藏的訊息和信號;藉由重新解構電影的過程,帶領觀眾探索影像敘事中的文化符碼。

同場加映
節目最後,筆者想用這首來自於joy division的Love will tear us apart進行收尾,就讓我們一同沈浸在Ian富饒深意的歌詞裡,為今天的內容劃下句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