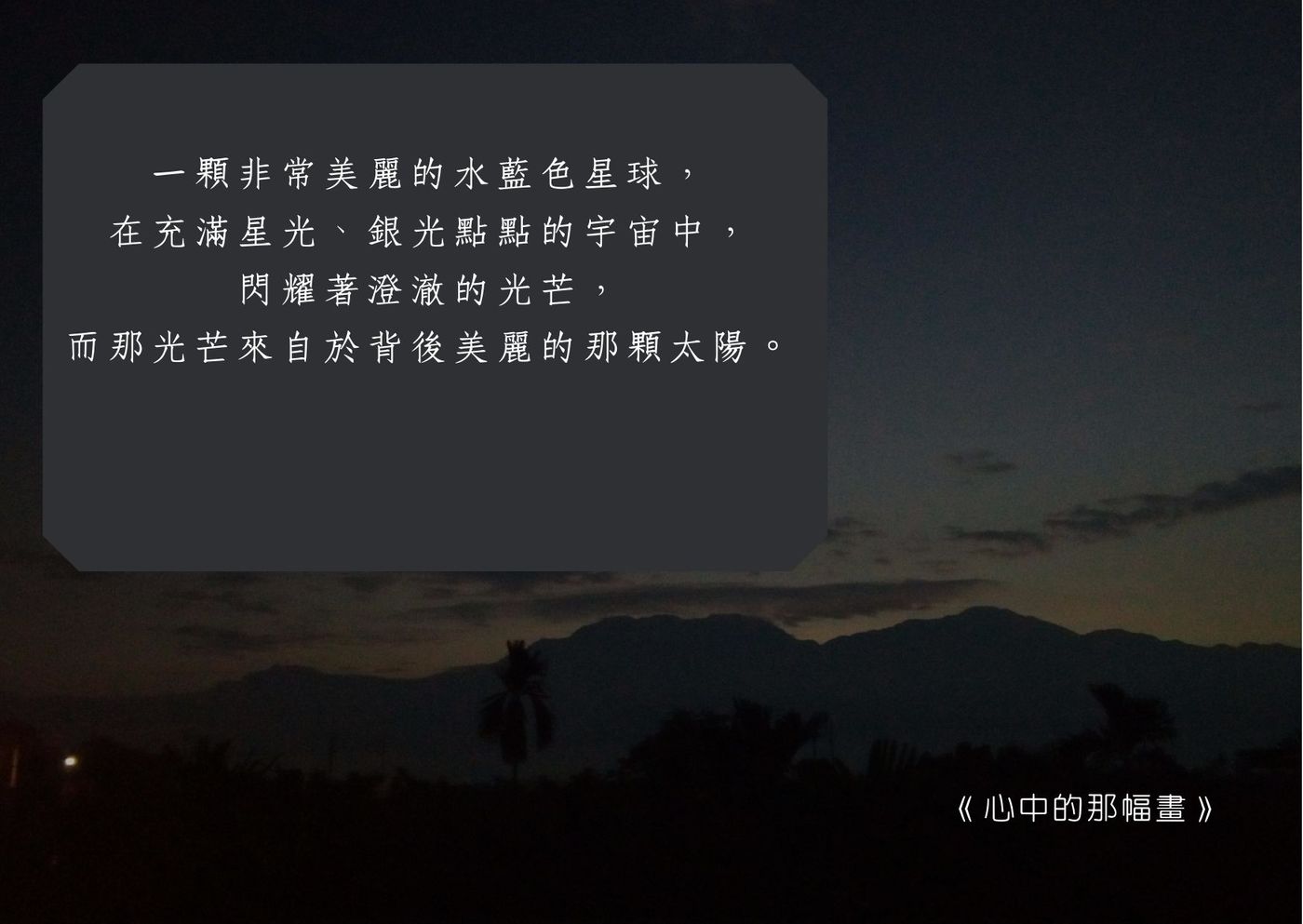我和阿城結婚十三年,好不容易懷上第一個孩子,只可惜三個月還沒到就出了意外。
孩子沒了。
我整日以淚洗面,連我們的感情都產生了極大的危機。他請了半年的假,想要陪我出去走走。
“孩子會有的。”阿城抱著我說,“如果我們分開了,就什麼都沒有了。”
我輕輕抽泣了兩聲,被說服了。
放下手裡還沒能給寶寶穿上的小衣服,和阿城計畫起旅程來。
半年時間,自駕遊,可以走很遠。
阿城租了一輛不算豪華的房車。
我們大部分時間在山林裡看風景,偶爾到城市裡補充食物。
想到可以遠離城市的喧囂,整日呼吸新鮮空氣,我的心情就好了很多。
三個多月後,我們居然在山林中找到一個村子,就像是書上說的桃花源,絕世而獨立。
地圖上根本找不到這個地方。
可能就是因為鮮少有外人,整個村子透露出古色古香的味道。
村子裡沒什麼農田,靠著一個清澈的河流,村民們以捕撈河鮮為生。
他們很熱情,拿出大量的河鮮招待我們。
我有些不好意思,提出可以付一些錢,作為這一餐的費用。
村長拒絕了,說是用不到;不過村裡人其實很喜歡這些偶爾出現的外來人,因為河神也會隨之出現,保佑村子一年的風調雨順。
阿城好奇地問起了河神。
村長表示他們也沒有見過河神,因為規矩是不可以窺探河神的樣貌;如果我和阿城晚上想到處走走,不要靠近河邊。
這是對河神的尊重。
阿城拉了拉我的手,對村長道了聲謝。
我們被安排在一個村民家裡。
他們家有個小男孩,看起來很乖很可愛;如果我的孩子能出生,應該也是這個樣子的吧。
小男孩把我們帶到房間,我從箱子裡拿了一些零食給他。
他接過零食,咬了咬嘴唇好像想說什麼。
我摸摸他的頭,安撫他緊張的情緒。
“姐姐你人真好。”小男孩顯得很是沮喪,“不像之前的外來人,覺得自己是大城市來的脾氣壞得不得了。姐姐晚上不要出門,明早就走,越快越好。”
男孩的母親聽到了,驚慌失措般跑進來抱起男孩,一邊走還一邊向我們道歉,說小孩不懂事。
最後連我的“沒關係”都沒聽到,直接把門關上了。
“不太對勁,”阿城皺了皺眉,“村民們都太熱情了;有時候反而是小孩子最誠實。我們住一晚,天亮前出發。”
我沒反駁,算是默認了。
但是阿城有些過於緊張,用行李抵住臥室門。
剛躺下,外面傳來嬰兒的啼哭聲,一聲一聲的讓人揪心得很。
我推了推阿城,說想要出去看看。
阿城轉身抱住我,說真的有事村民會管的,我生氣地推開他;阿城被我磨得沒有辦法,只能應下來,換了衣服便出去了。
出門前一再叮囑我一定要鎖好門。
過了半個多小時,嬰兒的哭聲都還沒停。
我很是擔心,拿起手機給阿城發了一條短信;十分鐘後,阿城還沒有回復。
電話也沒人接。
我徹底慌了,連續打了幾十通電話,還是沒人接;我丟開電話哭起來。
幾分鐘後,手機終於亮起來,阿城終於回了第一條資訊:
我在河邊。
附帶著一張照片,是夜晚的河水,在月光下波光粼粼的反射出星輝般的光芒,美得有些耀眼。
到河邊找我,阿城的第二條資訊。
我擦了擦眼淚,披上了外套。
越往河邊走,嬰兒啼哭的聲音越為明顯,還帶著一點風鈴清脆卻略顯淩亂的聲響。
我突然遲疑起來。
村長說過,不要靠近河邊,這是對河神的尊重。
我又給阿城發了條短信:
找到孩子了嗎?
啼哭聲和風鈴聲停了片刻,卻突然一同在我身後響起來。
更為詭異的是我腳下原本平靜的草地,出現一條河流,從我身側緩緩流了過去。
我的身體像結了冰一般,幾乎無法動彈。
但我還是強撐著向後轉去,想要知道此刻讓人恐懼的聲音到底是什麼。
餘光中,一些長長的像枯樹枝幹一樣的東西慢慢出現,底端掛著一個風鈴,晃來晃去,像鐘擺一樣不停。
我順著這些風鈴向上看去。
那是一個人,雙腿已經沒有肉了,枝幹是他的光禿禿的骨骼。
不,那不是一個人,是很多人被吊成一排,有規律地像鐘擺一樣左右搖晃,甚至形成一個個優美的弧線。
阿城,在一排的最後面,睜大了雙眼看向我。
再也不會有第二個表情了。
白鹿青涯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