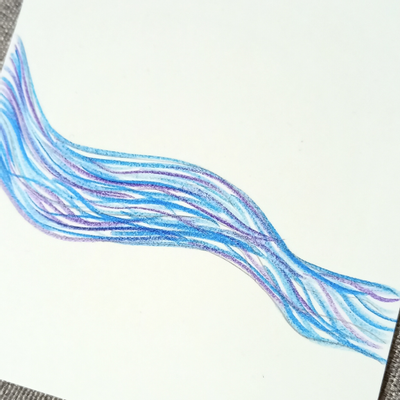離開時夜被掏空一層,氣溫比剛才沒有低多少。
我們出到街面,有點濕氣襲來。她換回高跟,淺灰拖鞋折疊塞進紙袋頂層,倒像是替今晚留下紀念品。
地鐵入口的階梯往下抽成冷光井。
末班前最後幾組人影匆匆刷閘;廣播用公式語氣把夜擠壓成剩餘幾分鐘。
我們站在閘機外陰影處,還沒有來得及對時間反應。
她想一秒:「應該會,比前幾天好。」像剛剛得到一張生效的處方籤。
還有兩分鐘。
再多說什麼都會顯得過度加工。
我差點順著那個浮在腦中的成語往外丟:「其實我們相見 —」,
她眼神很快掃過來,提前為那個太俗氣的成語截停。
後兩個字停留在我的舌根,原地解散並未流出。
找不到合適的語句後,我終於放棄,只是故帶輕鬆地說。
「那就 —」
她很輕地笑著接著說:「就這樣。」
沒有交換聯繫方式、沒有下一次的劇本,像把九曲橋最後一轉折留成空白,允許它在未被預定的某個時間再對齊。
她刷卡進去,回頭那一眼不是確認我還在,而像給今晚整段時間線做備份。
她與我反向,末班列車的風先到,帶起她髮尾一撮,再次眨眼時人已消失。
列車開動、車窗掠過,我在快影裡彷彿看見那雙拖鞋的淺灰,又很快被速度抹平。
地面恢復列車駛離後、一如既往地的寂寞。
我沒有刻意往前或往後,順著一股不指向她也不指向我的夜風慢慢走。
=== 往浦西的出租車上 ===
眼前,
車窗玻璃把浦東街燈拉成水平流線,耳機裡歌曲主旋律又響起,那四個字再次鏗鏘入耳。
我讓它們就停在那,不去補完當時被她截斷的半句,讓遲了的相見保持未完的故事情節。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