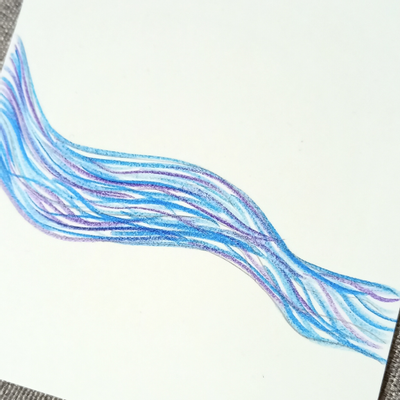離開餐廳那圈暖黃,我們又刻意往前多走幾步,直到背後的人聲淡去。
她肩膀還是硬著,呼吸短促,像飯桌對話還在耳邊緊緊纏繞沒有釋放。
我提:「先別就地解散,去坐船?讓風把剛那層油味、場面話吹掉。」
她看我一眼,像在算:剩下的電量是否還夠支援一段屬於自己的時間。最後點頭。
外灘此刻亮得像重新被上彩釉,江面被遊船灑出一道道五彩的亮痕。
往售票口走到一半,我想到等下還有更重要的事要處理,跟她說我去買個東西,請她先去排隊。
走到貨架旁邊,視線掃過一堆深色、亮銀小包裝,那一排物品很容易讓人多想。
不假思索地,我伸手去拿旁邊掛著的一雙軟底拖鞋:淺灰,超輕,塑膠套包著,有點單薄,但也剛好實用。 結帳,掃碼嗶一下就過。店員要給透明袋,我問:「有不透明的嗎?」她換一個袋子幫我打結。
我回到隊伍,手中捏著袋子,走近後打開,亮出那雙淺灰軟拖,大小估計應該適合。
她愣半秒,眼神裡那層戒備跟猜測像被溫水化掉,換成一種軟掉還來不及整理的表情。
嘴角往上一點:「你——」後面自動靜音成一口吸氣。
她低頭解細帶,踢掉高跟,腳背上隱約還有一圈淡紅壓痕。把腳滑進去,腳趾一放鬆,整個肩膀往下掉一截。她抬頭:「謝啦。」語氣很平,沒加戲,比任何一句玩笑都貼近。
我們排到接近末班。她說「正好」,像順便對自己交代:今晚還能再多撐一小段,不是直接收攤。船開出去,外灘那邊跟浦東那邊像兩種年代的句子,混在江面上變成一種淡淡的流動畫面。
她一開始只是站著,看燈光掃過側臉;幾分鐘後,肩線慢慢往下垮,像終於確定這裡不用再演誰。風把餐廳留下的油鹹味一層一層剝掉,剩下海潮味、金屬味,還有遠處偶爾傳來的船笛。
我說:「剛那桌妳幾乎沒有好好地吃一口。」
她嗯了一下,把那聲音丟往江面,不撿回來。
那聲音沉下去的速度,剛好讓我意識到:有些鬆動來得雖晚,但還不至於錯過今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