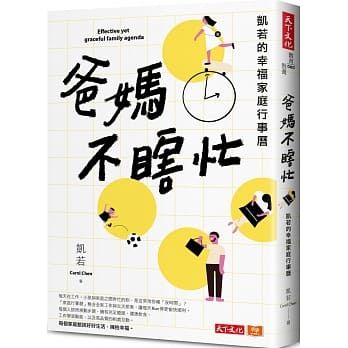寄書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我要寄書到上海。」
郵局人員抬起頭來,除了例行的給表單、秤重,還告知規則。「書在中國是敏感物,我們可以幫你寄,但是能不能順利寄到有風險。如果是禁書,你的收件人可能會被處罰。」 第一次遇到講這樣多的郵局人員,他盡了他的責任,卻將擔憂甚至恐嚇留給了我。
是嗎?我以為最多只是寄不到、被攔下銷毀而已,居然會害到收件人?望著這本《自由不是免費的》,雖然已經取下書衣,書封顯得相當樸素,但書名畢竟還是橫在那兒,它看來已經踩在紅線邊了。事實上,這本書並不那麽政治,如果它叫作《兩代記者十日談》就好了。
陳老師是我在上海認識的朋友。那是在《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演講的場子,他的詭辯與妙語吸引了不少在場年輕人,一片「中國在進步,大國不容易」的肯定聲中,一個個頭嬌小的中年女觀眾舉手發問:「都說跟著黨走,但如果黨走錯了怎麼辦?」就這樣,活動結束後我沒去簇擁著胡錫進,而是認識了陳老師。
一會兒,陳老師也發語音留言過來了,緩緩說道:「其實也沒關係,我確實也是她(查建英)的讀者,看到她有新書發行就想讀。我不知道這樣有什麼問題?『不知不為過』,我是這麼想的。」
不過就是分享一本書,不過就是寄了一本絕對不是什麼傳播極端思想、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書,不懂為什麼兩個超過40歲的成人,要這樣擔心、解釋,自己都覺得窩囊。
不喜歡生活裡有這樣的陰影,何況我明明身在自由之地卻仍得受制於對岸制度。書能否寄到已經不是最重要的事,會不會害到別人成了最大的心理壓力。
一週後,陳老師發來簡訊:收到書了。
比起郵遞跨越海峽兩岸、跨越兩個政治實體的不確定性,先把書親自帶到中國,再從當地境內快遞,就幾乎穩妥了——至少,我入境中國時沒遇過開箱檢查。
記得那是誠品敦南店收店前幾個月的一個冬天夜晚,逛到了十點多,忽然看到好幾本胡蘭成的書。而一位不曾謀面但請益過的大陸微信朋友L曾跟我說,可不可以幫他買胡蘭成的書。我把那些書拍了下來傳給他,問他要哪一本。
「全都要!」微信對話中忽然發現這幾個簡體字有很興奮的表情。忍不住回:「為什麼呀?」他說,有個很要好的朋友,酷愛胡蘭成的書,他一直很希望能送這個朋友胡的書,但這在中國是禁書,要不就是刪減過的。
不只是《今生今世》,還有《戰難和亦不易》等多本他的政論集。胡蘭成是汪精衛政府下的宣傳部長,一個存在僅5年的政權,一個有違中國歷史抗日主旋律的政權,相關政論的價值何在?因此幾乎沒有關注過。
幾個月後,這一袋書跟著我到上海,又跟著順豐快遞進到了河北省。年輕的送快遞小夥子簽收時沒多說什麼,胡蘭成對於20幾歲的他們來說,大概是沒聽過的。
胡蘭成的書在中國大陸是禁書嗎?可是明明當地的國營書店裡還找得到「今生今世」。後來有機會請教上海研究張愛玲的學者,算是解疑了,他說,這幾年應該是出版不了了,我看到的是早些年出的。
中國的很多事情都是這樣,你以為書被禁了就是下架都買不到,其實分成不同情況:不再版、網路書店下架但實體書店不處理、全部通路回收等。不懂這一層,常會困惑,聽說某書被禁了,但其實又買得到,那官方究竟禁了沒有呢?何況現在宣傳部下的命令許多是沒有白紙黑字的。
胡蘭成作品的旅行還沒結束。快遞送走後大概兩週,我正在南方城市出差,L來電。我們很少通話,這次他顯得迫不及待。電話那頭他語氣興奮地說,「書送過去,他高興壞了」,這摯友是北方某個「經濟百強縣」的地方官員,要我什麼時候去玩時務必聯繫,讓他招待。
真沒想過,在我生活城市裡這樣普通的資源,居然成了到海峽對岸行走交往時的資本;而超過70年前胡蘭成寫的文章,因為作者背負「漢奸」之名被禁,反而奇貨可居。此刻的開心和寄書給陳老師時的惶惶不安其實都是出於同一回事——資訊落差與管制落差。
「這麼晚了還在外頭?」那天在誠品買書時,L透過微信問道。我以為誠品24小時書店已經名傳千里,看來也不是人人都知。L後來說:「真好,書店這麼晚還在營業;我們這邊零下8度,外面商店早都打烊了。」
於我,那習慣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原來都不是理所當然。
這會兒,是要請上海朋友寄書給我了。從沒想過這會有什麼問題。
Y是一位小眾的藝術與文化活動策展人,從她在網路上的動態得知,她策劃的活動最近集結成一本小書,主題是關於COVID-19疫情對生活的衝擊,其中又特別關注女性的角色。
這完全符合我關注的範圍,便直接向她買了一本。Y說,希望郵局可以寄。
「有什麼不可以的!又不是從台灣寄過去。」
「現在誰知道?」
果然中國的郵局寄不了,最後還是走民間快遞公司。據Y說,因為她這本書沒有申請書號,郵局人員堅持要拆書的塑膠封套,Y就寧願不寄了,「這種形態就讓人厭惡」。而順豐快遞的簽收人員雖然也翻了翻書,但還是寄了,「可能自由度還是大些」。
實在很抱歉,讓Y白跑一趟,還要在網上填寫那麼多郵寄訊息。Y說沒關係,她其實也趁此機會了解當前郵局對於寄送審查的情況。
說到書號,那是另一個意識形態的緊箍咒。在中國,每本販售的書都該申請書號,取得書號的過程就形同歷經至少三個關卡的出版社內外部審查。有些不願大費周章申請並被監管的書,便以200本以內少量印刷的方式,在同好圈內流傳。不過,隨著這兩年官方以「文化執法」的名義加強取締,一些朋友說,連這樣的小眾空間也在被壓縮。
只是,沒有書號的書,連出海都不容易,要被基層的郵務人員拆封,用他們檢查挑毛病而非欣賞閱讀的眼睛審視著。
一週後,我收到了這本不敏感但也不願意被檢查的書。
「收到了嗎?」
「還沒。」
「咦,奇怪,寄上海只要一週就收到了,怎麼寄廣州已經超過兩週了還沒收到?」
「不知道啊,路上有各種可能。」
只能等了。這回一點都不提心吊膽,因為寄的是給0到3歲小寶寶的童書,不是甚麼有思想問題的書籍;只是覺得拖太久是不是寄丟了,真是這樣就讓人惋惜了。
和在廣州的M用臉書訊息溝通著,雙方暫時都只能等。
這年頭,郵遞雖然仍讓人牽腸掛肚,但在各種網路通訊軟體的輔助溝通下,由此產生的誤會應該是大大減少了。
戀愛中的男女,男生寄了信確認彼此關係或者求婚信件給女方,但信被女生的家長或學校給攔了下來,於是女方從等變成怨,或根本對男方意圖一無所知;原本可能的人生軌道就這樣走上了不同的路......電視劇不都這麼演嗎?
如果當時男生寄了信,然後發網路訊息給對方說:「我寄了,你幾天後應該會收到,注意一下信箱」,很多人生路是不是就不分岔了?不對,這男生根本就不會手寫信,直接寫電子郵件或在溝通軟體上發幾行字和照片就好了。但是,如果寄的是一本書、一盒茶葉、一份精心挑選的禮物呢?
在網路便利、數位監控也發達的時代,最傳統的郵遞依然是讓不得不使用它的人最提心吊膽的傳輸方式。因為它沒有什麼躲開監控的技巧,不能用暗號改關鍵字,要寄的東西就在包裹裡,對方資訊也必須真實,內容物不能亂填寫否則郵局不放行。簡言之,行與不行、過與不過,都是一翻兩瞪眼的事。
前些時候翻閱著剛再刷的「殷海光 殷夏君璐書信集」。
殷夏君璐在序中寫道,歷經抗戰和國共內戰,在局勢混亂且通膨嚴重的時代,他倆的通信沒有間斷實為奇蹟。尤其當時每遇寒暑假,她到鄉下親戚家住,那裡的房子沒有門牌街名,來信必須先寄到漢口親戚開的藥舖,等到有人要去她居住的鄉下時才會帶給她,兩地步行要兩個小時。
但她說,當時的人對寫了字的東西都畢恭畢敬,把信件當成珍品來處理,知道這些對收信人非常重要,所以傳送信件時格外小心。「在那兵荒馬亂,社會續蕩然無存的年間,信件能平安到達收信人手中,實在要感謝中國當時的郵務員和義務送信的鄉親們」。
現在已非戰爭時代,郵政發達,收不到信的理由卻多了「國家不許」這樣的人為障礙。
至少,三週後,廣州朋友收到了我送給他小孩的書。END
1會員
3內容數
留言0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