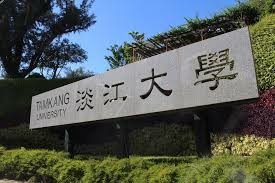就歷史上所屬主體的意義來說(壹)
關於福岡的旅遊紀錄

拍攝:Ken (博多車站前的夜間)
:工作日的晚間8:00,在博多車站的博多口,充滿一種爛漫的氛圍,這或許是在日本夜晚能有所獨特的感受。
第一部分 關於福岡的旅遊紀錄
以博多、天神為中心構成的福岡市區,再以北九州、自福岡向西南部延伸的,一側是對馬海峽的唐津灣澳,相反一側的濕潤景象下,長崎本線的綠號列車奔馳於佐賀的氾濫平野,彩霞則藏匿於山林水秀之間。

拍攝:Ken(綠號 特級列車的窗景)
:位處於九州西北側的佐賀有著大片的氾濫平原,若是從博多乘坐長崎本線的特急前往豪斯登堡、佐世保或長崎市區;那麼大約在車程開始30分鐘後,列車駛出福岡市區後其四周的景色會漸漸變得寬廣,除了大片田野與無數灌溉河渠之外,還有於遠處形成一線的丘陵地形,這裡的景色令人舒暢,其實此處更有可能在上古時代就已然擁有穩固的宗教秩序,又作為日本文明的濫觴,不管是否為普遍意義下的闡述。
若說起伴著福岡處於九州的意象,對我來說她是少女如時逢節日的秀麗著裝,一層衣物敷上另一層外衣,不久又是謹慎且留心地繫入裝飾,端莊優雅,因而使那身可愛衣著遮掩了青澀脆弱的體態,她無法嚮往花兒的自由,為著時節多少又能知曉自己的生命,因為不論何處,家族向著世界,散發的一切榮耀,是她被告知為她所有的能力,然而榮耀之刺眼卻令她無法眼見自身,認識自己。
一直到冷戰結束的20世紀末,北九州作為日本歷史的一處重要場景,從古代商業興起、元朝襲日,再到幕末工業時代興起、擴張主義在工業發展上的野望、戰後意識對立下的人群移動⋯歷史的繁雜,正如理想一層又一層包覆而上,新來的緊接取代陳舊的,而身屬於九州的歷史之所以特別,是就其歷史所在意義的畫面,遠比其主體所建造的選擇來得豐富;即便時代中心位處於遙遠的一方,不論時代為著奈良、京都或是開城、汴京所圍繞,九州同時是相異文明的交匯處,也是數十道隨著歷史軌跡推進而互為應稱的象徵。

拍攝:Ken(於日豐本線北段所拍攝的一側窗景)
:自日豐本線的列車車窗望去,處於起點小倉的北九州段路線,若稍有注意窗外的景色,即便特急列車的奔馳行駛,在無數流動的風景之後,唯一使人震驚的,是層層民房後的工業園區及數座豎立於後的煙囪;工業興起的圖像,作為九州歷史的重要轉淚點,即便進入日本現代史,這依舊顯示出深刻的印象。
不妨把福岡的意象從文化的純粹經驗上延伸開來,風景以層層堆砌而成又彼此相異,從峽灣到田園,夜間市街的燒烤店的霓虹燈到居酒屋的畫板照片,熙來攘往的上班族之中,不知多少交錯於自釜山渡船而來的旅客。
正如福岡的歷史:上個世紀還籠罩於戰火與意識形態之下,於此時刻又能築起層層高樓與觀光百貨,不僅僅是福岡的時間流淌著,隨著歷史的滾動,文化的碰撞正如氣旋轉動那樣,首先是東亞大陸的數個王朝、再來是處於半島而生的種種移民故事,從偏遠山林水秀之地傳來的食譜,現代民族意識的緊張,隨著微風吹拂下,作為文化內涵的花瓣,飄逸於暖陽照料的畫面,顯得繽紛不止。
第二部分 處於民俗與歷史之間的問題
不過,正因福岡從不屬於我們過往歷史所要關注的主角,而就那樣的美好便會置於內在並且不向外顯露的,她作為歷史的重心,卻不會是眾人所渴望思考的起點;因而那樣的可能,發展如此深刻的視角,不管那是否就以人所要去超越的,或是她儼然鑲上一種純粹經驗的存在,也就是說她成為一種存在的樣態。

拍攝:Ken (取自 2023年春季張貼於博多車站的宣傳廣告)
:一份處於車站內校園宣傳的廣告,或許會是一種城市哲學/社會學的思考起點,然而處於思考之下的我們,若是要為他人乃至社群帶來關切,那更不可能去逃避自身當下所要實踐的意義;或許這樣的海報,僅僅只能作為一種文化意識下的世俗產物,然而我卻可以嘗試先去理解畫面之下人物所作為何者,也就是誰?進而我才有辦法去理解其為何而做?因而那是如何地行動?這也是身為旅行者的可貴之處,他去思考他所理想的。
就以民俗的任務來說,其做思考努力就是向多樣的他者給予揭露,因而可以說民俗的方法首先去設想了一種他人的觀念,這樣觀念若被置於公眾的視野之下,其建構與詮釋亦是可能,然而這樣的可能卻造成了個體潛能的存在問題,乃至歷史哲學的問題;對於時間意識的忽略,且又快速地造就數種文化的符號,也產生出一種意識形態的對立。
這也是為什麼民俗無法解決廣義的教育問題,其中包含的現代性之特徵,也就是說就民俗觀點下的一種文化,他不考慮為人個體的究極,或說是一種人的潛能,而僅僅是指出其實然之理解,或理解的這項行動本身。當然這也可以憑藉語言質料的深刻體會而進入,也就是說:存於個人內在的語言,亦表示她自己之所以這般生活的模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