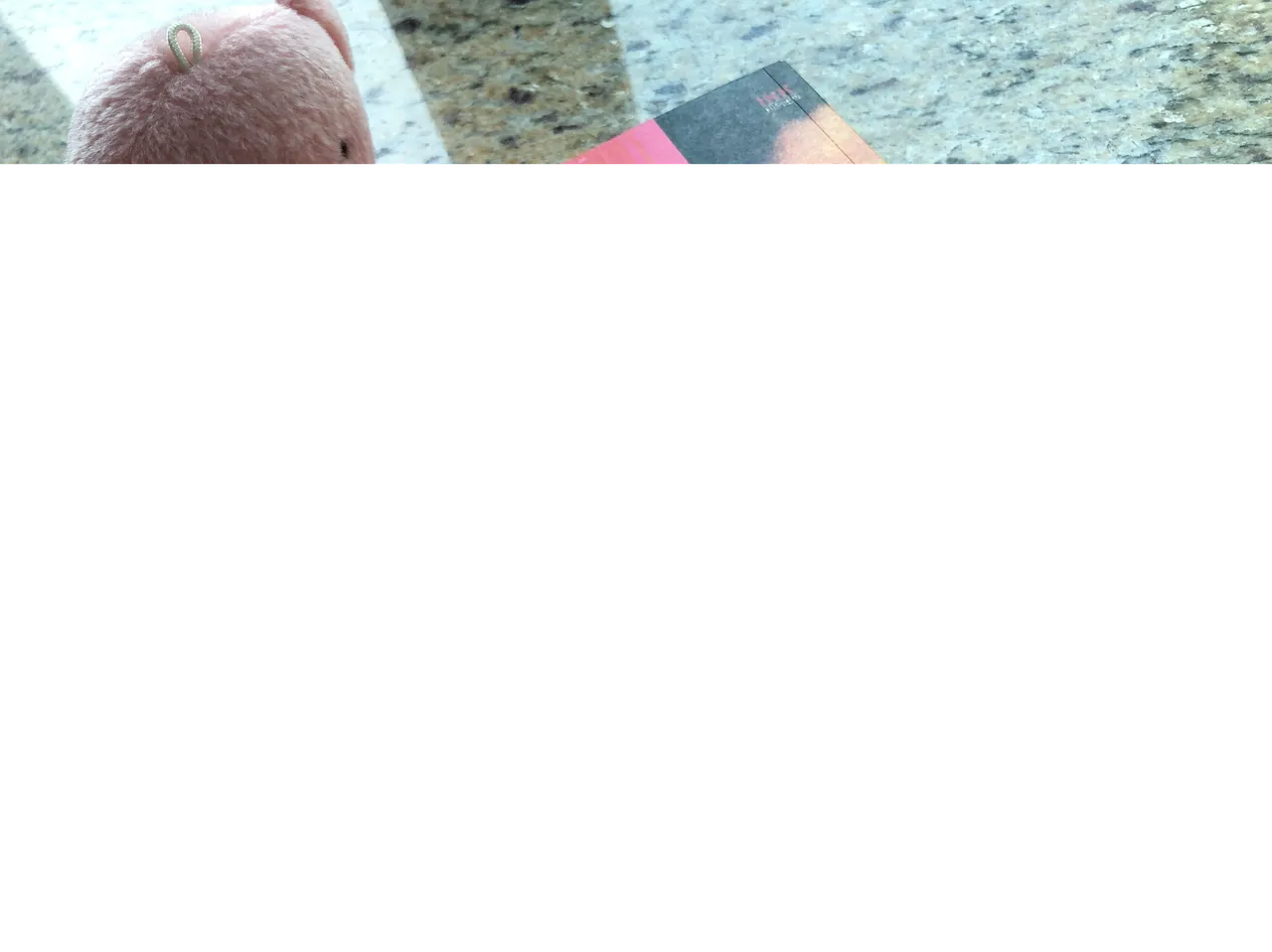每當彷彿走進了亂世,我就會想起《霸王別姬》(1993,陳凱歌導)。它訴說了一個關於中國如何碎成一地的故事。每再看一回,與自己所再的時空再一次對話.都有新的體悟。我總以為,如果兩岸真能看透這部作品,就能知道彼此的距離已是多麼的遙遠,或者多麼的相近。
十八
這是一部小我一歲的電影,我幸運地在18歲與它在學校裡的劇場大銀幕相遇。儘管在課堂中播放被分成了兩次才看完,卻不影響我對此片深刻的印象,我對張國榮飾演的程蝶衣深深著迷,感同於他的心痛,不捨他的殞落。在2003年愚人節開了世人大玩笑的張國榮,於我而言是上個世代的巨星,我在那一刻才真正認識他的美。並且,因而入戲的認為鞏俐飾演的菊仙,真是「臭婊子」。

二十一
我開始極度迷戀張國榮,這讓我在2013年金馬影展重映《霸王別姬》時,再度於大銀幕一窺此片風采。時隔三年,21歲的我,不在僅沉醉於張國榮,注意到了出身妓院的菊仙,如何在中國舊社會與新社會交替之中,敢愛敢恨的介於兩個戲子之間。我同情起菊仙的境遇,卻仍討厭這個女人。......我想,那時的我以為,介入他人感情的第三人,總是可憎的。程蝶衣的不幸,是時代所致,亦是這個婊子所致。
二十五
再一次觀看,是研究所一門課的指定影片,我讀了原著小說後,再看了一次本片。這次,只有小小的螢幕,我試圖為自己對此片的著迷,理出頭緒。
《霸王別姬》原著作家李碧華自己作為改編電影的編劇,在整個故事梗概上並無太大異動,些許的微調也都成功輔助了電影發揮影像敘事的力道。而令我訝異的是,那些文字裡角色情緒的小細小節,竟是那麼清晰可見的召喚回我當年的觀影情緒,我的迷戀與憐惜、同情與可憎。從小說的文字過渡到電影影像,我驚見婊子不再只是那可憎的婊子,25歲的我,可以理解菊仙了。一個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情的人。
我認為,陳凱歌之所以成功(而她之後再也沒有這種成功)並不再於本片多麼完整、磅礡的復原了時代與歷史,而是他更重於呈現角色情感。每一回波動的情緒不斷被放大,實是極度煽動人心的。逐格再看,陳凱歌給角色正面臉部的特寫鏡頭尤其的多。與此同時,這些鏡頭的背景,多半乾淨無太多雜訊,更適時的加入具有暗示性物件於前景,如薄紗、金魚、火、菸/煙…….等。陳凱歌的鏡頭搧風點火要觀眾入戲,卻又隔著紗叫我們來看戲,或提醒我們與「戲」保持距離。
這部片一再予我如此多情感的連結與觸動,正是那一個個人物特寫定鏡。他們對視、凝望著前方含恨著或流淚著,都更像是在看著鏡頭外面觀看著的觀眾,討取憐惜或同情。我忽然強烈的感受到,本該被觀眾觀看、凝視的戲子(舞台上的表演者)與婊子(女性身體),在那些時刻已穿過鏡頭反過來凝視觀眾。當此反凝視被啟動時,作為觀眾,便得採取一個對自己最安全的姿態來回應它。
我凝視程蝶衣,選擇了迷戀的位置;凝視菊仙,則是從視而不見、不願回應到坐立難安。前者並不是一種偷窺式的愉悅感,而是被導演掌控著一再近距離的凝視角色悲痛後,不忍的想要給予安慰。尤其,蝶衣(小豆子)這個角色自童年、少年到成年,無一不展示給觀眾極其無辜的眼神,並在整部片子被堆疊起來。後者,是隨著我的成長變化的心境,她在故里裡可以是個拿來怪罪的標的,但她也是那個中國人不願面對的真實樣貌。
在幾次觀看經驗裡頭,蝶衣和菊仙兩個角色總是吸引我目光的焦點所在。對照著小說,二者彷若隱喻著中國在民初以降的社會變動中,的兩種人心,正如小說開場白早的點題:
「婊子無情, 戲子無義。 婊子合該在牀上有情, 戲子,只能在台上有義。」 (李碧華,1985)
諷刺的是,在這個故事裡作為戲子的蝶衣與作為婊子的菊仙,似乎都是有情有義。偏偏蝶衣到頭來早已人戲不分,菊仙則自己贖了自己離開妓院,他們卻脫不去這身標籤,輸給自己那份有情有義。這是一齣,我想不管我到了幾歲,亦参不透的人心。
在這些鏡頭之下,觀眾被逼著重新理解成為戲子與婊子的全中國人。在整部片的最後一波高潮,文革時期的批鬥大會中,小樓與蝶衣互相揭發在那個現實裡倒都成了戲,批鬥場面成了舞台,小樓只要肯吐出一句「劃清界線」他就過關。菊仙,過往的妓女身分被批鬥仍不至絕望,那句「劃清界線」卻讓她選擇「下戲」。批鬥大會結束,人去樓空,菊仙與蝶衣對望,蝶衣在這戲裡鬥贏了卻也笑不出來,而到頭來人戲不分的不僅是蝶衣,菊仙亦是。
歷經那些年的階級鬥爭,相互批鬥,中國人又怎麼能分清楚是人是戲了呢?
所謂「婊子無情,戲子無義。」應是作者給讀者/觀眾的提醒罷了?
二十六
2018年年底,《霸王別姬》二十五周年數位修復版在台灣院線上映,已經看此片無數次的我,這回並沒有多激動地想再看一遍。不過,故事都說到這了,我肯定還是去看了。
這一回,第四遍,因為工作,我帶了兩個來自花蓮的17歲妹妹一起看了。時間與場次都那麼的剛好,好不容易北上,說好讓少女可以自己選想看的片子,但我卻早已下定主意說服她們就看這部!
其中一個妹妹看完感到生氣,她說她不喜歡這個片子,因為這一切太殘酷了,她沒有辦法接受這個結局。她嚷著:「他們不可以這樣....」,那個「他們」是誰呢?我沒有追問,只是緩緩地回應她,「但那可能都是真的」。另一個女孩當下沒有多說,半年後我鼓勵她去參加一個電影營隊,報名表要填最喜歡的電影,她填上了《霸王別姬》。後來,又有其他人告訴我,女孩想看更多像《霸王別姬》這樣那麼好看的片子。我覺得,她們兩都像我,18歲的我、21歲的我。
這一件讓我十分得意的事情。
.
也快十年了,距離我第一次看這部作品。我這一代人,與中國的關係、對他們的態度似乎也正在這十年間,彷若燒一鍋熱水,此時此刻還正沸騰著處理彼此的糾結。
而最近,因為這場波及全世界的疫情,我又想到了《霸王別姬》裡的隱喻。我一直對中國人極度好奇(這個前提當然是我沒把自己當中國人或甚麼中華兒女),這部片彷彿戳開了我對那一方的神祕想像。我經常,近乎窺奇的觀看中國,以及這個國家的人,那份窺奇,其實讓我無從真正理解他們。
然而,我越來越對那感到好奇,我想要明白我與它的關係,我認為我有必要搞清楚這份關係。和你不是同一國,這在我這一代,是很理所當然的。但我可以感受到,就像是我在不同年齡看《霸王別姬》,對菊仙的態度慢慢的轉換,我看待中國人的態度也如此。我起初討厭、我開始同情,最後,我希望我可以理解--我希望相信,理解可以讓彼此理性溝通。
可是,其實我理解不了。就像陳凱歌再也拍不出個像《霸王別姬》這樣經典的作品並且墮落、就像我連自己父母深信不疑的信仰價值,都理解不了一樣。電影有個能量,但電影只能是個推力,不是解方。而我只能持續困惑,他們在他們的世界裡,過著他覺得的太平盛世,我究竟要努力撼動他好,還是繼續視而不見?
不知道,中國人看了《霸王別姬》,都想了些甚麼,理解了些甚麼。不知道,如果在那個世界裡的人從未知道真相,他要怎麼知道,原來自由與不自由的差異何在。看著他們又安逸了起來,我卻心生不滿,矛盾了起來。難道,我希望他們遭受更大的災難?我希望他們受到教訓?我希望他們再也不要爬起來?
正當我以為,以為自己是充滿善意的。我對自己的這個念頭,害怕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