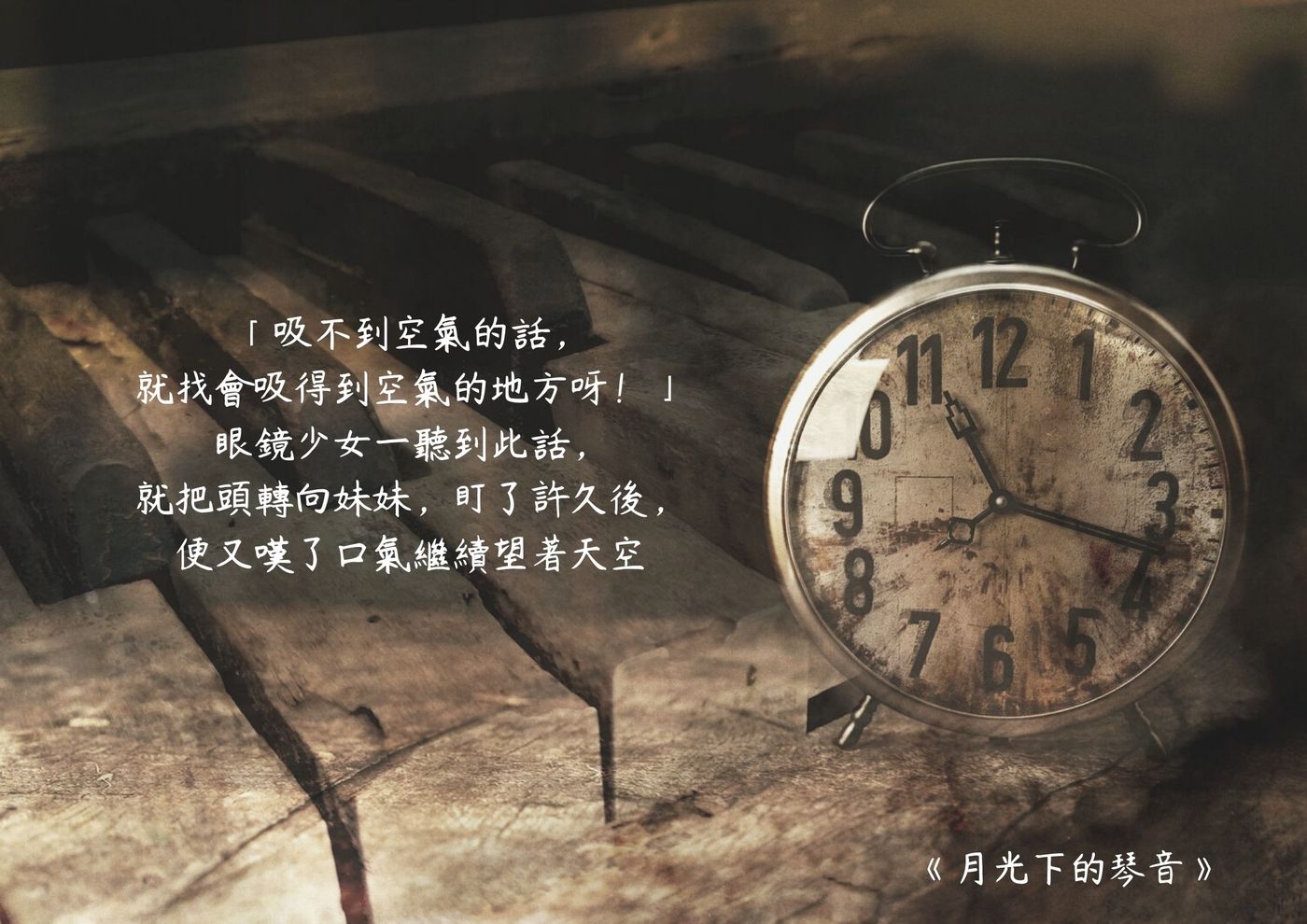圖書館的燈已經關了一半,留守苦讀到最後的幾個學生步出大門,周圍一個人也沒有。
秋天的夜空大概特別黑,沒有月沒有星沒有雲,整塊黑幕把一切封住。路上的街燈一盞又一盞,在行人路上照出一個一個規律的圓,樹一直在搖。
廣播在十一點半響起的時候,情恩仍然埋頭在一大堆醫學教科書上,那時她聽到熟悉的字句,知道時間又夠了,心中一陣矛盾。她出來後,先是吸了一大口空氣,這種空氣對她來說有特別的療效,能把她冰封住然後重新喚醒過來。她戴上耳機,像平時一樣,把兩手伸進長褸的衣袋裏,目無表情的走回家。
她走得特別慢,在折騰了一整天之後疲憊不堪,完全是合情合理,但她的潛意識清楚知道,自己在逃避。
逃避甚麼?聽說在某些野外的冬天是極為無情的,如果找不到合適的地方過夜,正常人根本沒辦法撐過去。情恩在不知甚麼電視節目中聽過這些東西,自己卻喜歡反其道而行──她也知道自己是一個奇怪得可怕的人──她正在逃避一種溫暖。籠統來說,是家的溫暖;仔細來說,是父親的溫暖、母親的溫暖、樓下保安叔叔的溫暖,各種各樣人的溫暖。
既然周圍一切都那麼冷漠,為何這些人要給她特別多的暖意,以致於她喘不過氣來呢?她討厭──不,她怎能討厭?那麼就說是不太喜歡吧──父母親對她的呵護關懷。每晚回家他們都會問她生活上各種事情過得如何,就連午餐吃了甚麼有時也會隨口問一句。她不知該如何忍受這些好意,它們也許是平常父母平常份量的熱情,最多只是微溫,但為何沒有人察覺到,它們長期像火花一樣灑在冰冷的情恩身上,是足夠把她炙傷的?
不知不覺她已走了十五分鐘左右,腦海中還殘存著剛才大惑不解的功課上的問題。每次她退後一步看自己的經歷,總是覺得它庸俗得可笑。自己成績好,親人對她的期望自然大,最後考進了醫科,現在每天卻是混混沌沌的過。就好像那些連續劇裏的小兒子一樣,沉醉在不知是音樂還是廚藝的他們,總是被父親逼去從商,然後垂頭喪氣的過著日子;不同的是情恩連那些任性的興趣都沒有。
她記得現在播著的是第六首歌,她的歌單裏都是些激昂富節奏感的音樂。
那些鼓聲和低音結他的迴響總是能暫時調和她的煩惱和寂寞,它們像帶有生命似的,這樣鮮明的發著聲,讓情恩就像是走進了一隊合唱團中間一樣。
事實上,她走進的是一座公園。偶爾她會在這裏兜一圈才回家,反正它就在家的樓下。四周人已經很少了,她看了看錶,快到午夜,人們都回家睡了吧,只有一兩個露宿者躺在那邊,還有一個男人在放狗。
這公園的盡頭就是大馬路,那邊有一塊頗大的草地,如果是春雨天,來到附近會聞到陣陣草香,的確是一個悠閒的好地方。
情恩不知不覺就站在這裏望著那草地,恰巧是聽著自己最愛的那首歌,她身心都興奮起來,頭隨著節拍搖了一兩下,手也擺動起來──她學過跳舞,舞步都忘了,但此時又記起來。
歌繼續播,歌繼續播!萬種麻痺的快感流過她的身體、她的靈魂。她的靈魂是一個空心的洞,聲音打在牆壁上又彈回來,逼出一種粗糙的回音──回音告訴她甚麼?她只知道自己正身處於天堂。肯定是的!回音又說話──她的手已經不停地搖擺著,最後全身都跳起舞來。
她把手袋和大衣拋在一旁,那樣忘形、用力的伸展拉動著手、腳和身體,歌一直在播,她一直在跳,草地是軟的,她脫去了鞋和襪,赤腳踏著各種舞蹈,草地的冰冷和柔和叫她狂喜不已,反正一切都是虛幻的──
一個司機在的士上清醒過來,他朦朧地望向窗外,公園還在那裏,路上一個人都沒有,周圍是熟悉的幽靜。十二點的鬧鐘這時才響起,他抖擻精神,揉了揉眼睛,把咪錶打開之後便揚長而去。(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