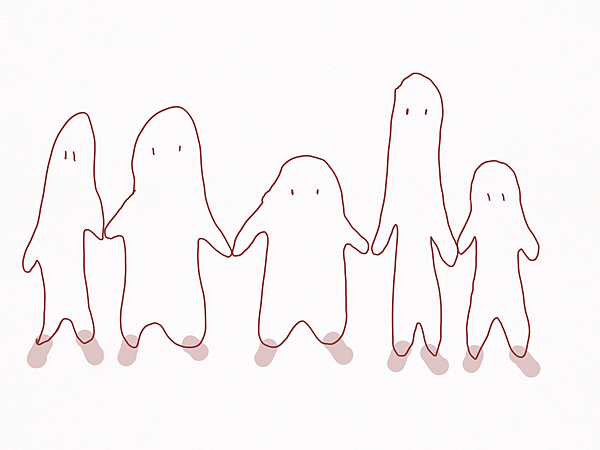文、圖/秀玟
寫在開始之前,關於家屬的痛
進入正題前,我先鋪陳一下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的起承轉合,讓初識專線的讀者們更易理解前因後果,已熟悉專線的讀者可自行跳閱。
輿論渲染下,一般民眾對家屬的第一印象可能是:「要盡照顧責任,讓當事人好好就醫服藥」,並於發生社會事件時,第一時間質疑家屬未盡協助治療(註一)當事人的責任。然而,精神疾病的處遇極其多元、複雜,以現今的治療主軸醫療來說,藥物的療效有其限制,而假使藥物對當事人的確有助於穩定,當事人也需要藥物協助才能好好生活,但忍受副作用的,是當事人。先強調,藥物對於症狀的控制不可或缺,但某些情況,藥物副作用下,減緩症狀的代價可能是功能的減損或喪失,當事人自此被弱化成一個需要時時看顧與防備的「病人」角色。面對疾病作用帶來的巨變,認這個身分、服藥,都不是容易的選擇,家屬難以涉入如此重大的抉擇,更遑論對自己的失序渾然未覺的當事人,連醫療都難以接觸。如以國家強制力促其就醫,先不論強制要件達成困難,家屬也須面對送醫後關係撕裂的風險。又,藥物之外的治療或其他與病痛共存的選擇不多,這些資源可能成本高昂、稀少,又或是設有資格門檻,院外的社區支持力道不足。這些困境,將家屬與當事人卡在難以動彈的兩難裡,將問題歸於「病人未服藥」,是過度簡化的說法。
社會氛圍如此,家屬可能自責「我是否沒有盡到照顧責任」,百般羞恥下,怯於求助。求助時,尋的大都是安頓當事人的方法,由於忙於解決問題及處理情緒,累積巨大耗損,鮮少有力氣思考如何安頓自己,無法回探自己在照顧或陪伴歷程中發生了什麼、感受是什麼、需求是什麼。因此,很需要正在經歷,或經歷過這些歷程的家屬,反思自己的經驗,以家屬的主體經驗提供貼近家屬本人,及整個家庭的支持。
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在一群經驗豐富家屬的密集討論下,冉冉而生。專線致力於陪伴思覺失調、躁鬱、重鬱等精神疾病經驗者的家屬,期望透過共學精神疾病相關知能與多元觀點作為反思素材,並在後續的教育訓練、接線討論中覺察、梳理自己的經驗,從自助走向助人。
素人工作者,生命經驗的碰撞
與專線的初識是在2020年,我以四屆接線志工的身分加入培訓。
身為診斷暫且為躁鬱症的精神疾病經驗者手足,我並不是大眾想像中典型的「照顧者」。專線志工報名表單上,我寫著:「我不太喜歡使用『照顧』這個詞彙,有上對下的關係感。」、「與其說是單方面照顧,不如說是從互相陪伴的過程中,讓彼此都獲得慰藉,及自我實現,是一個共生的關係。」、「想強調精神困擾者潛在的能量,精神困擾者並不是累贅,也不會讓陪伴者被拖下水。這些互相陪伴成長的歷程雖痛苦居多,但都是能放在心上許久寶貴的回憶。陪伴精神困擾者也能為自己賦能,在同理心方面獲得飛躍成長,也能成為生涯前進的動力。」——帶著這樣僵固的信念,進入專線後,志工時期及工作前期,我發現自己沒聽懂某些家屬的苦,甚至帶著當時的我渾然未覺的道德優越。
之所以難以將自己歸類為典型照顧者,是因為我的手足有群在失序倡議領域耕耘良久的朋友,而我也經常在他們聚會時到處串門子。已然浸泡在議題裡,在失序同儕的培伴下,我長出了另類的「家屬」(註二)經驗——我一直期許自己成為能夠涵納手足一切的,互敬互愛的「陪伴者」,即使要我移動原有價值觀、付出超出我所能負荷範圍,消耗殆盡也無所謂,也希求所有家屬都是。並且,當時,手足的狀況還在我和手足的同儕可以掌握的範圍內,讓我苦惱的多為與其他家庭成員疾病觀點的磨合,以及家人的經濟控制,與之而來的受苦並非太過難以承受。因此,從我的生命經驗出發,難以理解不願或已無力照顧/陪伴當事人的家屬的「苦」。再者,我出身的法律本科並無細微體察個體以至族群處境的訓練,且我長期接觸相關人權團體所揭示的,鮮少家屬聲音的倡議觀點,這些家屬儼然被我施以「惡」評,不曾去靠近、去理解,遑論承接這些家屬的情緒。
培訓後一年,非心理或社工等助人相關背景,我帶著僅有的三個月接線經驗成為工作者,開始以自身生命經驗,與家屬志工夥伴一起工作。
身為專線工作者,我給自己的期待是,能靈活切換工作者、志工、家屬視角,盡可能在工作上貼合家屬們的需要。然肉身上,由於彼此經驗的不同,挑戰隨之而來。前述的「聽不懂」也在逐夜的反思中,被連根翻起,鬆動原先硬化的信念。
泣訴歇斯底里女兒的母親、無法忍受當事人任性,直呼「想殺了他」的手足等等,這些家屬需要的僅是鬆開道德綁縛的空間,吐露被文化劃歸為暴戾的語言,以呼吸須臾。起初的我,由於「不能對當事人有負面情緒」的超高道德標準作祟,容易衝動地開啟說教模式,或感到不耐而表面同理,在暗地裡評價對方。然在更多來電者心聲的灌溉,以及與志工夥伴的逐次深聊與接線討論下,這些以肉身經驗所傾訴的受苦,其直接且密集的衝擊使我驚覺,必須移動信念——環境不足以盡心照顧或陪伴、適性不合、溝通條件尚未達到等等,種種現實的擠壓下,形狀破碎的家屬們,最需要的是支持與陪伴。誰不想善待他人呢?然而,這份善待,需要許多條件才能發生,譬如穩定的經濟、譬如激烈衝突後能將衝突作為養分的心理韌力、譬如家屬有能量、有意願去看見自己、照顧自己,將心安下。
我開始比較能以新生的,更貼近對方狀態的視角,面對來電者。
除上述我不擅聆聽的類型,不同類型的家屬或陪伴者中(註三),也有貼近,而我可以分享與陪伴的部分。
一年來,無事先預約、無轉接的情況下,有位躁鬱症當事人的陪伴者撥進的,其中約莫九成左右的來電,都是由我接聽。這一年裡,對方總在耗竭時打來尋求支持,所幸我陪伴手足的經驗,我所描述的病痛難題的語言(註四),足以讓他感到被同理,感到安全,把焦點放回自己身上。精神疾病作用下,經歷病痛的不只是當事人,家屬或陪伴者也是。對方所感受到的病痛、因之而生的情緒,與沒接好對方或埋怨對方,因此自責的情緒,幾層情緒堆疊下,漸次磨損來電者。和來電者一起指認情緒、陪伴來電者接納這些情緒,陪他檢視這些情緒帶來內耗的面向、抽離來電者主觀視角盤點現況......論「陪」,可行方式百百種,而有時,僅僅表示自己經歷如何與其類似的歷程、分享自己對這些歷程的反思,並將這些反思與來電者的經驗連結,對來電者而言,可能就已足夠。
與來電者連結的種種
接線時,電話另一頭的來電者除家屬外,可能是無親屬關係的朋友,甚至是鄰居、大樓管理員或軍隊長官,他們帶著各自的困境與接線者連結。有的需要的是資源,有的需要的是支持與陪伴。除了需求明確,短促結束通話的狀況,接起電話的頭十分鐘,你往往料不到對方的需求是什麼——有可能,資源分享到一半,發現對方需要的只是陪伴,以撐出在受挫經驗間呼吸的空間;亦或在能量耗盡,想放手時,獲得一份同理。
也有這樣的狀況:談到最後,接電者無法提供較佳方案、所提供的方案對方暫且無法收下或實行,或實行上可能經歷重重險阻時,時常聽見來電者說,阿,原來最終還是需要由我自己面對、自己解決——「好吧,我再自己想想要怎麼辦」——結束通話的同時,時常意識自己並不是一個全能的,能滿足來電者期待的接線者,學習接受自己與環境目前的侷限,在此基礎上,保留能量,汲取自我成長及倡議的養分。同時,對方也如同被提醒,自己仍須獨自面對系統而感到無力;假若身邊缺少夥伴,電話這頭的支持,便極為重要。
我也常在肯定來電者以撐起喘息空間,或指出對方與當事人相處方式的可能癥結點,推進來電者與當事人的關係間游移——後者必須冒點讓來電者感到被冒犯或被指責,或落入自責迴圈的風險。當對方明確尋求解方,且有空間聽取中性意見的情況下,我會選擇後者。此時,我的功課是,收起「讓對方評價為無效、感到不舒服」的恐懼,直面助人的陰影,嘗試在來電者這邊撒下架起雙方橋梁的種子。期間,有來電者因此豁然開朗,打開學習之窗的時刻;也有可能由於不符期待,不再打來,而我們主動回撥關心時,對方也意興闌珊的狀況。提出所看見的癥結點,用意不在於要求來電者全然接收,促使往我們想要的方向改變,灌輸我們認為「好」的價值,而在於嘗試提出一個,與以往相處模式不同,貼近來電者需求的可能。畢竟我們擷取到的僅是來電者的生活一隅,該怎麼做、可以怎麼做,最終還是握有最多資訊,並承擔結果的來電者才能決定。
在疾病的分水嶺,開鑿家屬與當事人間的雙向通道
精神疾病的定義是亙古不變的辯題,於我而言,也在與手足的相處中不斷辯證新的詮釋可能。於家屬而言,疾病是最為熟悉的語言,同時,也是最不熟悉的語言。就醫、服藥是最可近的管道,認下疾病,未來的治療渠道相對可見,資源也較易取得。但生物醫學模式下的醫療難以承接本質性的受苦(註五)、病痛難題的語言,SOP化的治療程序無法兼顧受苦的複雜性,巫宗教、神祕學等等新的「療遇」(註六)方式應此而生,他們在不同的情況下承接了疾病經驗帶來的受苦,但相對難以科學化的方式確保生理上的「療癒」。我所聆聽到的來電者,各對應光譜的不同位置,不相信精神醫學、相信精神醫學但不全然信任、全然相信精神醫學等等,家屬本身對於疾病的認同也常存在差異。
接線時,腦中常直覺地複製其他家屬的歷程做對照,但這些歷程是絕對的嗎?譬如,以經驗歸納,為控制症狀,穩定服藥是必須,但不服藥,嘗試自然療法,或以宗教靜心降低壓力減少復發機率,一定不可行嗎?又,我的信念全然正確嗎?我所觀察到的,符合客觀和主觀真實嗎?面對疾病作用的複雜性,我總在試圖找尋我、當事人、家屬間價值觀的平衡之處。
對於疾病認同與家屬迥異的當事人,嫁接家屬與當事人疾病觀的節點上,我可能會適時和家屬分享疾病的不同觀點,以讓家屬有機會多一點理解,與當事人連結,較容易找到轉機;但最終較可行的導向,往往仍是就醫、服藥,可能是當事人的痛楚所在,也是家的痛楚所在。如同本文開頭所描述,醫療,在某些情況下難以接觸,而服藥,相對可確保症狀獲得控制,但可能帶來副作用、部分自我的喪失,與角色認同的混亂(註七);不服藥,有時相對符合人性,但面臨的則是未知。選項有限下,打開視野後迎來的,可能是豁然,可能是矛盾與無解的開端。
沒有標準的答案與作法,所謂最佳解往往在相對中變動。目前我能做的,僅僅是持續在複雜中思考。
在暗處捧起火苗,踏過滿地玻璃大聲歌唱
專線一年,看著家屬夥伴們相聚相惜,時常心疼於,由於這些疼痛的經驗,我們才得以相遇,彼此療遇。前面提到的接線經驗僅是冰山一角,將這些經驗匯聚成倡議資源,在結構上營造更能支持家屬的環境,需要持續灌注精力。
我自認是個脆弱的工作者,與離自己生命經驗尤其相近的家屬工作,必定讓觸動或衝擊影響生活——例如,能夠同理對方的無力,所以更需不斷提醒自己,將經驗放下,回到對方的處境尋找轉機;反之,回到生活裡,我也需要花點力氣提醒自己抽離無力,靜觀、思考任何可能。以及,與家屬分享自己的反思時,時常走在實踐反思的歷程裡,可能甚至是在實踐中卡住的狀態,向對方坦承 「這很重要,而我也還做不到,還在練習」、「我知道很難,我們一起練習」,這樣的坦承偶爾將我拉回自我與超我的拉扯間,弄痛自己。但珍貴的是,這些也讓我得以重新反思過去以來的信念,以及我與手足的關係。
至今,我與手足的生活仍然變動,其中,最有感於彼此生命歷程不同所導致的,無法互相理解和接納,偶有張力的時刻。對於疾病經驗者及家屬間的甘苦、愛恨情仇,我仍然想試圖讓雙方看見彼此,理解彼此的可能與不能。在燈泡破裂的幽暗時刻,捧起火苗,陪伴在扎人的玻璃碎屑中捏塑仍模糊不清的關係的形狀,直到燈泡重新被點亮。
註一:這裡的治療,是指以控制症狀為主要目標的修復方式。
註二:之所以加上括號,是為了突顯自身經驗與典型家屬經驗的不同。我自認是一個形狀奇特的家屬。
註三:我無意將家屬或陪伴者粗暴歸類,但為方便說明,我暫且以「類型」描述有相似狀態的來電者。
註四:關於「病痛(illness)難題的語言」的說法源自醫療人類學,可參考《談病說痛》,指因病痛帶來的生活困擾,如當事人或家屬分享疾病帶來的相處難題。其相對為「病程的語言」,指在生物醫學模式下,醫師所使用的語言,多為控制症狀的技術用語,如診斷為何、如何治療等等。
註五:「本質性的受苦」一詞可參考《兩種心靈》,即在生物醫學模式下,醫療難以處理、不能治療的受苦,譬如如何回應家裡因疾病衍生的關係撕裂之苦。
註六:療遇,相對於療癒,在於強調非以「治療」、「痊癒」為目標,透過相遇,陪伴、充盈彼此。
註七:提及這些看見,並非否認精神醫療或服藥的好處。醫療能帶來許多幫助,曾有專線的家屬分享,藥物是救生圈,能幫助你不至於溺水;但上岸,需要藥物外,不同資源與條件的使力。而我想,或有當事人自此就得待在水面上,不上不下——其可能原因之一,藥物的侷限,也需要被談論。有些家屬形容,服藥後的當事人雖然症狀獲得控制,但如同變了一個人,遲鈍、呆滯、寡言,已失去原本的靈魂。有關藥物治療衍生的「失去」,推薦閱讀《背離親緣》第六章、多多益善網路專欄「李昀:遺失名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