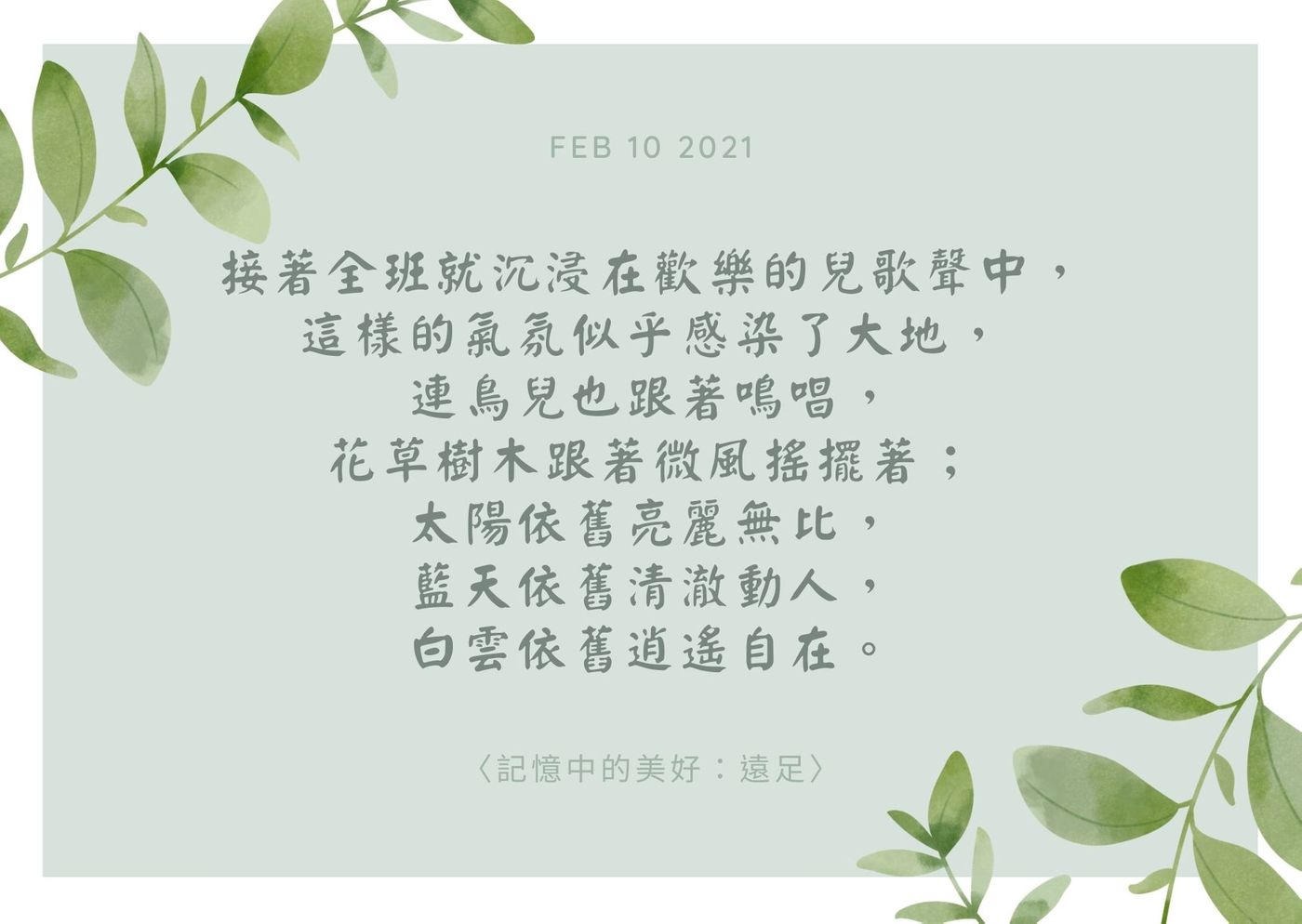昨天在地鐵上,和推車上的小嬰兒擠眉弄眼的玩了一會——起身離開的時候,他媽媽說:「你的朋友要離開了呢!」我笑著和他揮揮手,他的手好小,指頭就像是細長的小花瓣一樣。
這是一件很平凡的事,不知道為什麼——想起來特別愉快。奇妙的是,好像有什麼就在那天夜裡——或者就在這幾天裡,無形的轉化了。那是疲勞一觸即發的星期五——我刻意把自己照顧好——好到有力氣可以下了課還搭車到V&A博物館去參加一個舞蹈活動。
也許是前天的編舞課。
自從觀察到同學也會翹課之後,我開始有計劃的翹課——印度同學跟我說,她這學期打算每一門課可以缺席四次。編舞課是我最想逃跑的一類課,因為時常有很多的空白,而且剛開始我一點也不習慣這種不知道老師會丟出什麼抽象任務的日常,尤其是我不僅不知道要怎麼做,甚至也可能聽不懂老師說的英文。我每天都被迫要跟同學互動和討論——用我枯竭的英文詞彙,這令我相當難受。
「我現在不想編舞,只想跳舞,為什麼現在要一直逼我編舞。」上課時,被迫要想動作的時候,我總是想發牢騷。
這裡二年級的編舞課,分成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A老師固定的每週授課,一堂課三小時,另一個部分則以工作坊的方式,每週一小時半,大約三週左右會更換一個老師。
這星期剛換了新老師,好歹是初次見面,所以我就去上課了。老師帶了一些她說她隨意找來的物件:一袋看不出來原本用來做什麼的細竹棍(老師解釋了,但我聽不懂),還有一捆捆發票紙。
第一個任務,她要我們三人一組,一個當「移動者」,另一個是「標記者」,最後是「目擊者」。「移動者」隨意移動身體,「標記者」便用自己的方式用竹棍標記他的路徑,另一個人就只是看著這一切發生。
第二個任務,她要我們自由運用竹棍和發票紙——老師講了很多英文,我沒聽懂,同學想跟我解釋,但我還是不理解——總之我只得開始移動我的身體。
大概滾了一些「筷子」之後,很美好的事情開始發生,大概是從我和我的同學用竹棍開始玩起雙人舞,在地板上甩來甩去開始。
跳舞的時候,多數時間我們不說話,只會用身體感覺當下的默契——這大概是舞蹈訓練的一部分。我們在無聲的狀態下對話:「我可以這麼做嗎?」「你可以這麼做嗎?」「我們可以一起這麼做嗎?」不知道怎麼的,其中一個同學開始成了雕像,我和另外一個開始在她身上纏滿了發票紙,穿插著這像是鼓棒的大筷子——她看起來就像某個漂亮的異教女神。我們一邊玩,一邊憋笑——其實我和同學們根本就不熟——進展到這樣,真是某種神奇的力量。
我開始撕碎發票紙——我愛撕紙,在當代館的時候我就喜歡那麼做。撕碎的紙花從天空簌然而下,我看見同學笑了。其實我是在前幾天看韓劇《精神病院也有清晨》時學到這招的——而我一直想這麼做。
也許從那天開始,我心裡和同學的那一道牆,開始消逝了吧?
那天在V&A,有場十分鐘的簡單表演——但舞者一從人群中走到舞台上的時候,我差點又要哭了出來。那時我心裡又再次出現那個好喜歡跳舞的聲音。
過往人生猶豫的東西很多,質疑的東西很多——該有多大的驚喜,喜歡跳舞是我人生最確定的一件事——而且她時常在這麼說。
那是English National Balletu演出的春之祭選段。
2024/11/25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