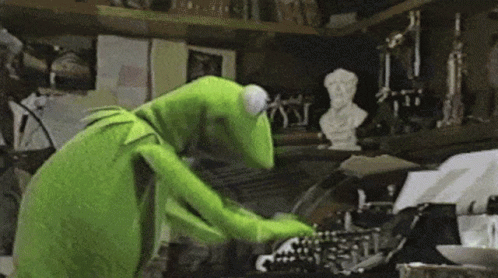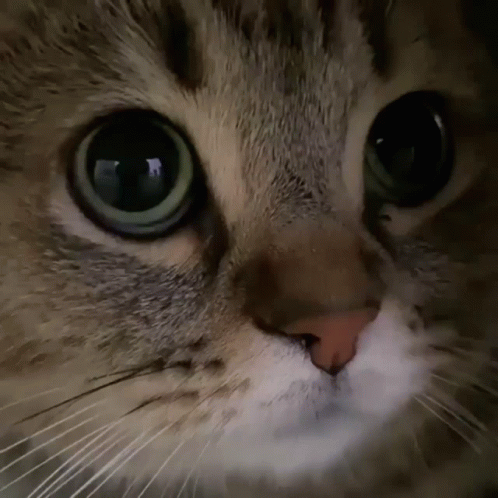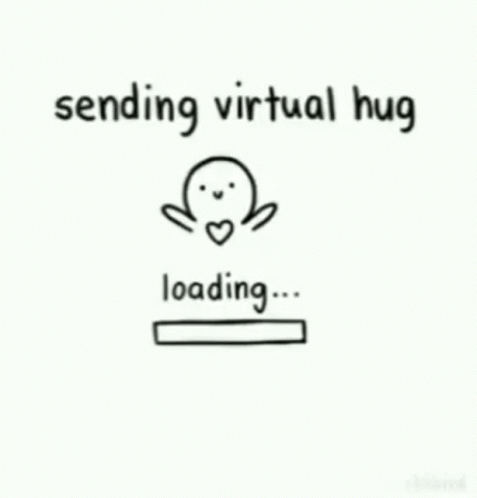宇耿張開眼睛,發現自己又坐回熟悉的辦公室,那個他每次午休起來都會先忘記「我是誰我在哪裡?」恍惚思考「我是誰我在哪裡」的地方。
宇耿的臉黏在書頁上,泛黃的頁巴著他的臉,不甘願地抓拉,掉回辦公桌面。
書是黃崇凱的《壞掉的人》,宇耿在二手市集買的,某年的牯嶺街書香創意市集。書本扉頁有一個寫給明珠的句子:壞掉的時候有很多,所以要記得那些好的時候。旁邊紀錄的時間是2012的某天。這本書的出版日期也是2012年,應該是書甫出版,就買來送給明珠了吧。
不知道明珠和這個送他書的人是什麼關係?他們兩個現在還有聯絡嗎?
買二手書窺見這些使用痕跡和對話紀錄,總是讓人忍不住有些想法和疑問泡泡。
我曾經有一個很酷的朋友。
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想法突然打進宇耿腦海。
明明剛剛還在公園露營,現在又回到辦公室;明明剛剛不到20歲,現在又來到29歲;明明已經沒有聯絡好久好久,想起人事物卻還是歷歷在目記憶猶新。
林宇耿整個人頹喪起來,想起今日的KPI、不想完成今日的KPI,他抬起額頭輕輕在辦公桌上敲,像敲木魚期許給自己某種功德迴向。
保一、小柔和阿尼現在在幹嘛呢?
印象中保一回到家鄉墨西哥,做科技相關的工作,小柔在做補教老師,從大學就在做,阿尼也在科技業,但沒事喜歡把妹還有玩樂團,樂團演出做得有聲有色。
但這些都是好久沒看到的人了,一起說過的話做過的事,想起來都跟眼前這本舊書一樣,有些泛黃褪色,甚至有些被水漫漶,稍微爛掉褶皺的跡象。
為什麼會想做不感興趣的事?
宇耿東想西想,想起之前自己聽過一個講工作和職業倦怠的電台,把職業倦怠分成幾種類型,其中還有一種叫做「無聊型」,講者探討這個分類的時候聊到這塊,分析「為什麼人會想做自己不感興趣的事」:
有可能是因為→有自己的興趣,但經過思考,覺得自己的興趣沒有穩定發展機會
也有可能是因為→沒辦法承認自己已經改變了
又或者是因為→太過於相信持續要在一條路上耕耘才會有收穫與成功
要怎麼了解自己是不是正在做著不感興趣的事?電台講者說,要問問自己你對產業還保有好奇心嗎?會想了解新知嗎?
如果你對產業沒有好奇心、失去興趣,你待在裡面的期間,就變成在消耗跟忍受。
宇耿邊想著這些職涯倦怠的事,一邊手也沒有閒下來,開始做起擱置了一段時間的月報表。
不管怎樣,重點是「我們是會變的。」
人是因為你所看的東西、認識的人改變的
那句電台裡講的話,像是相傳刻在德爾斐的阿波羅神廟的三句箴言之一know thyself一樣,銘刻在宇耿的腦門。
宇耿思及此,分心去Google了「know thyself」,卻看到一篇講「認識自己很危險」的文章:
「歷史終結錯覺」(The End of History Illusion)。我們都認為自己現在已經大事已定,我們在接下來的五年、十年、二十年都會一樣,但是心理學家發現,這完全是錯覺,在不遠的未來我們的喜好和價值可能會跟現在非常不一樣。
如果以為自己是毛毛蟲,像這樣追尋自我,就沒辦法在某天變成蝴蝶;毛毛蟲會變、人也會變,這是一種演化,也是一種必然吧。
「認識自己→像橡皮筋一樣伸縮自如地認識自己」
宇梗拿起藍色原子筆,在筆記本上寫了這樣一句話。
不曉得明天午休會去到哪裡,也許還是在辦公室裡。
我從哪裡來?我是誰?我要去哪裡?
這些真是奢侈的問題,真是如傑作般的問題。
明明薪水沒多少,卻依然能花著時間漫無目的想著這些的我,也許意外地自由吧。
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