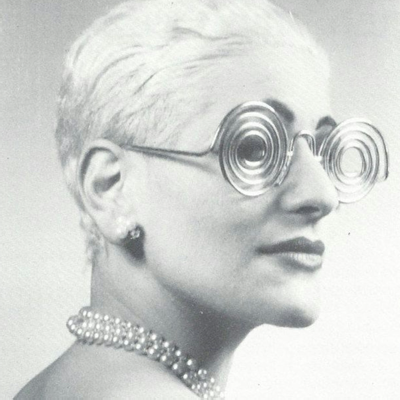談一下,我多年來致力研究日本國家級美術館系統性治理,並撰寫《文化中介之於文化菱形》一書的原因。
日本擁有6+1座國家級美術館,分別是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MOMAT)、京都國立近代美術館、大阪國立國際美術館、國立西洋美術館、國立新美術館、國立電影資料館,以及附屬於MOMAT的國立工藝館(原位於東京,後遷至石川縣金澤市)。其中,位於東京港區六本木的國立新美術館於2007年1月21日開館,為日本第五座國立美術館,也是首座無常設典藏的美術館。其主要功能是為美術團體(如各大畫會、公募團體)提供展覽空間,舉辦定期展覽與企劃展,成為藝術發表與流通的重要平臺,而非肩負藝術史建構的角色。自開館以來,許多以畫會為核心的展覽,如二科會、獨立美術協會、光風會等,已由原先的MOMAT或東京都美術館或文部科學省的展覽空間移轉至國立新美術館集中舉辦。
相較之下,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自1952年成立以來,持續擔任日本官方近現代藝術史建構的核心機構。MOMAT的收藏策略以系統性收藏畫會與美術運動為主,重點不在個別藝術家,而是通過代表作品反映藝術風格與思想的演變,描繪日本近現代藝術發展的整體脈絡。該館特別重視明治至大正時期的白馬會(推動洋畫寫實主義,由黑田清輝創立)、日本美術院(由岡倉天心、橫山大觀創設,重建東洋畫傳統)、太平洋畫會(以寫實與風景畫為主,具廣泛社會影響),以及昭和至戰後的前衛畫會,例如二科會(提倡個人表現、前衛精神,反對保守主義)、獨立美術協會(強調藝術家自由與反體制立場)、自由美術家協會和具體美術協會(戰後推動抽象、行動藝術與國際對話_等。MOMAT的收藏原則明確,首先是館所定位作為國家級近現代美術館,肩負保存、展示與書寫日本藝術史的重任;其次在收藏策略上,強調系統性、代表性、歷史性與風格轉折性,特別重視那些在技法、媒材或觀念上具突破意義的作品。MOMAT的收藏不僅為展覽資源,也成為藝術史研究的重要基礎。與此同時,國立新美術館則專注於為當代藝術家與團體提供發表平臺,兩館形成明確分工,分別肩負藝術史建構與藝術生態支持的雙重任務。
回到石川欽一郎未被MOMAT收藏,可歸因於三個結構性的因素。首先,他並未參與當時日本主要畫會,與重要藝術運動的連結相對薄弱。由於MOMAT的收藏策略是圍繞畫會與集體運動,藉此構築日本近現代藝術史的主幹,石川缺乏這種制度性的連結,自然難以納入其收藏範疇。
其次,石川的創作風格偏向保守寫實,雖具一定技術水平,卻缺乏在技法、媒材或觀念上的突破性與轉折性。這使得他的作品難以成為藝術風格演進中的關鍵節點。因此,他的作品多被收藏於地方性美術館,如福島縣立美術館與靜岡縣立美術館,而非納入國家層級的藝術史典藏。
最後,石川在美術史上的定位更接近藝術教育推廣者,其主要貢獻在於制度建設與教育實踐,尤其是在臺灣。他並未在日本本土藝術史的創作主體中扮演關鍵角色,無法進入藝術史主流敘事的核心。在日本藝術界的價值結構中,他的歷史地位遠不及岡倉天心、橫山大觀等被視為藝術發展關鍵推手的人物。
此現象說明了藝術教育的影響力並不等同於藝術史的核心地位。國家級美術館的收藏標準並非單純以影響力大小決定,而是根據藝術家在藝術史中的定位、創新性以及與藝術運動的關聯來判斷。石川欽一郎雖然對東亞美術教育,尤其是臺灣美術教育影響深遠,卻未能納入MOMAT的收藏體系,這正體現出MOMAT收藏邏輯的系統性與嚴謹性。
與此同時,日本已建立以MOMAT為核心、定位明確的國家級美術館體系,形成系統性收藏與清晰分工;反觀臺灣,美術館收藏仍面臨體系模糊、定位重疊的挑戰,缺乏完整的系統脈絡,易陷入「人情收件」與「拼圖式建構」的困境,且對畫會與藝術運動的重視不足,無法完整敘述藝術發展歷程。若缺乏國家級美術館系統性的典藏與支撐,臺灣難以建立具歷史責任感且具說服力的藝術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