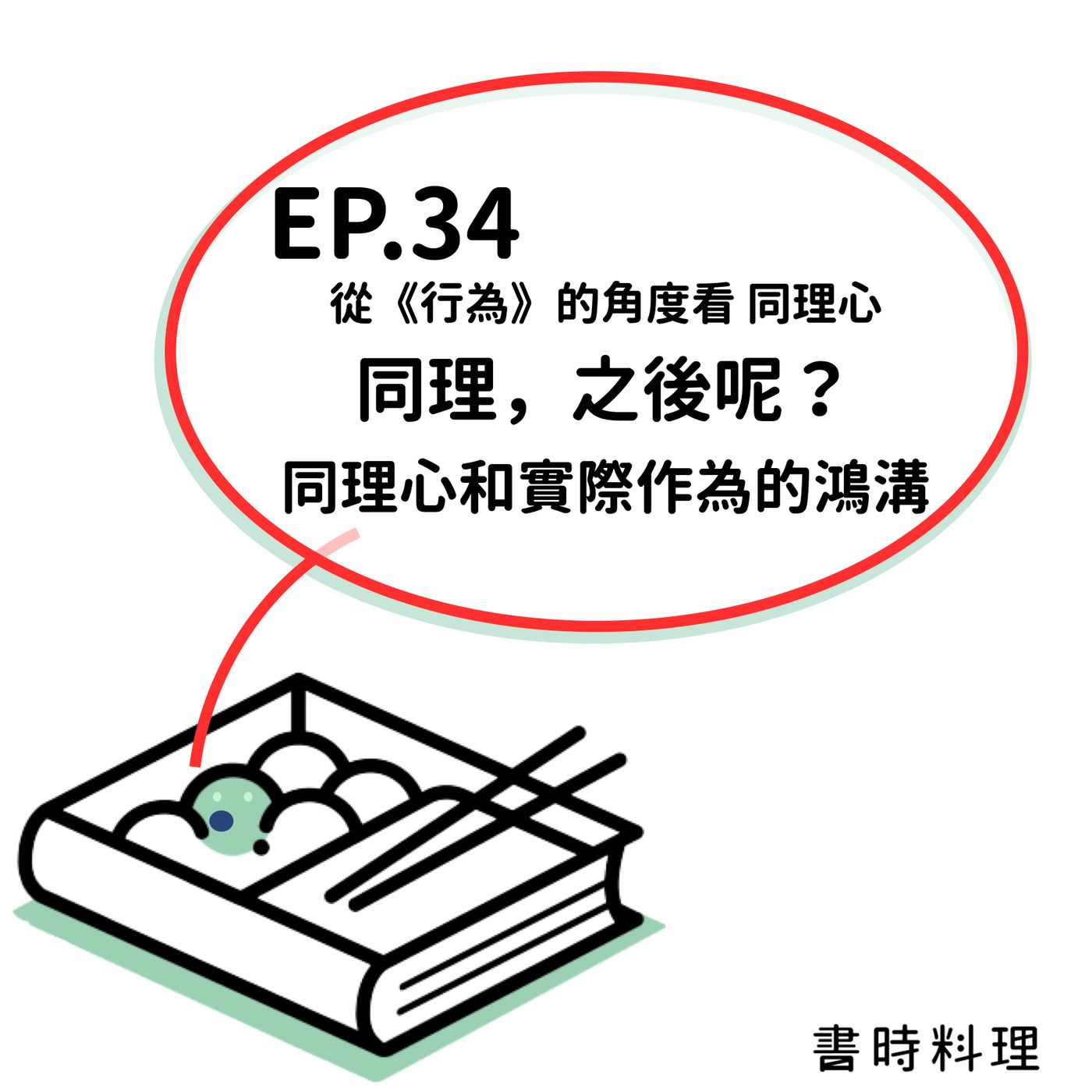前一篇的討論停在強者之間的對決。這個社會可說是註定由強者主導,而弱者之所以不會被過度傷害,是因為強者認為保障弱者對自己有利,這種有利可能是工具性的(讓社會安定),也可能是目的性的(是強者的英雄責任或整體社群的卓越)。
那強者之間要如何打鬥,又會打出一個什麼樣的格局?在這篇中,我們會從同性婚姻的頂上決戰看起。
同樂會
我之前提過,在台灣的同性婚姻立法論爭過程中,反同派的各種言論被挺同派利用到極限,也讓挺同派在相對不利的民意基礎上慢慢站穩腳步。不過我們先放下台灣的狀況,看看國外的同性婚姻立法。
從歐洲到美國各州,同婚立法爭議幾乎無一例外都是舊強者與新強者的頂上決戰。廣大民意當然很重要,也往往是最後立法通過的重要原因,但是整個宣傳戰(文宣)與動員活動(組織),無疑都是精英的一場大秀。
同性婚姻或許真的是這些強者很在意的議題,但我認為更值得在意的,是這爭議過程本質上就是經濟實力「測試」或「鬥爭」。因為技術改良或商業模式演化所誕生的新強者,會從經濟戰場(市場)跨入其他界別,嘗試佔有更多陣地,而同婚立法之類的爭議主題,就是測試他們「身體裡的那頭怪獸」長到多大的不錯方法。
請想像這個基本格局:年輕一輩的創新事業體主導者從舊強者身上取得大量的資金,讓其事業體不斷的擴張,也轉而讓舊強者獲得分潤,雙方合作愉快;但轉過身來,兩造又會各自把錢丟進挺同婚與反同婚的宣傳與動員戰中。
這種對決可以是「測試」,也可能是真實的「鬥爭」。當小屁孩發現老頭子的實力已不夠強,而自己體內的怪獸「長得夠大了」,就會展開更廣泛的實質擴權行動。當然,真正還有底力的舊強者不會被消滅,他們會為了生存而悄悄的與新強者合作,或找到停損點離開某個領域。
這種過程隨時都在發生,因此以意識形態劃分來看待資金流動的人,都會陷入一種脫離現實的宗教式幻境。講得太玄囉?就以大家看得懂的本土語言來說明。
在許多台灣人(特別是窮人、弱者,或意識形態宣傳者)的眼中,企業、媒體,或資金都有統獨之別。某某人是紅色資本家,那位仁兄是台獨企業主,經濟市場會依照特定的意識形態二元對立模式劃分運作,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
但錢就是錢,某甲可能拿他的錢去搞台獨,也會拿錢去買可以賺更多錢的東西,像是中國企業。所以贊助台獨的錢,可能是繞一圈進來的「中資」。那是一種看起來像中資的台資的中資的台資。
這概念你們可能會懂,也可能越看越不懂,但不要緊,你只要記得,錢本身是中性的,要說錢有某種意識形態,就有點古怪。有意識形態的永遠是人,一但人搞不清楚自己的錢轉幾手後跑到哪邊去了,你就不能說那意識形態會跟著走。
當持有明確意識形態的強者想要用錢來實踐他的政治主張,那你或許可以說他的錢是台獨建國基金或紅色資本。但在大多數的狀況下,意識形態的相關支出會是末流,因為意識形態很可能造成經營上缺乏效率。台獨建國基金總是很容易被愛呆灣的人隨便花掉,而紅色資本也浪費在沒阿陸要吃的台灣漁貨上。
這種支出比較像是消費活動,或慈善活動,真正的投資(賺錢)活動會是另一檔事。所以一個獨派的創業者,要取得紅色資金支持,並沒有那麼難,對方也不見得會有什麼統戰目的,只要你能真的幫他們賺到錢。
這也不需要刻意低調,因為人類搜集資訊的能力有限,老共也很難管到自己人的錢到底流到哪邊去,是不是用來投資台灣的獨派小企業。說不定那還是外逃資本哩。
即便是強者本人,也不見得知道自己錢或資源到哪邊去,他的錢很可能會被快速包裝成新商品,繞一圈到了沒人搞得清楚的地方。所以你所屬事業單位的運作資金,搞不好也有習近平女兒的資產。某種意義上的資產。
因此賺錢是一回事,賺錢有賺錢的道理,而花錢有另一套道理:透過慈善行動來累積陰徳值,透過消費行為來建構自我認同,或是透過資助意識形態團體來擴張影響力到政治上。他們想證明自己是全面的強者,想在一切的人類行動領域取得優勢;這時候,原本在資本市場可以合作的個體,就可能會發生碰撞。
合理性
那誰會勝出呢?
不見得是因為「有錢」,或是「有人」,我認為會在頂尖對決中勝出的,是行為較具有「合理性」的人。我們在前面才講「道理」,現在就將之轉化為「合理性」這個相對正式的詞。
合理性是近代政治哲學很愛玩的概念,某些自由主義者認為合理性存在跨越文化的共通基礎,其他社群主義者則主張每個社群都會有自成體系的合理性系統,彼此之間可能存在不可溝通的嚴重矛盾。
但這些都是學者的高見,你不用理會那麼難的東西。你只需要知道,在高速公路上逆向開車,有很高的機率會死翹翹;而你早就知道這點,所以你總是和大家開同樣的方向。這就是最基本的合理性,我們就從這種合理性出發。
事實上,人類的確存在一些共通的合理性基礎,這或許和最基本的物理與化學事實有直接關係。人不太可能否定自己需要吃飯、喝水、呼吸的事實。好好好,我知道有一些罕見的瑜珈或「氣宗」試圖否定這一點,但是他們真的存在嗎?我從自己的宗教相關知識去研判,我認為這種社群真實存在的機率極低,很有可能是魔術式的詐騙。
跳過這些特例,人都會從基本需求開展出最原初的合理性。「渴的時候應該喝水」就是這種合理性,「喝水時要盡量選喝乾淨的水」則算是從前者推演出來的合理性。
你或許會覺得這種造句很白痴,因為正確到根本不需要懷疑,「但是」(我要強調,總是有這種「但是」)總有人會跳過這種最基本的合理性。像是破壞或污染飲用水來源。
人要活就要喝水,喝乾淨的水,但有些人的行為是對抗這種最基本的合理性。講到這,你應該就有很多聯想了:集水區開發與濫墾、污水排放、水庫優養化,圈圈叉叉的一堆。
原本很簡單的事,因為對抗合理性的行動層出不窮,就會變得很複雜。那誰會勝出呢?我認為回歸最基本合理性的遲早會勝出,而強者之中的強者會加速這種驗證的過程。
從農業轉往工業,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會開始犧牲環保,因為這種犧牲還不會對抗到最基本的合理性。但工業化到某種程度後,「環保」就會被抬出來了,不論是以科學的角度,或是以「消費」「文青」的角度,一種回歸基本合理性的力量,會出來「制動」社群。這當然是由強者帶領的。
在這個過程中,會不斷有新合理性的主張者躍上台面,提醒眾人這種合理性之必要性。但這不只是一物剋一物、一種合理性取代另一種,而是合理性彼此結合,建構出越來越龐大的合理性系統。
我們現在知道維護水資源的重要,不代表我們就會放棄發展經濟的道理。就算有些人想回去南陽耕田的舊日子,但真正的強者會知道,你必須在不斷冒出來的合理性原則之中尋求一種新的均衡。
回頭看到頂上對決。在強者之間的較量中,能勝出者,顯然是配備比較多合理性,並且將這些合理性有效組合在一起的人。這會讓你想到什麼?科學家的集團?可惜許多科學家並沒有配備「生活合理性」與「理財合理性」,這讓理工人的競爭力被大幅削弱,甚至稱不上是一個強者集團。
真正掌握合理性的強者,會在大社群中形成次文化社群,擁有一組獨特的合理性知識系統,這種知識系統具有吸收力,就像跑得順的OS系統,能不斷「安裝」新的合理性上去,又能維持一定效能。有沒有感覺和我們本系列最前面談的東西串起來了?
有學者會稱這具有許多這種次文化社群的大社群是「開放社會」、「多元社會」、「有健全公共論域的政治社群」,但看到冷戰之後的宗教對立與中國興起,又讓某些人開始懷疑,或許不見得只有開放和多元的社群才會是真正的強者。
但你可以仔細觀察那些宗教社群或中國,就會發現他們雖然有各種「反」基本合理性的力道在,但如果無法修正,那麼通常會在某個方面走向衰弱與失敗。他們仍無法對抗現有合理性系統的挑戰。
合理性知識系統就是強者(除了錢以外)的無形資產,讓他們在社會中無往不利:至少碰到弱者時會很有利。有些研究甚至指出,在經歷了破壞力十足的反右鬥爭與文化大革命(標準的反合理性力道)後,中國的傳統世家大族也還是能在當前的中國掌權者圈子中佔有一席之地,甚至與清末沒什麼太大差別。這很可能因為他們掌握了合理性的知識。
那為什麼要談合理性的觀念?因為這會成為強者為了壯大自己而抄來學去的東西,所以很可能會成為公共政策的基礎(只要強者都同意某種合理性,那不論是比投票或比拳頭,都應該能成為主導整體社群的主流規則),那我們就可以爽快的轉頭看一些政治實際議題。
人活著該有的
就來看基本工資。現在台灣的基本工資是喬出來的,不是考量到真正生存的合理性,而是一種談判溝通之後的混雜概念:參戰各方都不滿意,但可以接受的版本。所以不論都市鄉村,基本工資都是一致的。當然,台灣多數鄉村地區不太鳥這法律就是。
回歸基本工資的原始理念,應該是讓勞動者可以獲得滿足生活最低限需求的薪資,低於這個,就會是悲慘到難以生存的程度,所謂「不值得活」、「失去做為人的尊嚴」的情境。
有一些政治哲學概念可以拿來比對,像是自由主義者講的「社會基本善」(這「善」指具體好處,不是道德上的善),這是人活著應該有的基本條件。在社群主義者中,也有人主張應提供社群成員追求人生目標的最低限度「外在善」(就是錢可以買到的東西)。
顯然於此有某種合理性,就是「我們應該滿足社群成員的基本生活需求」,讓他們像人一樣活著,然後追求自己的理想。這樣對我們這些沒那麼慘的人來說,也是件好事,因為我們可能因為機運突然淪入社會底層;或是這些人如果吃不飽,就會來亂我們;又或是讓大家過得像人,整體社群才能追求卓越。
你會發現這邊講來講去,都是訴諸一種客觀性,認為這種主張是可以溝通並建立共識的。但正如我在第四篇或其他系列提到的,人與人的溝通,或強者與強者的溝通,往往都是在展示自己立場,進行意見交流而已,大概不會產生什麼共識。
因此我們可以把思考反轉:我們在成長與生活過程中早已接受了某些合理性,這些合理性可能是強者奉行,並讓靠他們生活的我們(弱者)也接受。這種合理性在具體行動層面上,可能得出共通的結果:左派右派都同意要有基本工資,雖然大家給它的理念支持不太一樣。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會是雞生蛋還是蛋生機:到底是先有了結果,才能證明出合理性,還是先有合理性,再生出具體行動?
左派會主張,先證成了合理性,才能有具體行動,行動過程又可以再檢證這合理性是否真的合理。那右派呢?社群主義右派呢?先有了事實結果,再透過描述事實來生出合理性?人都是要吃飯的,然後我們再幫吃飯找個合理性?
這樣好像怪怪的。因此,社群主義右派的最後一個任務,就是自身的道德正當性。也就是說,為什麼做一個右派會是正確的決定?當右派結論已確定是「弱肉強食」,還可能取得道德正當性嗎?
這也是右派做為一種政治可能性之前,要走完的最後一哩路。
系列回顧:
封面圖片:賈克-路易・大衛所繪的法國大革命網球廳宣誓。在法國大革命期間的各種立法議會中,革命派和保王派分坐左右,為後世「左派」、「右派」的濫觴。
編輯:宅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