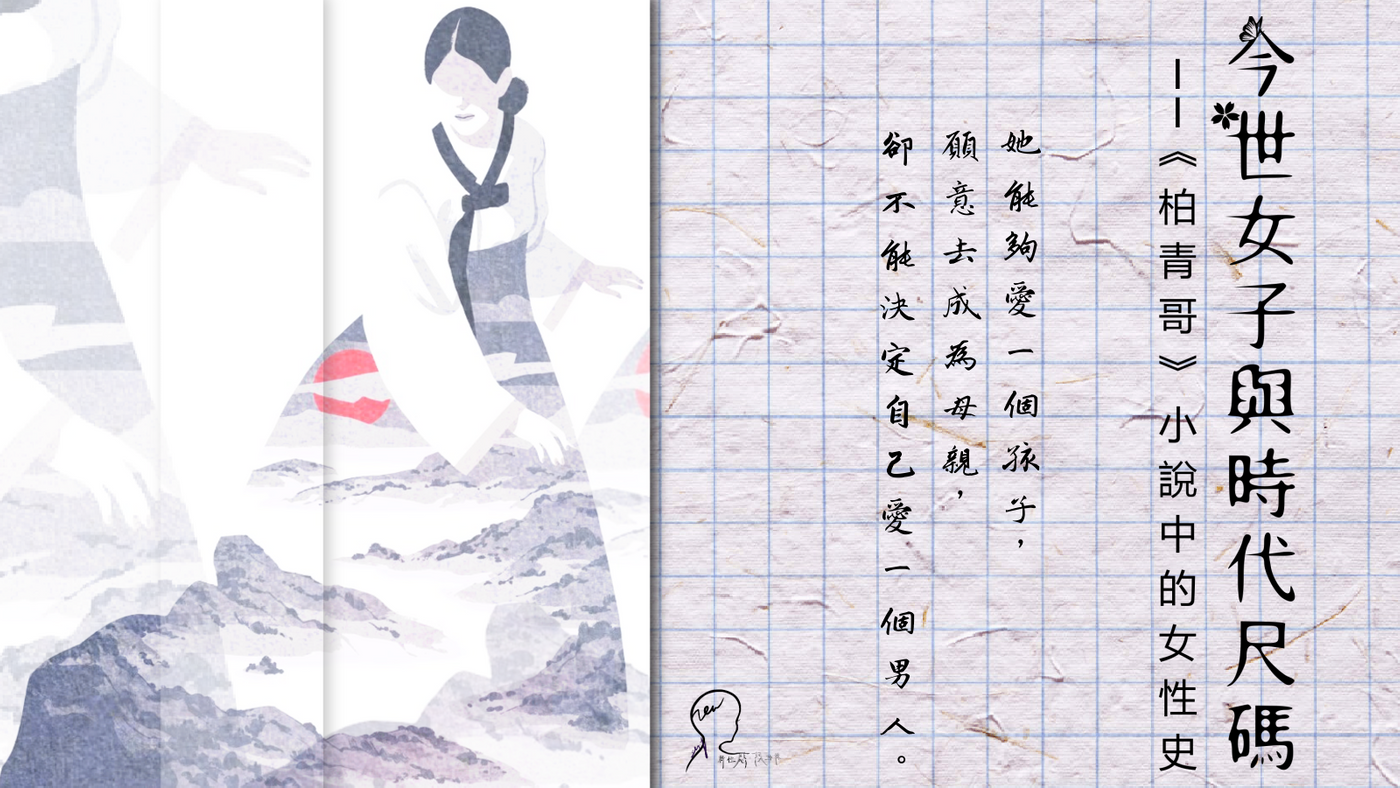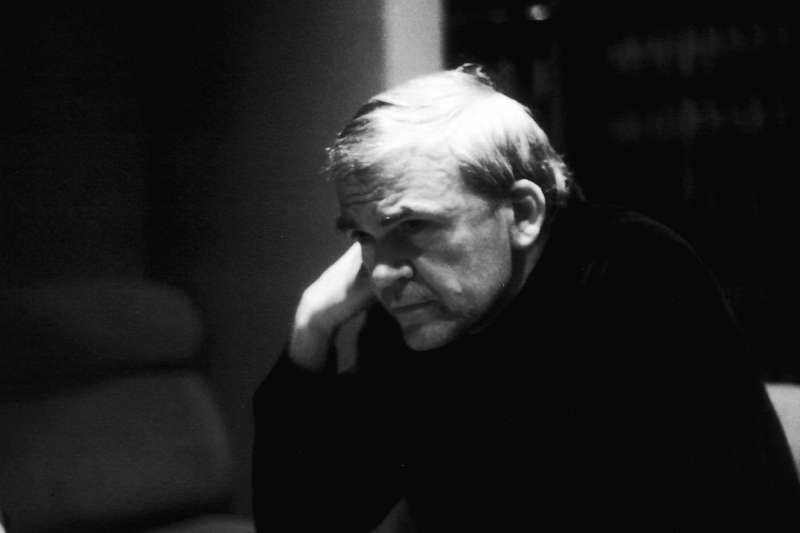我從來都不喜歡讀任何名人傳記,包括作家。總相信從作家的著作中就能了解他的道德觀與價值觀,但不知道為何愛上了《巴黎評論》(The Paris review)的作家訪談,讀得極為著迷,甚至放棄前幾日閱讀的其他文學著作。
《巴黎評論》是由哈羅德·L·休姆斯(Harold L. Humes),彼得·馬西森(Peter Matthiessen)和喬治·普林普頓(George Plimpton)於1953年在巴黎創辦的季度英語文學雜誌,簡中版的作家訪談有七冊,其中有海明威、亨利・米勒、米蘭・昆德拉、納博科夫、馬奎斯⋯⋯等等大作家。
身為讀者,我是幸運的。尤其是在這個年代,不需要理解多種語言,依然能閱讀各國的文學著作,讀著《巴黎評論》的作家訪談,更是覺得身為一個寫作者,即使不以此為職業,也是幸運的,窺視作家們的閱讀與寫作偏好,還有他們對於文學的解讀。從訪談中看到作家們人性的一面、他們的脾性而吸引我⋯⋯從中知道他們對於藝術和創作的看法,理解他們當時為何如此創作?我又意外發現,讀著作家們的訪談除了能增進寫作技巧外也有大量的娛樂性質,他們可會直接對採訪記者耍脾氣的說:「你讀了我的小說還看不出來嗎?」、「我真的要花時間回答這個無聊的問題?」、「這就是庸俗!」⋯⋯想像著採訪者與受訪者間的那種動輒得就的緊張氛圍總讓我有點興奮,若是能拍成實境秀就好了!
我算是個很「認真」閱讀的人。
喜歡一字一字的細讀,不願錯過任何一個細節,讀到最後還以為自己與大作家們很熟悉,算是他們的朋友了。當我讀著《巴黎評論》與納博科夫的對答,能猜想到哪一個句子他會在心裡說:「真庸俗,無趣啊。」;而那個寫出「媚俗」兩字的昆德拉的訪談是眾多作家中相對難閱讀的,個人認為有太多的意識與理念⋯⋯或許可開玩笑說這是大作家的傲慢吧?
說到與大作家交朋友,我曾這麼幻想過,寫一封信給《異鄉人:翻案調查》的作者,但在那篇散文中,沒有透露是要寫給他的,創造出一種自己與大作家間的秘密,也是我這個小作家的浪漫:
你寫給我的那本書,我反覆讀了十四個月卻不真的明白,你說的那個語言,我能理解但那並不是我們的母語。
四百多天來,我試著拆解、分析再轉換,才發現自己把你投射在一個我曾經喜歡的人身上,那人也有著跟你一樣的文化背景。你們自認是異鄉人不只是居住在他鄉或使用別人的語言創作,而是找不到靈魂的歸屬。在你們的文化中「靈魂」似乎很重要。
輕描淡寫的說活著只為等待死亡、俾倪他人對愛情的渴望、憎恨母親對自己的忽視。
我知道,你們都嘗試著用一個當代人能理解的通俗故事來影射大時代之下的悲劇或是訴求你們的政治觀點。可是你忘了,這本書將會發行於世界各國,並非所有的讀者都看得出來那些暗喻。
我又不忍心看別人的註釋,害怕破壞你的美感及我的想像⋯⋯因此我艱難的反覆閱讀這本書,足有十四個月,直到昨天才翻完最後一頁。
這幾天讀著作家的訪談,突然靈機一動,想再來寫幾封信,部分揭露出來。
其一:
當你說著自己的政治立場就是反左派與羅素們,這看似一個任性的玩笑話,但不用說我也知道這是由於你身為俄國帝國時期的貴族又流亡海外,所說出的帶有血腥味的論點。我也想著你們那代人經歷過的革命與戰爭,然後我們搖著旗子高喊「這是正義」,我們是太輕易得到這些,才能如此義正嚴詞的主張。
我們這年代講究一切言行要「政治正確」,在你眼中就是庸俗,過度的追求無瑕疵的「道德感」,其實也是一種不經世事。這是我寫給你的信才能如此說,現在已不能像五十、六十年代能夠自由的主張自己的想法,凡事都會被檢視,這點也是很諷刺的吧?
當你意識到有了一本比自己還有名的著作時,雖然有著無奈,但總比其他人寫了一輩子還沒有代表作好。
其二:
在你之後有許許多多的青年們,聽著你那關於巴黎的敘述去了那座城市,追隨你曾經待過的咖啡館,但如同你說的「創意是存在於基因當中」,要有多少人之中才有一位能擁有此創作基因?
又害那些仿造你的美國遊客被當作笑點寫入各時期的法國電影當中。電影笑他們蠢,是他們最終也不會沾染到你的創作基因,因為將其與巴黎連結在一起。
會不會到了巴黎才發現這是一場詐騙——我的意思是,靈魂空洞的人可能感受不出那座骯髒城市的魅力。
《巴黎評論》問你如何養成獨特的風格?你說,「如果你花幾天的時間回答這個問題,你就會變得非常自知而不能再寫作了」也許我說的太多,寫的太少,但即使你的文字給我很多的啟發,我依然不當你為偶像般的崇拜。
自己玩這樣的遊戲,有種與作家秘密交流的快感,雖然這些信記不出去,也收不到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