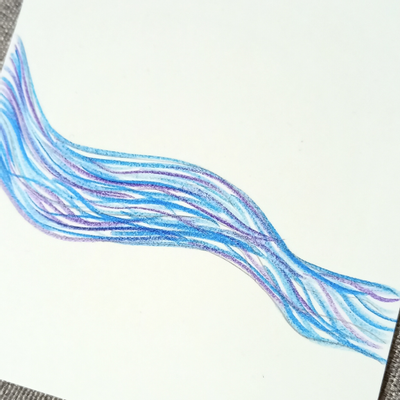貝都因哥哥
剛到沙漠的那天,下午的陽光懶洋洋的,你們正在玩撲克牌,我搞不懂規則不斷發問,你一直在模仿我的why?why?why?
前兩天我們並沒有什麼接觸,你跑去佩特拉了,我被另一個教我在沙漠開四輪傳動吉普車的老男人纏上;再見面的下午你看起來很累,我們去看你裝在岩壁上的燈,手牽手躺在上頭曬太陽。
每天我都覺得我該繼續移動了,但起床一看到陽光跳躍在沙堆上的光影, 就想再多待一天也無妨。
有幾個晚上,你說你以前當五星級大廚的那段日子,你如何十分鐘內變出幾十道不同的沙拉和甜點,說得我飢腸轆轆餓死了;有幾個晚上,你說你如何開把來自各方的女孩,你描述所有細節鉅細靡遺一個接一個,露骨得我都害羞了;有幾個晚上,我們和寥寥幾位旅客打屁聊天,你都講一樣的冷笑話聽都聽膩了,可我照樣配合演出;還有那個晚上,你說了你弟弟過世的事和那個你一生無緣的安曼女孩,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瀟灑狂傲的你露出傷痛的眼睛,我不知道該怎麼回應所以灌了你一大杯伏特加,那是我們每晚一定有的東西,營火菸伏特加星星和那個konafa的低級笑話,難以啟口那就繼續吞下肚吧。
然後我終於離開了,你叫我小心敘利亞小心阿拉伯男人記得回來,所以我回去了,我們在那條漆黑的公路上蛇行,每十秒停下來一次,因為我們太開心了,然後我又離開了,因為我從不停留,那天你看起來還是很累,我記得你在路口的揚手燦笑,你問我什麼時候回去,回去那片我的沙漠,會的會的,總會有一天的,我還記得你欠我的konafa,我的貝都因哥哥。
0會員
18內容數
我到過很多地方,遇見很多人,聽到很多故事。
有些地方聞起來都一樣,有些地方一首歌就能喚起。
有些人我忘記了,有些人從此住在我心裡。
有些故事大同小異,酸甜苦辣五味雜陳,有些故事卻牽動心房最柔軟的那根神經。
其實就是人生罷了,然後生命繼續,we are still on the road。
留言
留言分享你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