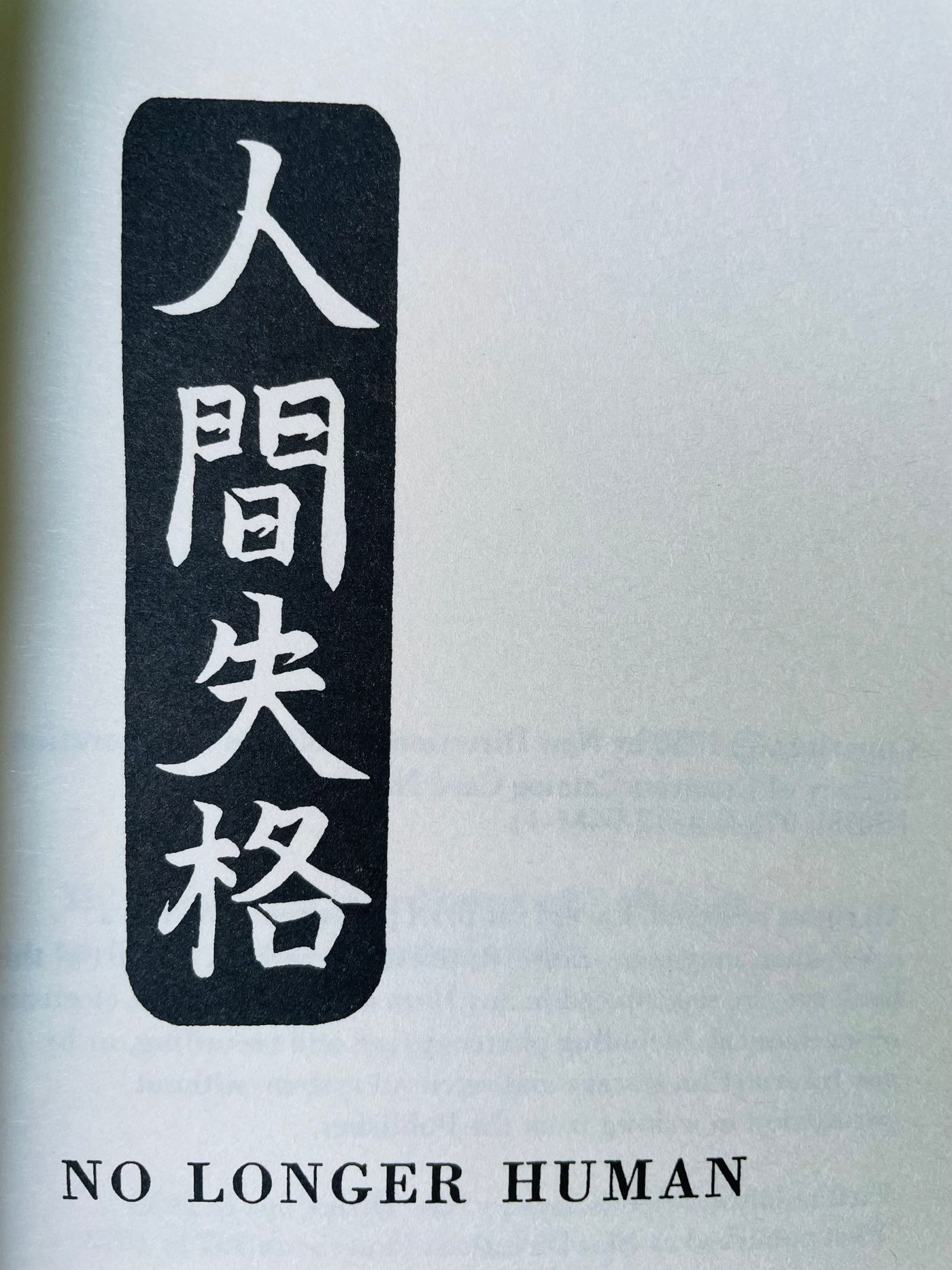◎文/楊照

日本的島嶼地理條件決定了在歷史的發展上,小型散居的聚落成為主體,不容易形成較大的群體。小聚落意味著人與人之間有著緊密的互動關係,必須要有明確的法則來予以規範。日文中將community翻譯為「共同體」,反映了他們社群生活的濃厚「共同性」。一個小聚落就是一個「共同體」,其中的成員被視為是高度同質性的,有著同樣的行為模式,有著共同的感情反應。而管轄行為模式與感情反應的,是「義理」,或「人情義理」。
緊密的「共同體」中,個人沒有太大的自由,也沒有發展異質個性的空間。群體「義理」衍生出種種社會機制彼此加強對於個人的規範。日本有遠比中國發達的地方性傳說、神話,每個村落有自己的神社,有相應的傳說、神話來將成員包納進來,更有相關的民俗儀式反覆確認彼此的人際連結。推薦大家可以看一部漫畫,也曾經在日本改編成電視劇,但漫畫的內容比電視劇更豐富些,那是星野之宣的《宗像教授異考錄》。宗像教授是一個大熱天都要披著大斗篷,高頭大馬光頭的民族學教授,到日本各地去考察傳說與民間宗教,常常走一走不小心掉到一個坑裡,從裡面挖掘出一份日本民俗的重要知識。讀《宗像教授異考錄》最容易具體感受到,一直到今天,即使經歷了長期西化、現代化的洗禮,日本的傳統民間風俗、禮儀的資源與力量,都還持續在發揮社會作用。其中一項作用,也就是維護「義理」,將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放入嚴格的框架中。

在這樣的「共同體」中,必然有集體規範與個體意志的衝突,在日本被視為「理」與「情」之間的緊張。當「情」與「理」不相容時,大部分的人會選擇遵從「理」,按照集體的「義理」行事,但有少數人在更強烈的情感驅使下,對於「情」的堅持超過了「理」,相反地選擇了要徹底忠於自己的心,在嚴密的「義理」籠罩下,他們沒有可以離開「義理」活著的空間,於是只能和感情的對象,那「相對者」攜手「相對死」,如此完成了「心中」──貫徹自己內心的感情願望。
在這樣的文化價值觀中,「心中」背後必然有「情」與「理」的衝突,因而描寫「心中」事件的重點,就是凸顯這份無法解決的衝突。像是在開啟「心中」意識的《曾根崎心中》戲劇中,明白鋪陳了多重的衝突。第一重是德兵衛對繼母的家庭責任;第二重是繼母替他安排答應下來的婚姻約束;第三重是他去借錢產生的還錢承諾;還有第四重,是他認定和九平次之間的朋友關係。德兵衛被重重的「義理」責任綁得動彈不得,所以要實現對はつ(阿初)的感情,最終只能訴諸於極端的「心中」手段。
順道一提,はつ這個名字有特殊象徵意義。以前台北開過好幾家叫做「初」的酒廊,一看招牌就知道是特別招待日本客人的。「初」在日語中的發音是はつ,為什麼要將「遊女」命名為「初」,將有女性陪酒的地方命名為「初」?
那是「初心」、「初衷」的「初」,意思是這家店裡的女性都像《曾根崎心中》劇裡的女主角一樣,身為「遊女」卻一直保持著天真浪漫的「初心」,仍然相信愛情,仍然以清純的態度來對待人,不會變成敷衍客人的老油條。
「理」與「情」的衝突無法解決,人保有感情、忠於那樣一份沒有被世故磨滅的自尊,唯一的方式只剩下「心中」。因而「心中」在此取得了和武士道中切腹自殺一項共同重點,那就是以死明志保護自己的尊嚴。切腹自殺換得尊嚴的方式,是刻意選擇一般人無法忍受、不敢選擇的最痛苦過程;「心中」換得尊嚴的方式則是找到了「相對死」,表示這份感情是真切的,不是一廂情願,不是個人厭世,一般人要自殺不可能找得到另外一個人願意陪著,藉著兩個人的共同行動保證了這樣的死亡有其非常價值──面對「義理」世界,當我喪失在這裡存在的資格時,有另一個人能夠體會、能夠證明我的「情」的真實性。
無論從外在「義理」標準看,我的生命如何不堪,如果得到了顯現自我忠於心、忠於感情的機會,我就能從「相對死」中得到救贖,做到了別人做不到的,也得到了別人得不到的終極愛情。
如此整理「心中」殉情在日本傳統文化中的深厚意涵,我們可以更精確地分辨,一些對於太宰治及其作品的通俗看法,是不是值得我們接受、相信。

最簡單、常見的一種看法,認為太宰治很年輕時,才二十歲,就和一個咖啡店的侍女相約殉情,結果女方死了,太宰治卻活下來,真是無賴、不堪。再下一次殉情事件,又是太宰治活了,女人死了,而且在事件調查中發現,女人身體裡有殘餘的鎮靜劑,合理的推測是太宰治勸女方吃了安眠藥自己卻沒吃,難怪將兩人綁住的衣帶鬆開後,太宰治可以從海中游回來,女人則淹死了。這同樣是無賴、不堪的行為。
然而我們應該將這樣的事件,《人間失格》中描述的,以及太宰治自身親歷的,放入日本傳統「心中」背景中,重新理解、重新詮釋。

小說中寫得很明白,這對男女是在各自都走到人生最不堪的落魄谷底時相遇的。兩人在一起的動機,從來都不是愛情,毋寧比較接近是互相取暖。女人對男人說:「床頭金盡你就不露面了,不需要如此,作為女人,我也可以養你。」男人山窮水盡到這種地步。但女人這邊也沒有好到哪裡。小說中的形容是:她連陪酒時都全身散發著一種落拓、敗破的氣味,讓人家不想靠近她。她當然不可能完全沒有自覺。
而她還賴活著,因為沒有自殺的勇氣,直到這個境遇比她還糟的男人出現。男人糟到讓她提議來養他,男人還不要接受她的供養。於是兩個人在這個「義理」世界中保有尊嚴的最後方式,是彼此可以形成「相對死」,可以不必再忍受生之痛苦,還可以不必孤伶伶的自殺,向世人證明,或更真切的是欺騙世人,自己至少還有愛情,還有可生可死的愛情走到生命盡頭。
終於有了「好死」的理由,不用再「賴活」下去了,所以由女人提議,男人答應了,兩人一起到鐮倉去。
並不是兩個人感情多深,也不是這個世界有什麼巨大的力量阻礙他們的愛情,讓他們到鐮倉去投海。

還應該進一步了解的,是他們選擇的自殺手段在日語中叫做「水死」,關鍵在於這個「水」字,其意義來自淨土宗佛教信念。淨土宗也是從中國傳到日本的,中國的淨土宗雖然信眾不少,但在佛教各宗派中地位不高。因為淨土宗強調念佛誦經的重要性,主張隨時念佛、經常誦經就能在死後前往淨土極樂世界。不像在中國高度發展的其他宗派,如華嚴、天台或禪宗有精妙的教義,有吸引知識階層的理論探究,所以比較是在一般庶民間流傳,後來往往還和道教合流。
傳入日本之後,淨土宗也因教義簡單,重視儀式高過教理,而得到了眾多信徒,並更容易和日本傳統神道並存、甚至結合,成了佛教的一支主流派別。在日本,淨土宗特別突出離去「穢世」的種種法門。「淨土」對應「穢世」,從「穢世」通往「淨土」需要有洗淨清潔的過程。而水,在現實上、在象徵層次上,是最普遍、最有效的洗淨手段。
在多山多河川又靠海的島嶼環境,日本文化本來就和水很親近,淨土宗的信仰隨而更抬高了水的地位與作用。太宰治三次「心中」都是選擇「水死」,讓生命殞滅在河裡,背後的意念是要兩個人綁在一起,彼此攜手,透過水的清潔作用,去到另一個世界,那是洗除了現實汙穢的淨土。
大江健三郎晚期的作品中,有一部小說就叫做《水死》,書名絕對不能翻譯成「淹死」或「溺斃」,必須保留日文中的專門名詞及其背後的強烈信仰意味,我們才能理解大江健三郎如何描寫父親「水死」的過程,來對傳統日本信仰,尤其是天皇信仰進行嚴厲批判。
很長一段時間中,「水死」是日本庶民自殺時的首選。日本幕府時代初期的武士,例如在《平家物語》中所記錄的,也都還是以「水死」方式自殺。不過到後來,武士產生了新的階層意識,發明了切腹的儀式,那是特別彰顯武士地位的一種死法,庶民沒有資格模仿。倒過來,武士也不可以「心中」,因為武士只能有一個絕對的效忠對象,將他的「忠」從主公轉移到任何一個女人身上,對武士來說都是恥辱的行為,不可以有,更不可能張揚。
在日本的「義理」世界中,作為一個人而活著,也就是具備「人間條件」不是那麼簡單的事,而是牽涉到歷史傳統的複雜問題,在現代情境中得不到容易單純答案,這是太宰治寫《人間失格》的文化背景。

●本文摘自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 出版新書《走在人生的懸崖邊上:楊照談太宰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