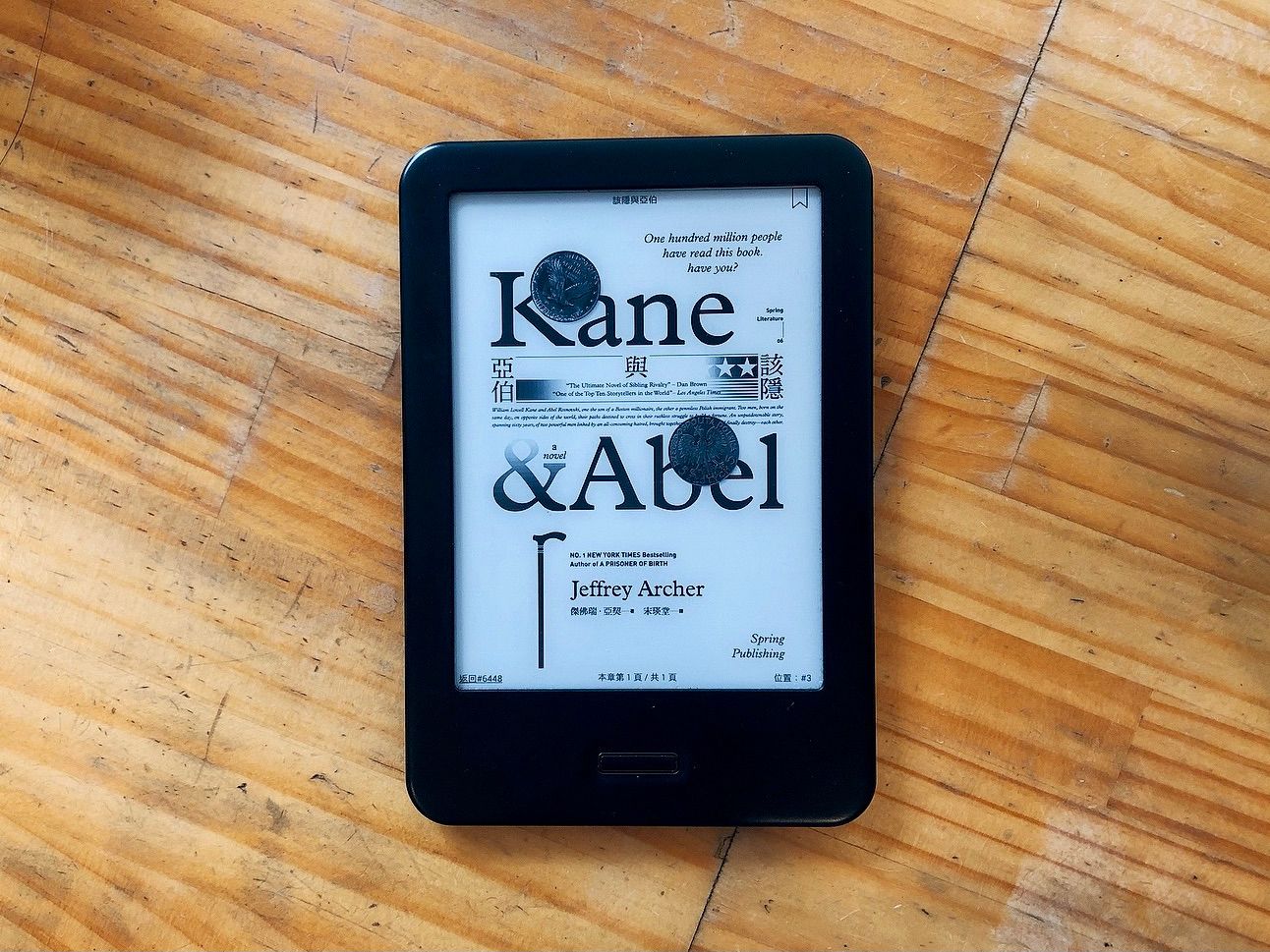「小說」 一張沒有靈魂的照片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七月,在多日豪雨過後的一個晴朗早晨,我手上提著一串出門時阿母塞給的燒肉粽,練着阿爸的那輛老鐵馬,一如往常地練啊練地來到盧師傅的照相館上工,才八點一刻,這南方城市的太陽就已炙熱得滾燙,從三民路過來十幾分鐘的路程,我的頭皮早已被蜇得麻辣辣,沿著廢棄運河旁直走並熟悉地往盧師傅的店門口衝,然後迅速跳下鐵馬,把它靠在騎樓柱子下,整個人頓住深深喘了幾口大氣,這一呼一吸之間怎覺一股不尋常的氣味,一陣陣腐屍般氣息自廢棄的運河底竄升上來,不過這很平常,因為豪雨淹滿了下水道,一些遭殃的死老鼠自然流到運河裡,時不時可見飄飄浮浮像脹滿氣球的屍身。
那年我十四歲,阿爸朋友推介我到盧師傅的照相館當學徒,當照相學徒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習慣黑暗,在黑暗中像一隻貓,持續地將瞳孔放大,靜靜窺視着一張張如鬼影般的黑膠底片,在暗房裡,師傅一邊將底片軸放入底片罐,倒入顯影藥水,經過顯影、急制、定影最後水洗,取出後交給我一張張夾在麻繩子上懸掛晾乾,在極弱的微光中,那些膠片上隱約浮現出各種臉孔,有男人、女人、小孩、全家福、結婚照、學生大頭照、以及為了拍遺照才照相的老人,這些如被放射線透視過的影像,帶給我極大的神秘感,我好奇地以為他們就是人的靈魂,於是,當我獨自在暗房裡時,我總感覺背後有許多眼睛一直眼睜睜盯著我看,我不時轉過身去瞧他們,心裡告訴他們:『你們放心啦!我會很小心,不會搞砸的啦!』
在當學徒的時候,一個人待在暗房的機會很少,都是跟著師傅一起進去,大部份時間在外間學修片,在我那年紀要成為一位修片師,感覺與現實差距還很遠,我不懂得大人所謂的美感是什麼?而我對人臉五官的概念也剛從“阿三哥”“大嬸婆”提升到“明星”,我想”明星“裡的明星臉就是大人們的範本吧!即使那只是想像,不過盧師傅的修片功夫到家,他的手法有如精緻的整形醫師,不同是他只需透過光影明暗的技術就能把照片中的扁平臉變立體,如鼻子墊高些,眼睛變大些,嘴巴變翹些,最主要是不失這個人的神韻,也就是看起來讓照片裡的人感覺有靈魂。
盧師傅時常說:『照相很容易,但是要照出一張有靈魂的照片可就難了。』
照一張有靈魂的照片? 我似懂非懂感到疑惑,要如何招換人的靈魂進入那塊黑布裡的盒子內呢?每當盧師傅在替人照相時,我就凝神專注觀看,看到底有什麼訣竅?有時盧師傅讓我的頭鑽進黑布底下,透過小格子視窗看見被照者的表情,一般來說看起來都顯得僵硬,尤其是一張嘴角上揚的微笑自己定格在那裡,我還沒有按過一次快門,也不知道哪來的靈魂?但是能夠照一張有靈魂的相片一直是我心中的願望。
話說,三十幾年前的那個夏天,就是濠雨過後舊運河浮著老鼠屍的那天,我如常地在盧師傅的像館內學習修照片,起初盧師傅會拿一些不要的舊膠片讓我學習描線,那天我很專注地描,ㄧ直到快中午休息前,盧師傅接到一通電話,當然是客人打來預約去某一個地點拍照,大多是結婚、生日、喜宴的時候,不過這通電話讓盧師傅的表情頓時僵住,一臉的為難說:
『好吧!馬上就去』。
盧師傅轉過頭來對我大聲喊:『阿弟仔,彼佇後驛e高十三伊媒死了啊,叫咱去佮伊照相,你趕緊傢俬款好齊,咱趕緊來去!』聽到盧師傅在喊,當下我心裡充滿疑惑,到底是要幫誰拍照哩?沒有預約又那麼緊急。
『歐,好啦!』
於是我筆ㄧ丟,一屁股從椅子上彈起去檢查盧傅的工具箱,底片,電磁,閃光燈...盧師傅自己在檢查相機咖擦咖擦測試了兩次才放心收把腳架收起,把老nikon小心塞進工具箱裡,盧師傅自己背起工具箱去發動山陽125,我則抬著笨重的腳架跟在後頭。那高十三是後驛在地的富商,亦正亦邪的霸氣作風,附近的攤商店家也不討厭他,算是廣結善緣,幾年前從商界收手,娶了個美嬌娘,夫妻恩愛遠近皆知,這夫人也不知得了什麼病,怎麼說死就死了呢?
當我們來到高十三的寓所,幾個幫傭的已等在門口,其中一個二十瑯當的小伙子,從我肩上接過腳架,一個使勁走在前頭領我們上了樓,門是敞開的 ,掀開鏽着鴛鴦鳳凰的門帘, 直接閃入眼前是一張紅暝床,床上躺著個女人,女人已換上了金線鏽袍,粉紅緞底牡丹繡被蓋到胸口,露出脖子和一張五官娟秀的臉龐,遠看神情如同睡着,近看那臉已蒼白毫無血色。
盧師傅吩咐我把腳架立在床尾,他自己鎖上相機,又吩咐女傭過來幫忙在夫人臉上塗抹脂粉,正當大紅口紅上完妝,盧師傅又要我去把夫人的臉抬高,下巴抬高,把唇角微微扳上揚,還將眼睛周圍的細紋撫平,就這般小心翼翼的調整彷彿深怕擾醒熟睡的女人,直到盧師傅感覺滿意為止。
盧師傅:『 阿弟仔,你過來!』
我:『..喔好..師傅...還要喬哪裡?』此刻我的背已經一片冷涼,這是我來當學徒第一次遇見的事,在此之前,盧師傅的相館應該也難免會幫死人拍照吧!我想。
盧師傅:『你過來!我不要拍沒有靈魂的頭!』
我:『.. 啊...』師傅在我耳邊小聲咕嚕着,並騰出位置要我近前操作,他偏過臉退到我身後。
盧師傅:『來!你來按!』
我:『...我...』
盧師傅從相機前移開,手指着他腳下站的位置要我站過去,我照著他話做,把脖子伸進黑布裡,對著調好的視窗,我從鏡頭望去一張沈睡中猶有輕輕微笑的臉,一個咖擦按下了快門。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按快門,對一張死去的沒有靈魂的臉。事後,高十三付了很優渥的酬勞給我們,這感覺不知應該是喜還是悲?聽說高十三一直把那張照片掛在床頭,天天陪伴著他,直到老死未有再娶。而盧師傅自己也留了一張,還時常指著那張照片說我:『你看!你拍的人像沒有靈魂!』
人死後拍的照片就沒有靈魂了嗎?我很吶悶,我記得當我從視窗看見那張臉的時候她似乎在輕輕地微笑著呢!於是我在那一刻按下快門,我相信她的靈魂正對着我的鏡頭微笑定格呢!在那十四歲的夏天,我學習到人都有一死但死亡無法將相愛的倆人分開,還有,我不想要沒有靈魂的活着。
後來我沒有成為攝影師,但是照相一直成為我生涯中的嗜好,在這攝影工具數位化的時代,每個人隨手都可拍一張人像,但是就如盧師傅說的:『照相很容易, 但是要照出一張有靈魂的照片可就難了。』
完
Molly Lee
5會員
15內容數
留言0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