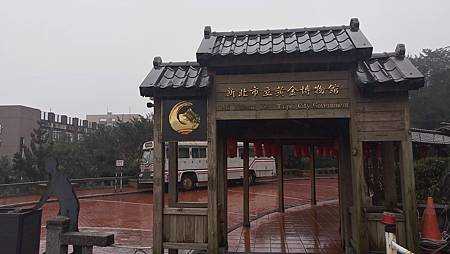以博物館來探索城市?藝術家、策展人在城市博物館的角色
在1995年的專刊中,有兩篇經常被拿來引用的經典文章(Jones, 2008: 6)。分別是妮可拉強生(Nichola Johnson)所寫的〈探索城市〉(Discovering the City),以及赫伯迪克(Max Hebditch)的〈關於城市的博物館〉(Museums about Cities)。前者當時為東安吉拉大學博物館學的學者,後者為倫敦博物館的館長。
赫伯迪克館長以其豐富的藝術行政經驗指出,要討論與城市有關的博物館,要先定義何謂「城市」。通常,會有兩個取徑來討論城市。第一種,強調其地理性的、行政管理與開發起來而構成了城市的區域,並以此與鄉間有所對照。另一種,則是強調人們相互之間組織的方式,以對比出都市與鄉村社會的差異。赫伯迪克的區分方式,在既有從地理與行政體系的物質基礎上,試著強調「城市」這個時代性產物,更值得討論之處,在於其所牽動的,構成人際與社會間,特有的組織與溝通方式,以及特定的心理狀態。放在博物館的思考架構上,他進一步地從典藏角度,提出了四大類型的資料,分別是:物件(artefacts)、環境證據(environmental evidence)、地點與事件的紀錄(records of places and activities),以及證據(testimony)。他以此資料典藏的思考架構來建議哪些東西與城市有關,最後可以進入博物館的典藏中(Hebditch, 1995: 7-9)。
所謂的「物件」,指的是在這個城市中所存在的/使用的,與這個城市的脈絡相關。「環境證據」指的是,從自然史博物館的實踐來看,人們探索對環境衝擊的各種證據,但關於對城市環境的影響,在博物館裡卻少被關切,這應該是未來值得持續關切的。
對地點與事件的紀錄可以分成三個層次, 分別是「歷史物件與檔案」、「歷史地圖與城市和建築的平面圖」;以及「博物館自身研究與典藏過程中留下的紀錄」。這些資料對於認識城市的空間配置至關重要,有利於對城市遷徙、變動的社會結構、土地利用與經濟活動等等的討論(Hebditch, 1995: 9)。也就是說,這裡對於博物館地點與事件記錄的觀點同時是物質性與後設性的。一方面是對於靜態檔案性資料的收集與呈現,此外,由於涉及了實質環境變遷,必須對這些變遷過程也留下圖像與文字等多元紀錄之外,博物館如何收集、整理、詮釋與保存資料的過程,也應該詳加記錄。
所謂的「證據」可以從溝通表現形式區分為「影像」與「口語」兩大類。前者像是繪畫、圖案、印刷品與照片。這些資料看似客觀,卻有賴於如何詮釋與運用這些素材(Hebditch, 1995: 9)。他雖然從博物館的典藏角度,來論述如何找到或辨識與城市相關的資料及素材,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將這些博物館典藏的素材和歷史證據連結起來,對城市博物館所肩負著,為公眾闡述與詮釋城市的使命是重要的。
赫伯迪克館長以當時(1993年)倫敦博物館耗時三年推出命名為「在倫敦的人們」(The Peopling in London)展覽為案例,來詮釋這項見解。這是一個結合了博物館專業人員從典藏研究所發展出來的展覽,同時搭配出版與對外提供服務。展覽主題探討那些移民倫敦的人們,在城市中的感受及其所產生的影響。

「在倫敦的人們」(The Peopling in London)展覽 (圖片來源:Internet Archive)
研究人員經由研究各種典藏資料,在這個展覽裡挖掘出三個重要的課題。第一,這個展覽的內容挑戰了許多倫敦移民在過往紀錄中相當罕見的假設。第二,經由這個展覽發現,倫敦博物館跟許多在地社群之間是有所連結的,只是過去較少聯繫。第三,採取一個超過兩千年的編年史觀來作主題展可以發現,移民不再是一種當代的新趨勢,或是一般人普遍認知的危險現象,因為對任何一座大都會來說,不同種族與背景的人混居一起,是很自然且舉世皆然的現象。透過從展覽素材的挖掘,以及藉由展覽來說故事,城市博物館可以妥善地運用自身優勢與專業技能,讓這些故事和現代社會有所連結(Hebditch, 1995: 11)。
綜言之,「城市博物館」的重要任務在於,詮釋與解釋都市社會及其變遷歷程。策展人必須要可以整合三種證據,以從中獲得的洞見:第一種證據來自於考古學,包含物件的型態與空間使用,或這兩者間的關係及其變遷歷程。第二種來自於圖像與口語的證據,以提供人們在情感與想法方面的證據。第三種則是檔案文獻類的證據。除了前述三種物質證據外,「城市博物館」更需要的是對每個地方獨特處的敏感度(Hebditch, 1995: 11)。
博物館館長從博物館專業技能的物質性面向切入,提醒了如何從典藏與展示的面向,探索個別城市的獨特性,也從時間軸線的歷史縱深,同時挖掘出人類社會具有普同性,及其特殊性的關係與對話。但除了掌握善用資料與證據的能力外,不可諱言地,博物館裡的展示,任何的證據資料,必須經過一個視覺化的轉化過程。也就是將硬邦邦的歷史材料或文物,轉化為讓博物館觀眾可以消化的展示材料。當然,隨著時代進步,各種展示科技與技術的發展,讓這個視覺化的過程可以被充分設計。舉例來說,郭雪湖的《南街殷賑圖》,原作掛在博物館裡展示,觀眾可以充分體會藝術之美,或是從其筆法、色彩、構圖等不同層面來分析畫作構成;應用擴增實境等展示手法,則可以創造出讓觀眾在博物館裡體驗當年的市井喧囂的街肆景觀,甚至,還可能創造氣味與聲音等,更為豐富的感官體驗。但所有這些花俏的展示技術與工具,核心價值在於讓觀眾在感受與體驗之際,能夠理解當時的社會情境、城市景觀與畫家創作間的連結;或者,更進一步地,從當時的日本殖民歷史脈絡,來解讀這幅作品的市街再現中各種訊息。關鍵不在於運用了什麼樣的高科技展示手法,重要的是意圖傳達的訊息,是否可以透過這樣的展示方法,讓觀眾更容易感知與理解,達到博物館與觀眾溝通的意圖。
那麼,對於藝術家來說,在城市博物館中,要如何以其藝術生產的觀點,跟觀眾有更好的溝通呢?專刊中另一篇文章提供了兼具藝術家/策展人觀點來檢視博物館展覽的看法。
海德根(Carl Heideken)提出了以一個藝術家在城市博物館中應該如何策展的見解,並從這個提問的問題意識出發,闡述他自身在諸多城市博物館工作的經驗與觀察。對藝術家來說,可以在博物館裡創造跟觀眾對話的方式,是一種很好的工具。但這其中一個很大的差別在於,「藝術」在傳統的美術館展示中,作品的展示與存在,乃是意圖引發觀眾的感受與共鳴,許多作品有很大的自由度,也可能透過虛擬、幻想,創造出充滿奇想的作品;而這個互動溝通的過程,來自於觀者和作品之間的聯繫,某個程度訴求於相當個人化的、難以複製或假設觀眾的反應為何。甚至,我們可以說,藝術即是為了引發觀者的感受與想像。
然而,在城市博物館的展示活動中,展示內容某個程度乃是具有反映與再現真實世界的需求。海德根提出一個主張:如果我們接受今天在討論歷史時,歷史是一個被主動書寫的過程,而沒有所謂的客觀或絕對的存在,那麼,我們應該也必須清楚知道,博物館是一個人們參與其中,主動創造的場域,而不是存在著某種「客觀」真實的機構(Heideken, 1995-18)。這樣具批判性的主張,於今看來或許並不新鮮,但放在「城市博物館」實踐的脈絡來看,一方面提醒觀眾,可以如何理解與觀看展覽,另一方面,毋寧是更為基進地,想要提醒博物館專業者,如何看到自身如何在訴說一個城市的故事。
海德根具高度批判企圖,意圖以藝術創作的展示跟博物館既有的典藏品對話。他想要揭露的觀點是,博物館觀眾必須體認到,任何一個展覽都是由策展人員與設計者精心規劃過的;換言之,這些展覽所欲呈現的意涵,也都是經過建構,而非只是本質固有於這些藏品和物件身上。此外,他也相當睿智地點出,藝術作品與典藏品間的對話形式必須不斷創新,否則,這樣的展示型態無法產生新鮮感(Heideken, 1995-19),在這個層次的意義上,則是關切於博物館專業技藝的反思了,特別是對一個同時具有博物館策展與藝術創作背景的專業者來說,如何在角色切換之間,既能確保在展示論述上的反身性思維,同時在展示技術上的創新性。
另一方面,海德根發現,藝術家在博物館裡成為一個經常要幫不同專業者彼此跨領域的工作者,包含協助展覽成形的建築師、畫家、雕塑家、攝影家、影像工作者等等,都在這個工作過程中被捲動進來,大家彼此都在跨界,也都在支持著不同專業做好自己的工作。而他同時身為藝術家/策展人的角色,在此可以經歷一個沉思的機會。特別是在藝術家跟學術研究者之間,海德根認為,相較於學者總是埋首於成堆知識中,藝術家僅能訴求於本能的感受來回應,但以「藝術家/策展人」的角色,則嘗試在這兩端折衝協商,他們必須要能掌握歷史學家、人類學家或是博物館教育人員的企圖與方法,並以此來判斷藝術家作品的形式與內容的品質如何。
藝術家/策展人充分能掌握相關的文化符碼與脈絡的關係。放在博物館裡,並不是所有的觀眾都能夠掌握這些展示文法;觀眾對一座社會史主題的博物館,跟一座現代藝術的畫廊的預期也有所不同。身為一個藝術家/策展人,海德根期待看到觀眾帶著微笑,辨識出館方建構的展示中,所欲揭示或傳達的訊息。他以自己在斯德哥爾摩城市博物館執行的展覽為例說明,這個名為「家─私人情感與公眾規劃」(Home-Private Emotions and Public Planning)的展覽裡,展出許多城市居民的照片,也採訪他們,從影像與口語闡述兩個層次的呈現,讓觀眾以此來詮釋他們所看到的世界。此外,透過將訪談整理成文字稿,觀眾有了第三層次的詮釋素材,這樣的做法,乃是館方希望邀請觀眾參與在這些訪談中,以共同完成對何謂「家」的詮釋。換言之,策展人期待,在這個從展示出發,邀請觀眾共同參與詮釋的過程中,觀眾可以歷經「事實」如何由此誕生,而不是只是盲目地相信博物館餵了什麼給你(Heideken, 1995:21)。
海德根這個展覽案例的實踐,從批判視角警醒於博物館展示本身可能難以避免的特定立場或價值。然而,其策展中納入觀眾共同參與的做法,也實質論證了當代博物館積極邀請觀眾共同參與在展覽詮釋過程中,避免過於單向且觀點單一的展覽論述生產。這樣的批判性意識展現於二十世紀晚期,博物館實踐場域對於多元社會文化差異有著更高的敏銳度與反思力。例如,在
這本專刊中,卡拉(Amareswar Galla)另一篇鏗鏘有力的批判文章:〈都市博物館學:一種和解的意識形態〉(Urban museology: an ideology for reconciliation)。
卡拉教授為印度裔。在新德里、澳洲等地受教育,也在許多國家不同城市出任博物館學領域教職,更活躍於聯合國的各種相關組織中。他的文章,直接破題點出,當代城市面對多元文化、多元族裔的地景,這些課題自然是城市博物館必須面對的。殖民導致的離散社群,全球性的國際移工流動,以及基於政治困局的難民等等,都是當代民主社會無法忽視的新挑戰。
工業化、都市化這兩股共同作用的力量,在二次戰後,使得全球人口的多樣性,在地區性、區域性,國家與國際等各個層級,都變得更為複雜多樣。如此一來,對城市博物館來說,要面對與處理的人口特性,及其在文化上的再現也變得更為複雜。當博物館要處理與歷史有關課題時,通常公眾會期待博物館應該要成為一個更為文化民主的機構,以展現都市場域中,多樣豐富的人口特性;許多博物館有意地透過特定族裔文化主題的展示,以支持都市多樣的文化活動。換言之,城市博物館扮演了一個支持城市多元文化架構及其持續穩定發展的角色(Galla, 1995: 40)。
然而,城市博物館不僅是關於城市中心及其發展與歷史的創生而已。更牽涉了都市發展過程中的有機演進,以及都市中心的延續性課題。因此,許多攸關城市居民生活的各面向,舉凡城市交通、住房、公共衛生與醫療,就業與傳播系統,以及典型支配性文化意識形態等等,加上社會正義等課題也牽涉其中。某個程度來說,「城市博物館」就是一個批判性的機制,卡拉教授提醒,城市博物館不應該落入一種二元分化的刻板印象,認為城市文化保存是靜態的活動,而文化發展是動態的,應該更積極地看待博物館作為一座文化設施,以支持個人和社群認同與自信的核心價值。他且指出有五個向度的許多相關活動,都與這樣的理念有關:(1)當代的藝術運動,包含把舞蹈和歌劇等古典形式,整合為我們的生活與動態資產的形式;(2)重要的節慶與事件活動。(3)保存、延續與管理文化資產。(4)社群的聲音、價值與傳統。(5)在更為廣泛的環境中,我們必須發展永續的文化系統(Galla, 1995: 41)。
在卡拉教授的詮釋中,「城市博物館」對於支持城市文化多樣性,與在地文化傳統的延續與傳承,可以扮演積極且有所助益的角色。他不僅將城市博物館與在地的文化資產保存延續相提並論,主張博物館應該要具備包容性(inclusivity),更直接點出,必須要以「社群參與」來讓文化更豐富。為了要達成這樣的目標,他以ICOM原本對博物館的定義為基礎,提出了城市博物館的工作定義:
「城市博物館是一個非營利的、動態與變動的常設組織或文化機制,以服務都市社會及其發展。對公眾開放,且為了多樣的人群及其所處環境,以及研究、教育、和解、溝通、娛樂等目的,以整合、獲取、保存、研究、溝通與展示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
城市博物館是一個為了都市人文化再現而整合活動的中心。其採取的方式包含:(1)讚頌共同的認同,地方感與多樣人權的自尊。(2)為都市中心及周邊區域的自然與文化遺產相關的社群文化發展活動,提供焦點與資源。(3)建立一個中心以整合保存、展現、延續與管理所有人們對於藝術類的、文化與遺產的熱情。」(Galla, 1995: 41)
因此,城市博物館需要(1)發展整合性與全面的社群文化發展路徑。(2)建立或重建自身為一個多目標的機構,以具備回應與刺激跨越了藝術構成,遺產與社區利益等不同類型活動的能力。(3)提供地區內遺產與藝術產生相互關係的機會,並且讓城市中心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社區。(4)透過會議、論壇、交換想法與辯論、互動劇場與遺產展演等多元方式,讓更廣泛的社群來探索其自身的地方感。(Galla, 1995: 41)
卡拉教授這篇文章雖然出現在1995年,但可以說是相當具有前瞻性地,一方面試圖調整博物館的定義,也提出了現在相當受到重視的幾個核心概念——博物館的包容性、人權、文化遺產、多樣性與社群參與。更重要的,在他的文章所闡述的價值中,早已經跳脫以博物館「機構」為思考中心,而是轉而以「人」作為博物館關切的所在。城市,為人們聚集之所,博物館關心居住於此的人們及其生活日常,以城市作為理解在地社群的博物館尺度,也就變得再理所當然不過。只是,當1990年代,全球化的腳步越來越快,邁入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時代,城市博物館又面臨著何種時代性的挑戰呢?
原文網址 https://artouch.com/artcobooks/content-116699.html
相關書籍

建築學者殷寶寧最新著作
《臺北.城市.博物館》
跟市民一起經歷每日城市生活,並期許致力於朝向更好的城市未來推展的「城市博物館」,在臺北,究竟會以何種姿態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