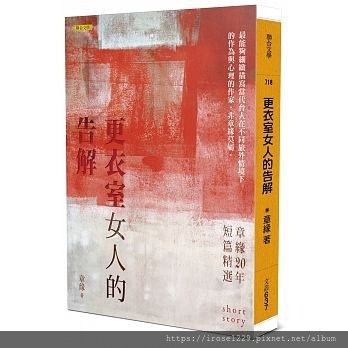章七十七
萬里晴空,日輪正當中,鴻雁結群北歸,激越鳴叫,昭告天下寒冷的季節已然過去,溫暖濕潤的天候即將到來;千畝甫田,陌路錯此方,稻薑如茵南種,快速抽長,預示眾庶桌上的菜餚已非醬鹹,豐富多樣的滋味更為適口。
農夫躡屐刈禾莠,田犬搖尾吠行人,寧澈和桓古尋走在田間的小路,形如雞蛋,頂若竹笠,用來存放米糧的穀倉座落農舍旁,少的二三並排,多的四五成聚,足見年年豐收,家家戶戶不愁吃食。
「這兒的農戶這麼多,該從哪裡找起呢?」今兒個太陽很大,桓古尋拉了拉領口,讓有些汗濕的前胸透透氣。
「你覺得呢?」寧澈反問:「是甚麼樣的緣故,才會讓這種產於蘇、常兩州的秔米,出現遠在千里之外的神都?」
桓古尋答:「就像你之前推敲的,他們都到過同一個地方,例如水田、稻埕、穀倉……」
「以及水碓房。」光潔的下頷稍仰,示意前面一間茅屋,屋旁一輪水車直立而轉,屋裡傳出哆、哆、哆的擣擊聲,密集規律,正納悶那是甚麼,寧澈再道:「水碓是南方礱米、舂米的機具。以水流帶動水車運轉,水車的輪軸再撥動碓桿,使桿末的木杵上下移動,並將石臼埋在木杵下,稻穀放入石臼裡,木杵即能碎殼去膜。第一次來江南時,我對這東西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兩人走進水碓房,就見水車的中軸自外延伸入內,貫穿整間房,十來根碓桿分列中軸兩旁,一齊運作。每根碓桿中間皆有支架撐高離地,一端接合木杵,另一端則由水車中軸上的木片撥推,木片一觸及相對的碓桿,碓桿此端應力往下,彼端的木杵就會高高上翹,木片轉走後,沉重的木杵直直墜下,重擣石臼裡的穀粒,狀似秤鉈一邊高,一邊低,周而復始,無人自舂。大量降低人力消耗,村民只需算準時間,記著回來收取自家的米就好。
「哆、哆、哆、哆、哆、哆……」舂米的聲音很響,外頭又有淙淙的流水聲及轆轆的車輪聲,純亮的嗓聲遂提高音量:「那兩粒秔米均已去除殼膜,煮熟了就能吃。嘉興人民大多務農為生,自給自足,少有糧行賣米,秔米不是在灶房,便是在水碓房。」
他又道:「嘉興縣是蘇州乃至整個中原的糧倉,禾稼穰歉,關乎江淮一整年的康儉。秔米十有八九出自茲,加上晉淵莊不在嘉興招募新兵……我不認為這是巧合。」
「但是不算農戶,光是水碓房,這兒起碼有上百間,總不能一個個找。」大手爬梳頂上毛髮,桓古尋道:「假設他們都曾來過嘉興,該先弄明白他們要幹甚麼,這兒就是他們的大本營嗎?」
「晉淵莊的名頭裡雖有個『莊』字,然是否真有那麼一座莊宅,尚不得而知。」寧澈分析:「蘇州全境地勢低平,叛黨真將本營設於此處,不消一個月,便給朝廷的鐵騎踏平,常州的地形也差不多,惟西南方有三座山,山勢均不高,山裡住了一堆修道人,潘文雙已逐一盤問,那些道士皆為不食人間煙火的方外士,不似叛黨。」
桓古尋沉吟:「倘若沒有所謂的莊宅本營,那他們把軍備放在哪裡?出兵前又在哪兒集結?」
「就目下所知尚不足以推斷。」寧澈道:「回到剛剛的問題,他們來這兒幹甚麼?」
「絕不是整隊行兵,那等於告訴大家快來打我……」桓古尋摩娑下巴,忖道:「也許是有很重要的人事物,促使他們到這裡來……會是慧觀嗎?」
寧澈蹙眉思索:「若為慧觀,那米粒該是從出江寺的灶房出來……可是你想想,這樣至少有一人去出江寺時,不但與慧觀碰面,還出入灶房,搞不好還做了飯,使得米粒不經意地滾進衣袖,再乘船渡江越河,抵達洛陽,去了郊外的染坊與城內的小屋後,落下米粒……」
「不太可能。」桓古尋搖頭晃腦地否定:「慧觀離寺前,已十幾年未曾與晉淵莊來往,就算真有這麼一個人,進了出江寺的灶房洗米煮飯,事後能有多大的機會,讓兩粒米分別掉在染坊與小屋?」
「所以呢……」寧澈進而推想:「他們應是待在一個米粒很多,多到溜入衣襟褲兜也不自知,而那些人離開該處後,分頭行事,米粒亦因而散落在不同的據點。」
「倘使該處真為水碓房,房內有機具有米糧,太過擁擠,更不會是為整兵……」桓古尋搔了搔頸側,然後大眼一亮:「難道來的人僅有晉淵莊的高層,像是堂主、太陰使、太陽使……甚至是莊主?」
寧澈露出贊同的微笑:「那他們便是為商議後續行動,方同聚此地。再大膽一點猜測,莊主平時便在嘉興境內走動!」
舌尖滑過唇廓:「既然將目標鎖定在水碓房,那該從哪一間下手?」
「我說過了……」深邃的長目來回掃視房裡的水碓,「它是一處米粒非常非常多的所在……這水碓房不小,但仍不夠大。」
桓古尋遂問:「嘉興最大的水碓房在哪兒?」
「貴為一國糧倉,錢塘江以西,嘉興坐擁最多軍屯官田,自有官倉轉運穀糧、賑災濟民。」寧澈答說:「官倉旁的水碓房,肯定大得不行。」
*****
「小龜,你怎地真跟隻烏龜似的,走路慢吞吞的?」謝追鴻行在頭前,瞧師弟始終拖著腳步於後,忍不住回首抱怨。
「呼……好熱,我想喝水……」羅韞盤抬手搧著被曬紅的臉龐,但沒甚麼用。
談皓遙指前方,「那邊有戶人家,向他們借點水喝吧!」
羅韞盤聽了便加快腳步跟上,謝追鴻不禁念道:「你可是習武之人,怎能如是嬌氣?」
「我汗流得快,水當然也喝得多。」匆匆拋下這句話後,不等師兄師姐,逕自跑向那戶人家。
來到柴門前,羅韞盤拍拍門板,喊道:「有沒有人啊?方便給嘴乾的旅人一杯水嗎?」
「咿呀──」門扉應聲而開,卻不見人影,猶自奇怪,軟嚅的童音自下方傳來:「水井在左邊的茄苳樹下,你要碗嗎?」開門迎客的小女孩兩條辮子紮在頭頂,目光無畏,猶有一個年歲更幼的弟弟藏在姐姐後面,僅探出半邊小臉,怯生生地仰望陌生人。
羅韞盤蹲下身來與之平視:「我要三個,麻煩小姑娘你了。」
「我不小,我已經十二歲了!」女孩叉著腰,略顯不滿。
「唉呀,是我說錯了,該打!」他輕掌嘴頰一下,又問:「姑娘,你的娘親呢?」
「阿娘去送午飯給阿爹,阿爹是耕田的。」小女孩邊答邊往家裡深處走,再踅回門口時,小手捧著四疊碗,並言:「井裡有阿娘早上放落去的涼茶,很好喝喔!」
「多謝!」談皓和謝追鴻亦雙雙走近,她問說:「姑娘,你可知你阿爹耕得是別人家的田,抑是自家的?」
小女孩牽著弟弟,領著外人踱至井邊,「是官田,阿爹說縣老爺是大好人,知曉佃農辛苦,地租房租收得很少。」
謝追鴻轉著井上軲轆,拉起井裡的茶壺,接連倒了四碗,第一碗給小女孩,自己則與師妹師弟各拿一碗。女孩啜了一小口涼茶後,湊到弟弟嘴邊,也餵他喝了兩口。
井水冰鎮過的茶解渴也解熱,羅韞盤咕嚕牛飲,耳聆大師兄問:「小妹妹,你們這裡時常有目生的人造訪嗎?」
小嘴一嘟,女孩撇開臉,冷冷地回:「不知道。」
謝追鴻眨眨眼,心想我哪裡得罪你了,但聽小師弟嗤嗤竊笑,又問一次:「姑娘,你有沒有看過可疑的叔叔伯伯,在附近的水碓房神神祕祕、鬼鬼祟祟的?尤其是晚上的時候。」
是次她肯回答了:「沒有,阿爹說村民們都很友善,能在嘉興安穩下來是我們的福氣。」
「哦?」談皓發問:「聽姑娘此言,你們家不是嘉興人?」
「對呀!」女孩答道:「我們家原本住在隔壁的吳縣,那時佑佑尚在阿娘的肚子裡,阿爹講那兒的租金太高,我們才搬到嘉興來。縣老爺對我們很好,如果今年的收成不好,他便會免去租金,說明年再繳。」
「那最近有沒有新來的住戶?」談皓再問。
「唔……」女孩側首想了想,說:「沒有。」
「這兒也沒有……」謝追鴻有種陷入死胡同的感覺,數日以來,走過的農村、問過的農家均給出雷同的答案,沒有生人遊走,鄰里間相處融洽,一如世上其它千萬個村莊般,平凡而和睦。
真正如斯,心底那股揮之不去的詭異感又從何而來?
「阿娘!」一直默不作聲的弟弟忽然放開姐姐的衣角,奔向左方小徑的一名農婦。農婦熟練一撈,單手托著小兒子,又續:「湘湘,你在跟誰說話?我不是說過阿爹阿娘不在家時,不能隨便打開家門嗎?」她招手喚女兒過來,口氣嚴肅。
謝追鴻說:「大姐午安,我們是從洛陽來的,因為我師弟口渴,只好厚著臉皮向令嬡討水喝,還請大姐莫責怪令嬡。」然後掏出一串銅錢,遞予農婦。
農婦見他們三人衣冠楚楚,面善有禮,於是鬆下戒心:「不是我婦人家小氣,而是這裡不常有外客來遊玩。」她不眼饞錢財,見著三人腰間的三叉鐵尺,僅說:「屋裡還有飯菜,三位少俠若不嫌棄農家菜粗淡,要不吃頓飯再走?」
談皓想再打探得更詳細些,欣然答應:「那就叨擾了!」
四大兩小魚貫進屋,跨過門檻便見祖先牌位置中而設,左手邊是草席矮几,右手邊是方桌板凳,桌上擺著兩菜一湯。
農婦放下小兒子後,往灶房走去,並說:「咱家房子小,隨便找位子坐!我去拿碗筷。」
湘湘和弟弟各自坐上一只板凳,吃著碗裡沒吃完的食物。談皓也揀了一只就座,謝追鴻和羅韞盤則落坐草席。
「恰好今天是我公公的忌日,特地殺了一隻雞,煮的菜比較豐盛。」農婦擺上新的碗筷後,為客人各舀一碗飯,夾了兩撮白菘、一塊竹筍燒雞,甚為大方,「三位不用客氣,儘量吃,吃完飯尚有蜊仔湯可以喝!」
這戶人家姓霍,丈夫是二房,村裡的人習慣叫他霍二,其妻便是霍二娘。談皓親切喚她姐姐:「聽湘湘說,二姐姐你們是吳縣人,雖然這裡離吳縣不到三十里,但終究是異地他鄉,舉家搬遷,必經一番勞苦,方得安居樂業。」
「適應新生活自要花上一段時日。」霍二娘再添一碗飯,「多虧有左鄰右舍的協助,他們當中也有不少人是從別處來的,我幫你鋤田插秧,你替我看顧小孩,利人利己。」
「哦?」羅韞盤口嚼香噴噴的米飯,「沒想到這裡這般受歡迎,能吸引外邊的人前來開墾耕耘。」
「受歡迎自有其因。」霍二娘道出緣由:「比起那些動不動就漲租苛扣的大地主,官田收租低廉,嘉興的土地又肥沃,少有歉收年,若不幸碰到,李大人亦會減租開倉,有哪處及得上這處?」
談皓道:「怪不得我們一路行來,途經的水碓房輪軸頻轉,猶在疑惑暮春時節,穀倉裡的稻穀不都該見底了嗎,怎地還軋軋不斷?原來不只住到好地段,還遇上好老爺。」言罷,吃下一塊燒雞。
霍二娘再夾一塊給她,隨口詢問:「聽妹子頗感心動,似乎有意在此住下?」
「是啊!」嚥下嘴裡的雞肉,談皓說:「實不相瞞,咱仨正在為家中的姥姥尋個養老處。姥姥年事已高,身子骨大不如前,念及勞累大半輩子,還未好好享受過人生,久聞江南風景優美,生活步調不像京城緊湊,便盤算南遷至此,安養天年。」
此時謝追鴻走至桌邊,夾了一撮白菘至碗中,順便探問:「聽二姐姐敘述,這兒的確物饒人秀。不悉治安如何,夜晚可有宵小徘徊?」
「少俠儘管放心!」霍二娘說:「這兒暗時只有狗吹螺、貓發春,有李大人在,那些強盜惡徒豈敢靠近嘉興一尺?他前些天還親手格斃那個橫行霸道的顧惡少!那時顧家老子人在京城,事情傳至他耳裡時,驚得他當場吐血,後來還想向蘇州的刺史討公道,但李大人是依法行事,有理有據,他又能怎樣?」她一面夾菜入嘴,一面口沫橫飛:「小孩子當真寵不得,不然小時鬧家,大了禍害他人,末了就害到自個兒,丟了小命。」言罷,喝茶潤口,然後秀麗的細眉忽地一斜,大力叩杯在桌,放聲怒喝:「霍家佑,你在幹嘛?」
家佑弟弟趁著大人們談話時,揣著大碗滑下椅凳,偷偷摸摸地溜向門口,本以為神不知鬼不覺,不料卻被眼尖的娘親發現,嚇得他手一抖,差點把陶碗摔到地上!
但聞霍二娘再喝:「你敢把菜倒掉的話,以後你就給我吃餿水,甭想再碰老娘做的熱菜熱湯!」不僅是家佑,謝、談、羅三人亦被霍二娘宏亮尖銳的話聲震得心一緊,惟獨女兒湘湘早已見慣這種場面,泰然自若地吃飯喝湯。
而後她神色陡轉,復回剛才的和顏悅色:「你瞧,小孩子就是這樣,講過的話永遠是左耳進,右耳出。妹子日後有了兒女,可得好好管教約束。」
「自然、自然……」不著痕跡地拭去額角冷汗後,談皓說:「安逸太平固然是好,那麼這裡的人怕生嗎?姥姥生於洛陽,長於洛陽,北方口音忒重,恐驚會和鄰居們處不來。」
「別的村子我不敢說,但若落腳在這個村子,妹子大可放一百二十個心。咱村大都是從外地來打拼的艱苦人,村南的黃家和李家以前也是河洛人,大夥兒都能體會在異鄉的不便與難處,只要你不是歹人,我們都熱情相待!」話行半處,霍二娘思及某事,道:「說到外地人,去年隔壁村多了張新面孔,不時來我們的庄頭,只不過……」
敏銳捕捉到此中的遲疑,謝追鴻忙問:「只不過甚麼?」
「只不過那人未知是初來乍到抑或怎地……我頭一回見到他,是某次湘湘在外面跟人玩耍,玩得太高興,一不留神跌了一跤,磕破嘴唇,血流得滿口滿地,疼得她哇哇大哭,恰逢他路過安慰,遂好心帶湘湘回家。那時正值炎夏,他抱著湘湘,把斗笠給湘湘戴著擋太陽,腰間掛著鐮刀,手提一袋蜜桃,說是來咱村拜訪朋友。我向他道謝後,他還送了湘湘一顆桃子……」霍二娘細細回想:「約莫一個月後,我們倆又在村北巧遇,同樣是來訪友,那次他卻拎著魚網魚簍,大概是改行作漁夫,我沒問得太多,寒暄幾句便分開。再過一陣子,佑佑得了傷寒,我去縣城抓藥,在城裡又碰上他,他人在對街,隔著人潮,我沒和他打招呼,但瞧他一襲青衫乾乾淨淨,半捲著袖子,似在替人跑腿……」
羅韞盤舔去嘴角的醬漬,抹了抹油膩膩的嘴巴,道:「不就是換頭路換得頻繁些嗎?莫說人生地不熟,就是成年剛離家的小夥子,也會到處試試,碰碰機運,有何稀奇?」
霍二娘道:「他可不是甚麼小夥子,年紀比我家相公還大,三十五歲有囉!沒有穩定的生計,好像亦無妻小,看上去也不是那種遊手好閒的人,那樣子可真少見……」
扒了一口飯菜越過齒關,謝追鴻說:「大丈夫沒有成就一番事業,何以為家?」
「那倒是……」霍二娘喃喃,思緒似已飄到別處。談皓見了,笑著調侃:「二姐姐,那個『他』究竟生得有多俊?教你這般魂不守舍。」
聽得這番話,兩個大男人登時瞭然,對方必定是一位美男子,霍二娘才會如此關注。羅韞盤和謝追鴻皆非八卦的好事者,卻不免面露好笑,羞得霍二娘直揮手,道:「妹子別瞎說,孩子們還在呢……不準笑!你們男人不也愛看路上的漂亮姑娘嗎……」
這頓飯吃得開心,聊得也熱絡,飯後又有水果點心,直到午後的陽光不再毒辣,客人起身欲離,本想給點錢當作餐費,然霍二娘搖手推拒,任憑謝談二人好說歹說,不收就是不收,最終是羅韞盤道:「二姐姐,這些錢你就拿去吧!從城裡請個先生來,教孩子讀書寫字,這樣湘湘長大後才不會被壞人騙,佑佑未來說不定還能中個狀元!」提及兩塊心頭肉,霍二娘果然動搖,咬了咬唇,勉強收下。
告別霍家,已是未時末,謝追鴻挺著飽食的肚皮,「可惜沒套出甚麼有用的情報。」
談皓道:「清官治下的嘉興人際緊密,居民守望相助,風土淳樸,若有面生的人來來去去,必會引起注意。」
於是師兄揣測:「晉淵莊合該是扮作普通的佃農,偽裝成當地人,將農民蒙在鼓裡。」
「我有特別留意經過的農家佃戶,其步伐沉重,喘息短促,均是不識武藝的莊稼人。」黛眉微攏,她說:「但願桓兄弟那邊有好消息……」
「我去瞧瞧!」羅韞盤自告奮勇:「你們倆慢慢查,回頭見……呃……」謝追鴻揪著他的後領,道:「我去。」不理會小師弟難為的表情,兀自朝東而遠。
「走、走吧……」羅韞盤撓了撓右臉,往西而行。
談皓沒有移動腳步,「你就這麼不想看到我的臉嗎?」
「哪、哪有……」他仍是背對談皓,支支吾吾:「正……正事要緊,還是……」
「羅韞盤,看著我。」女聲強勢,被呼喚全名的人下意識轉頭正身,但見花瓣般飽滿厚實的雙唇微翹,秋水般的眼眸含嗔帶怨。
羅韞盤的心臟幾乎破出胸膛,有口不能言,有耳無法聽,只瞧緋紅的唇瓣開開闔合:「既然這麼在意,為甚麼問都不問一句呢?」
「問……問甚麼?」羅韞盤的思考能力尚未恢復。
兩道柳眉間的皺摺瞬間變多,他倏地醒神:「這……這是你和師兄間的事,你們兩個說好就好,何況是師尊的意思,有甚麼好問的……」談皓鼻息重哼,正欲開口,他卻搶先再說:「前邊有群樵夫,我過去問問。」然後一溜煙地跑開。
望著漸漸遠去的背影,她深深嘆了一口氣,眼下只得先將兒女情長擱一旁,把心思花在要事上。下了決定後,視線移到師弟說的那群樵夫,樵夫一共七人,頭綁藍巾,距離太遠,看不清他們的樣貌,僅見其中幾人兩腮蓄著短鬚,體型高矮不齊。
羅韞盤越來越靠近人群,樵夫們依然自行自路,左肩擔著兩捆木頭,隨著步伐上下跳動,右手五指緊握斧頭……
小師弟出聲搭話前,談皓猛地高叫:「小龜,當心!」
此話一出,木柴立即喀喀掉地,斧頭對腰砍來!已有防備的羅韞盤急抽鐵尺,「鏗!」斧鋒卡在兩尺交叉處,羅韞盤雙腕一翻,兩把鐵尺夾住鋒刃木柄,一拉一帶,瞬時繳械!
接著兩把斧頭左右襲身,他速速後撤,卻給另外四人封住退路。心叫不妙之際,一斧逼至左頰,一斧迫至右腰,三叉鐵尺轉守反攻!左尺直戳,右尺橫劈,兩敵摀腹掩面,蹣跚而退,然則羅韞盤猶未脫困,在他的視野死角,三把斧頭破風欲殺!
千鈞一髮之刻,天外飛來另一柄鐵尺,正中斧面!力道之大,不但擊偏第一把斧頭,尚存餘威撞開第二把,談皓及時趕至,一記高抬腿踢中斧後手腕,第三把斧頭在半空中旋了六圈半後,落在青青秧田之中。
拾起方才擲出的鐵尺,談皓當機立斷:「小龜,走!」己方人數不佔優勢,早前又聽寧澈描述晉淵莊的厲害,深恐敵人一擺出三垣九星陣,非死即傷。
哪有這等容易?敵方七道身影交錯,再度包圍談羅二人。
一人當先發招攻向談皓,談皓左尺攔下斧鋒,右手倒持鐵尺進攻,尺柄末端捅著敵腹,一擊退敵!隨後縱身一旋,巧轉鐵尺,靈動生風,一雙柔荑似是拈著兩朵耀黑的飛花,快截迅刺摀復扦,剋刀制劍解槍斧!
這一廂談皓以一敵五,另一廂羅韞盤雙手與四拳戰得難分難捨!「鏘!」一聲響亮,鐵尺架住當頭劈下的斧頭,再直腳前蹬,踹人入田,旋即迴身對付剩下的那個。該人手無寸鐵,拳頭還沒打直就被扣住手腕,後遭鐵尺如棍揮下,啪啪啪啪,轉眼間,他的臉面又是血又是瘀清的,滑稽可笑。
末了羅韞盤一腳勾倒敵人,正要補上最後一擊結束戰鬥,原先被他踢進田裡的人已爬上,鬼吼鬼叫地撲來,更令人頭疼的是,他雙斧在手,氣勢洶洶!
臨敵經驗不多的羅韞盤心下一慌,連忙避遠,敵人得以相會,被揍得鼻青臉腫的人呸出一口血,抓過同夥遞來的斧頭後,咧齒獰笑,踏步欺上!
危急時刻,羅韞盤強定心神,眼見二人前後逼近,就先等前斧失準斬空,右尺劈其側顱,再擎高左尺鎖住後斧一扳,敵門大開,右尺尖端直奔眼目!
「小龜,別下殺手!」談皓喊完,矮腰閃過橫向砍至的短斧,左尺一揚二甩,兩人咚咚倒下;右尺三挑四拍,又有兩人悶哼昏死。第五人雖見同黨如紙片一一軟倒,仍不甘示弱,斧頭高舉高下,卻被精準格住右腕,她再運臂一拐,把人的臂膀反剪於後,另一手的鐵尺抵上喉頭,冷問:「你們是何人?到此有何目的?」
一開始會對這七個人起疑,是因這群樵夫各挑著兩擔柴,明明路寬人少,卻要單肩扛之,斧頭也不收,拿在手裡大搖大擺的,甚是古怪。衝突發生後,談皓便察覺不對,這七人雖皆身負武學功底,但出招雜亂無序,毫無配合,想怎麼來就怎麼來,遑論軍勢陣形,絕非寧澈口中訓練有素的晉淵莊。
「哼!那東滎派的又來幹啥?難不成神都待不下去,跑來嘉興搶地盤?老子我同意了嗎?」那人受到桎梏,僅能歪著半邊身講話,語氣依舊狂妄噁心:「小妞兒,勸你快放開老子,否則等老子掙開了,不把你肏得……唔!」話到一半,逕被尺柄敲得翻眼暈厥。
素手一鬆,六尺之軀頓時仆地,正臉重重親上泥土路面,屁股高撅,姿勢頗為難看。
「哎,你別亂動,乖乖讓我師姐問幾句話……」相較談皓的俐落颯爽,羅韞盤正努力將人壓制在地,但怎樣壓都壓不好,身下人像條會罵髒話的大鰻魚,扭來扭去地試圖逃脫,「安分點,不然我下重手啦……」
正當他忙得額頭冒汗,一只尺寸略小的黑靴輕輕踩著髒兮兮的後頸,女音冷硬:「再動,就踩斷你的脖子。」那人立時不動,噤若寒蟬。
談皓二問:「名字?目的?」
「他們是火猿寨的土匪。」清朗的男聲插進,轉過頭瞧去,正為桓古尋。他與寧澈、謝追鴻一起走來,對著趴地的人說:「我記得你的味道,你是在宋城時,想毒死旅店馬匹的人……唔……希望那些馬兒後來沒事。」接著歪頭瞅人:「你是不是瘦了?」豈止瘦了,他兩眼發黑,雙頰凹陷,看來日子過得不太好。
寧澈眉一軒,彎下腰說:「你們的三個當家皆到地獄還他們業報了,還想搞甚麼鬼……啊!」他撫掌醒悟:「該不會是要運出那些黃金吧?」後又瞄了瞄散於四周的斧頭木柴,笑道:「居民沒提及汝等,看這樣子,先前顯是躲在野林裡過活,挨到今時方敢現身,打算鑿開墳墓,盜走裡頭的不義之財,卻好死不死,撞在談姑娘和小龜的手上。」
火猿寨一事,謝追鴻等人亦明大致情形,他道:「既已逃過追捕,為何不思改過,棄惡從善,非要往死路走呢?」
那人側過頭面對謝追鴻:「火猿寨和東滎派素來河水不犯井水,老子要做甚麼,關你屁事……喔喔咯咯咯咯……」頸上的靴子力道忽大,使人難以呼吸。談皓正色:「火猿寨的罪孽罄竹難書,讓你們多活一刻都嫌慈悲心氾濫,哪來的河水井水之分?」
「呵……」那人左臉貼地,頸部受迫,卻語帶嘲弄:「平平都是搶東西……咯……我們搶錢叫土匪咯……那你們……搶神器叫甚麼?少在那邊假清高!」
此話說得斷斷續續,卻令現場氣氛凝結一瞬。
談皓移開皮靴,「嘉興縣令鐵面無私,把他們交給官府吧!」
「正好李大人在偵查此案,他會很感激這份大禮。」寧澈長身道:「勞煩三位將這幫匪人移送至衙門,我和阿尋繼續探詢。」
「我留在這裡幫忙!」羅韞盤道:「晚點我再和小澈他們一道回杭州,師兄師姐不必擔心。」
劍眉一挑,朗星般的明眸悄悄瞥了師妹一眼,但瞧她不發一語地取出繩索,縛住七個敗寇,謝追鴻心底一嘆,口說:「好,萬事小心,切莫輕舉妄動。」
牢牢綑好匪徒後,謝追鴻一掌一個拍醒昏去的人,同談皓一前一後地押隊,邁向縣城。
隊伍行遠後,羅韞盤首先啟口:「接下來要做甚麼?」
桓古尋卻問:「你和你師姐怎麼啦?」「咳!」他縮了縮脖頸,閃爍其詞:「甚麼怎麼了……沒事啊……」
「哪裡沒事了?」寧澈直接戳破:「從面見潘文雙那天,到今日你們倆都沒正眼瞧過對方。」
羅韞盤大感尷尬,煩躁地擺擺手,「別管這些芝麻蒜皮的瑣事,你們不是有許多活兒要忙嗎?」
當事者不願談,他人自不強迫,寧澈遂說:「我們探聽的結果和你們一樣,嘉興政通人和,很難想像會有人意圖謀反。」
「然則叛黨不在這裡囉?」羅韞盤提議:「興許是在偏僻的小農村……」
「不。」寧澈搖了搖食指,「像他們這類不明著起兵反抗,劃地為王,而是潛伏暗地,四處流竄的,最重視新聞音訊,定要經常走訪通都大邑,方能掌握先機勝券,兼且城邑人口稠密,皂帛難分,龍蛇雜處一地,反倒比藏匿窮鄉僻壤更難調查。」
羅韞盤努嘴:「盤據城邑雖然不易被找到,卻有個大隱患,一旦被看出端倪,即是覆巢傾卵。」
「因此得選個介於城市與鄉下之間,既可即時獲知新訊,一有突發狀況又能迅速撤退的地點。」桓古尋闡述己見:「嘉興緊鄰蘇州州治的吳縣,與吳縣不過半個時辰的航程,有甚麼大事,透過往來的船家就能得知,即使真被朝廷發覺,周圍便有現成的軍田糧倉,就地造反都不是問題,反而是朝廷的兵馬要煩惱糧草通路。若造不了反,四面交通發達,在人數不多的情況下,藉由密林水渠,即能遁逃他方,捉也捉不著。」
「在這裡晃了好些天,僅知縣官課稅少,稻田收穫多,看不出絲毫異狀,難不成整個嘉興皆與叛黨為伍,互相包庇?」連日追查無果,羅韞盤的猜想不由得誇張起來。
「人沒異狀,不表示地沒異狀。」寧澈掏出一張紙,道:「我們適才繪製地圖,粗略畫出這個村莊東西南北的地貌、河渠、道路、稻田、糧倉及房舍。」
地圖簡明易懂,無須解釋便能理解圖中所繪:數十個「木」字聚集代表森林;彎彎曲曲的單線條是道路,雙線並行則為河渠;數塊相鄰、內有「禾」字的方框是稻田;頂著三角形的圓圈該為糧倉;其餘大小不一的方形便是房舍。
羅韞盤第一眼便瞄到一處被圈起的方形,遂問:「這是甚麼?」
「官用的水碓房。」寧澈捏著鉛筆虛畫,「依照律令,年過二十一歲的男丁每年須上繳三斛稻米給官府,官府將收來的稻米運至糧倉儲存,每月發放糧餉時,領到米糧的差役會到這間水碓房舂米,其規模相當大,能同時供五十個水碓機運行。」
「你要設陷阱埋伏?」覷狡黠的鳳眸咕溜溜地轉,羅韞盤道:「會不會太躁進了些?畢竟仍未確定他們就在這個庄頭謀事,也不能確定他們何時聚會。」
「他們若在嘉興,就一定在這座村莊。」桓古尋很是篤定:「這裡不但有整個嘉興最大的水碓房,並且超過半數的農戶是外地人。」
「喔!」羅韞盤說:「邀請我們作客吃飯的霍二娘,他們家也不是土生土長的嘉興人。」
「我的想法與謝師兄的一致。」寧澈道:「叛黨如若假扮平民,定居此村最易掩人耳目。」
羅韞盤點點頭,而後躍躍欲試:「那你們要設下甚麼樣的陷阱?要不做個機關?」
「不急……」晶瞳澄淨如洗,與白亮的犬齒一同閃耀:「先去常州玩個幾天再說。」